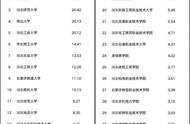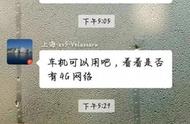在郝懿行的笺疏中补充了其外貌特征以及人取养之的特性:“ 陈藏器 《本草拾遗》云:‘风貍似兔而短,人取笼养之。’即此也。”而在宋人汪若海的 《麟书》中,显然则更加强调它对于人心的治愈功能:“安得朏朏之与游,而释我之忧也哉!”
不难看出,这里的“其状如狸”以及“养之已忧”,不正是现代人眼中的猫主子的真实写照吗?但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古人眼中的”狸“在早些时候,一般多指野猫;而”忧“则很有可能在当时指鼠患。

猫这个字最早见于《诗经·大雅·韩奕》“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在此将猫和虎并举,和现代人将其归于猫科动物的做法是一致的,但此时的猫还尚未被人类驯化,属于野猫。到了春秋战国,《礼记·郊特牲》中有“迎猫为其食田鼠也“,《韩非子》中有”使鸡司晨,令狸执鼠“的说法。
可见,此时狸猫已经开始为人所驯养,并专门用于解决老鼠问题。
此时,人类尚未彻底沦陷,而当赋予它的实用价值日渐稀薄后,“猫奴”才由此诞生!
宋人聘猫要论生活情趣,恐怕没有哪个朝代能比得上宋朝。在君主高度集权的历史情境之下(不需要贤臣,只需要忠臣),宋人进不能“治国平天下”,便只好退而“修身与齐家”,将唐人追求事功的“外王”纳入到了注重个体修养的“内圣”之中。
时代精神与审美情趣的转变,人们目光从盛唐的“黄河”、“落日”、“大漠”、“孤烟”,一变而为“空庭”、“梧桐”、“微雨”、“芭蕉”。在细琐平易之间、浅吟低唱、辗转腾挪,因此更加注重对于日常狭小生活的性质和趣味,软萌较小的猫,便在此时映入宋人眼帘,不停地在其心上挠上一挠。

宋人养猫有多狂热,从北宋汴京以及南宋杭州都有专门卖猫粮的市场就可见一斑。《东京梦华录·诸色杂卖》中有“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的记载,原来,人不分古今,只要被其征服、沦为猫奴,都得拼命干活去给猫主子买小鱼干啊!
陆游知道吧?这个忧国忧民的汉子,此时也无法抵御它的“萌力”,在壮志未酬退居到山阴老家,便养了一大堆猫,而且为每一个猫主子都起了独一无二的名字,比如什么“粉鼻”、“雪儿”、“小於菟”等等。此外,为猫写诗,也是情理之中,比如这首《赠猫》写的就极为有趣:
“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

他对猫爱得深沉,爱的热烈,和猫在一起的时候,非但没有壮志未酬的满腔悲愤,有的反而是如老父亲般的宠溺。说自己好不容易请到了猫君,帮自己护住了万卷藏书,但无奈自己这个铲屎官很穷,让猫君睡觉没有温暖的毡子,吃没有美味的鱼干,自己真是惭愧的无以复加。
果然,吸猫一口,便落入虎口,这个问题不仅现代人有,古人也有而且似乎“病的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