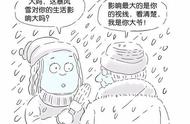6月16日,河南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百米长的花圈靠着围墙,摆在灵堂外,从中午到晚上,仍在延伸。
除了父母两边的亲戚,张计发的四个女儿,没再通知其他人——更多人是在看到新闻后赶来的。
络绎不绝的吊唁者,涌入灵堂。长明灯的烛光,跳跃在张计发遗像上,左胸挂满了军功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摆在灵位右边,这名194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没有机会再戴上它了。
6月15日7时30分,抗美援朝战斗英雄、电影《上甘岭》连长原型张计发病逝,享年95岁。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他共打了10年仗,荣立特等功4次、一等功2次。离休后,为青少年作革命传统报告1500余场次,光聘书就有一大箱,当地不少上岁数的人,都知道这位“张连长”。
张计发逝世当晚,信阳下起大雨,此后连日都是阴雨天。

6月16日,张计发的灵堂外,花圈摆了一排。新京报记者杜寒三 摄
“你打下的江山我守着”
在一众黑衣的家属中,外孙崔和平,穿着一身醒目的军装。
17日凌晨,灵堂外。崔和平练着礼步,从这头走到那头。他是孙辈里唯一当兵的,当天出殡时,将抱着遗像,走在队伍前头。
每年回家探亲,如果崔和平穿着军装,上下打量后,张计发会满意地点点头:“嗯,小伙子,部队需要你干多久,你就在部队干多久。”这次奔丧,崔和平特意带上了军装,“看着我穿这身衣服,他会开心。”
天空泛白,离出殡时间近了,守了一夜灵的崔和平,又换上军官礼服。
“穿这身送姥爷,他配得上”,崔和平说。金黄色的装饰条,从肩上垂到前胸,两夜没有合眼,这身军绿色却衬出了精气神。他和张计发都长着又黑又浓的眉毛,人们见着他,都会说上一句,“你和姥爷真像”。
最后的时刻到了,崔和平戴着白手套,从灵堂抱出遗像。
送行者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有人举起手机拍照,有人闭眼双手合十。还有一个大叔弓着背,朝远去的灵车敬军礼。前往殡仪馆的路上,下起大雨。一长串车队,打着双闪,一眼望不到头。
信阳市殡仪馆福寿厅,张计发的遗体被鲜红的党旗覆盖,瘦削的头上,罩着一顶空军蔚蓝色的大檐帽。
家人们哭得泣不成声,崔和平却憋着眼泪,“我不能穿着姥爷喜欢的衣裳,在送他上路的时候哭,这样对不起这身军装,也对不起他。这是我作为一个军人必须要有的坚强。”他左手托着军帽,鞠躬向遗体告别:“姥爷,你放心走好,你们当年打下来的江山,我们好好给你守着。”
雨没有停,更显红山公墓松柏青翠。
张计发的墓穴里摆入了《上甘岭》连环画,一副墨镜等物品。他一生守时,离不开手表,但住院时瘦得很,表在肘关节还戴不上。本想留作纪念,三女儿张爱民还是把这块表放进了墓穴里。
“老连长,我爹在隔壁,你们可以一块儿喝酒啦”,有人跪在坟前说。
崔和平撑着一把黑伞,挺直腰杆站在一边,迎接一拨又一拨叩拜者。“这伞该由我来撑,不管是他的家还是国家,都有一个从军继承他事业的外孙帮他守着”,崔和平说。
张计发生前常说:“我要好好活着,替那些牺牲的战友,看看祖国美好江山”。说到这些,崔和平笑了,“姥爷的战友叫他去报到了,回去看一看他们。”

6月17日,信阳市殡仪馆,人们赶来送“张连长”最后一程。 新京报记者杜寒三 摄
“一个苹果”和一篮子苹果
6月17日,张计发下葬当晚,信阳当地电视台重播电影《上甘岭》。
1956年,正是这部电影的上映,使他作为志愿军某部八连连长张忠发的原型,被全国人民熟知。三年内,他都不忍看完这部影片,但在看完后又说:“战争的残酷和激烈展现得都不充分,不及十分之一。”
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张计发共打了10年仗,他最难忘的仍是上甘岭战役。张计发91岁那年,侄子张二顺问起这场战役,他还止不住掉泪,此后张二顺再也问不出口,“他掉泪我心疼”。
一组数据说明了上甘岭战役的残酷:“联合国军”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山头被削低整整2米,表面岩石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志愿军第15军45师,27个步兵连有16个连两次打光重建;最终飘扬在主峰的战旗,布满381个弹孔……
张计发曾回忆,上甘岭阵地上浓烈的硝烟夹杂着血腥味,飞机、大炮不断狂轰滥炸,整个阵地像大海里行驶的船儿一样不停地摇晃,表面阵地上根本无法站人。
1952年10月15日,张计发所在的15军45师135团7连,奉命转入坑道,在坑道里坚持了10天。层层封锁切断了粮食和水的运送,严重缺水下战士们的嘴巴裂开口子,浑身像是着了火,他们将身体和嘴巴贴在坑道壁上,用凉爽的泥石缓解身体痛苦。尿液由白变黄,又变成红色,后来是紫色的,最后排不出尿液——腥臭的尿也成了宝贵的水源,战士们端着自己的尿,谦让给战友。有的伤员紧闭着嘴,牙齿咬得嘎嘎响,有的咬掉了舌头,但为不影响战斗情绪,没有一个伤员喊痛叫苦。
10月31日傍晚,在阵地上苦战近24小时后,7连大部分战士都已牺牲,只剩下包括张计发、4名步话员、卫生员张乐、通信员邢志林和受伤战士兰发保在内的最后八人。
上级命令四连派5个战士前来支援,战士刘明生塞给张计发一个苹果。四个步话员喊哑了嗓子,遇到紧急情况喊不出话,猛抽自己的嘴巴打出血润润口,接着喊话。张计发先把苹果交给他们,但他们闻了又闻,摸了又摸,谁也没舍得咬一口。他又传给了伤病员、卫生员、通信员,苹果在8个人手中传递,转了一圈,又完整地回到张计发手里。张计发说:“同志们,我们可以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却连一个小小的苹果也消灭不掉吗?”他带头咬了一小口,苹果在8个人手里转了三圈才吃完。
在张计发长女张爱党的印象里,上世纪60年代家庭条件困难,但只要一来卖苹果的,父亲就会买上好多,分给孩子们,“那么多战友都没有吃上,现在可有苹果吃了,你们多吃。”
张计发去世后,一篮苹果,被黄白两色的菊花簇拥,搁在灵堂。
上甘岭战役结束,张计发220人的大连队,仅剩23人。2020年,张计发因病住院,护工张新丽说,每当有人探望时叫他“英雄”,94岁的张计发会收起笑脸,赶忙摆着双手:“可不敢这样说,我不是英雄,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才是英雄。”
接着,他会报起一个个战友的名字。

6月16日,张计发灵位前,摆着一篮子苹果。新京报记者杜寒三 摄
“军功章都是你的”
南征北战,张计发有不少军功章。他曾对妻子魏祖勤说:“军功章不是我的,都是你的。不是给你一半,是全部给你。”
1955年,29岁的张计发已是大龄青年。在妇联的动员下,19岁驻马店姑娘魏祖勤和张计发花了5元钱,置办了瓜子、花生、糖果和两个西瓜,算是结了婚。“为啥人家那么大岁数?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都有饭吃”,魏祖勤对浓眉大眼的小伙一见钟情。张计发肤色黝黑,魏祖勤皮肤白白的,他老打趣说是“黑小子找个白妮”。
魏祖勤的卧室,挂着结婚50年后补拍的婚纱照。这是她第一次穿上婚纱,花白的头发打着卷儿,捧一束红花。老头儿穿一套黑礼服,俩人贴在一起,露出灿烂的笑。
1962年,患上肝硬化的张计发,被医院判了死刑,心情愉悦的情况下,还有可能活3到5年。他挺着肝腹水的肚子像个孕妇,几家医院都治不了。
张爱党念小学的时候,张计发上她的学校作报告。望着台上挺直腰杆的父亲,张爱党知道,那是因为弓腰窝着肚子犯疼。他每次入座,屁股都贴着椅子边,裤腰则用一根细绳拴住。
魏祖勤四处寻医问药,用20颗红枣、20个莲子和20粒花生米熬制炖品,再搁点红糖,睡前让丈夫服下,一熬就是二三十年。
1966年,40岁的张计发因病离开部队,来到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生活。他将当时三个女儿的名字改为张爱党、张爱军和张爱民。1967年,小女儿出生,他取名为张爱东,热爱*之意。“他不能继续为党工作,就用这种方式来报答”,张爱党说。
失落之下,张计发把劲使到了孩子们身上。每天清晨在家吹响哨子,规定穿衣服、叠被子、洗脸、刷牙的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三个孩子在院里集合,跑步、投掷手雷模型。若是迟到,张计发就抄起小棍子打。到后来,几个孩子都不敢脱衣服睡觉。
张计发有午睡的习惯。吃完午饭来不及收拾碗筷,魏祖勤会把孩子们招呼到外头的树荫底下。母女们围成一个弧形,孩子们嬉戏打闹,魏祖勤织毛衣、纳鞋底子。待张计发睡醒了,才领孩子回去。
魏祖勤常同孩子们说:“不要惹你爸爸生气,他有病,能活一天是一天。”
在魏祖勤的调理和包容下,张计发的身子,一天天好起来。他对妻子说过,“你是张家的功劳,没有你就没有我,临死我得给你磕个头。”
6月17日凌晨3点多,85岁的魏祖勤,又一次拄着拐杖挪进灵堂。冰棺上蒙着一层黑布,看看老头穿得咋样,成了她最后一个愿望。“怕老了眼睛看不见”,早在20年前,魏祖勤就给老伴做好了寿衣。
操劳了一辈子,魏祖勤没让张计发做过一件家务,他出门兜里甚至都没装过钱。魏祖勤说:“我没啥了不起的,但没拖过他的后腿。他为革命、为祖国出力,我好像也给国家尽了一份力”。她揉着自己的膝关节,“我要完成任务了。”

6月17日,85岁的魏祖勤在家中。她说这辈子没给张计发拖过后腿。新京报记者杜寒三 摄
医院里的“张宝宝”
6月18日,张家人来来回回好几趟,才把病房里的东西搬走,“住了快3年,都成自己家了,跟搬家一样。”病床上的墙上,贴着小学生看望张计发时送的手绘画。一盒铁罐子里,堆着张计发没有吃完的糖,药苦,他爱含着甜的。
医院清洁员刘玉兰再往里探脑袋时,空荡荡的病房,只有沙发上留着一沓X光片。刘玉兰曾拍下张计发的一张照片,一张在张家人手上,一张摆在自己家里。他们唯一的交集,是刘玉兰打扫他房间时,张计发会挥手说:“你辛苦啦。”
胃癌晚期并多发转移癌、营养不良性肝硬化、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联勤保障部队第990医院信阳院区,4446号病人的最后诊断,密密麻麻列了12条。像这样的病人,生存期或许只有3到5个月。心肾内科副主任蒋德军说:“能活这么长时间,是个奇迹。”
每天早上,蒋德军见到张计发在走廊里坐着轮椅,还能走路的时候,他由闺女搀扶着,走上两圈。老人家爱唱歌,唱的最多的还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这么多年过去,不忘词也不跑调,有时整层楼都能听到。
在张计发生命的最后几年,家人们有时开玩笑,叫他“张宝宝”。
护工张新丽早年是幼儿园老师,躺在病床上的张计发,乖乖地跟她学唱儿歌。他摆出走路的姿势,假装给自己戴上军帽,敬一个军礼:“解放军真正好,穿军衣、戴军帽、扛长枪、开大炮,打得敌人嗷嗷叫”。他还会改编,“花园里花儿开,红的红,白的白,花儿好看我不摘,大家都说我真乖”,左右晃着脑袋,把最后一句唱成“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好乖乖”。
张计发也有脆弱一面。
他告诉张新丽,他想老家兄弟,想妈妈了,“我妈可辛苦,没有享到福。”16岁那年,张计发离开家乡河北赞皇,加入抗日先锋队。在他的印象里,小时候经常半夜娘还在纳鞋底;凌晨鸡叫头遍,她又下炕打水刷锅扫院子;天还没大亮,娘一准儿在磨房推豆腐,“一年到头,我娘的双眼都是红红的。”
有时一觉醒来,张计发又掉下眼泪,说梦到战友了,还是在前线,“特别想他们”。
6月15日7时18分,张计发被宣告临床死亡,他终于和老娘、战友们团聚了。
这些日子,张新丽常梦到张计发。每天六七点钟起床,张新丽拉开窗帘。若是晴天,他两只手在被子上打节拍,笑着唱:“这样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开往前线,老乡们呐听分明,这就是那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军民团结咱大家一条心,打走那个日本鬼子咱享太平!”病房朝东,太阳像鸭蛋黄一样,阳光洒在他的病床上。
张计发身体好的时候,驼着背弯着腰,每天在家门口的浉河边上走两圈。下葬当晚,河边依然人来人往,有人遛着狗,有人摇着蒲扇,还有人在钓鱼。他埋葬的红山,离这不远,在这条路上就能望到。
(文中崔和平为化名)
部分资料参考自《铁血丹心:张计发回忆录》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