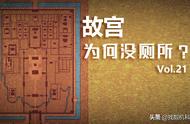12年深秋的时候,我去疗养院看过我妈。
她瘦了很多,在老年人里也并不合群。她几次病倒进了医院。
医生说,她的病况也越来越复杂,尤其是那些特殊的病,严重影响了她的身体。
那些病,是瞒不住的。
所以疗养院里的人打听到我妈的病,并不为奇。
只是,她们大概知道我妈得的是脏病后,眼中的鄙夷和不屑太过赤裸和明显。
不得不让我妈回想起
那些尘封着我和我妈所有的过往。
我曾以为,这辈子我和我妈都不必再想起的那些难堪的过往。
终究还是难以真的逃离和躲避。

07年,我八岁的时候,我妈就背着包袱离开了家乡。
我爸带着我和我哥去送站台送我妈,那时候,我还很小,不懂得别离的痛苦,只知道我爸说我妈是出去大城市挣钱。
等过年回来,我们家就有钱了。
有钱买糖,有钱买肉,也有钱买最漂亮的衣服和最好玩的烟花。
我很欢喜,并没有像哥哥一样,哭着求妈妈不要走。
我哥比我大几岁,对于我妈的离开,他已经朦朦胧胧意识到了什么。
所以,他哭得很凶。
对了,你看我,差点忘了和你们说说我爸。
我爸是个酒鬼,也是个赌鬼。
我妈嫁给他之前,我爸是开着一个棉花铺。
就是专门给人弹棉花,那时候这项需求在农村很旺盛,生意也一直不错。
但没人想到,我爸会在婚后第二年,染上赌瘾,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我妈嫁给我爸几年后,我爸迅速的输光了所有的家当。
连弹棉花的机器和家里的彩电还有我妈陪嫁的缝纫机都输了。
我爸开始酗酒,经常打我妈。
一边打一边骂我妈是扫把星,娶了她以后,他的好运都输光了。
就这样,我爸还是好赌,还借了高利贷。
我爸没钱还,就跑出去躲债。
赌场的人来我家里搬东西的时候,我妈哭着把我和我哥护在怀里。
那些讨债的人,搬的搬,砸的砸,满屋狼藉一片。
要债的人还恐吓我妈说要是不还钱,就等着给全家买棺材。
彼时我哥十一岁,已经有了男孩的一丝血性,他冲上去咬了一口恐吓我妈的男人。
男人转手就是一顿毒打。
我妈死死护着我哥,被一巴掌扇肿了脸。
要债的人骂骂咧咧的走了后,我和我哥才抱着我妈倒地痛哭。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哥就发了誓,他说他这一生都不会再认我爸。

半个月后,我爸听见风声过去,才从外面回来。
他跪在我妈面前哭了一宿,他求我妈想想办法。
我到底还是心软了,她去姥爷姥姥家借了钱,还了一部分债,保住了我爸不去坐牢。
可没过多久,我妈再次在赌桌上找到了我爸。
你看,可笑吧。
就算是这样,我爸都没有回过头,他依然好堵如命。
他已经赌得昏天暗地了,一把推搡开我妈。
他说:“滚。”
“倒霉货。”
那天,我妈彻底死了心,咬着牙从赌桌出来。
她清楚的看明白了,一个赌徒,就算是死,也不会戒赌的。
几个月后,家里实在没法支撑。
我妈狠心抛下我和哥哥,随着北上的妇女一起北上打工。
我妈选了最苦的塑胶厂,开始没日没夜的熬,熬命一样赚钱。
我和哥哥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只是家里的米缸终于有了米。
我爸依旧整日整夜的赌,很少归家。我哥就带着我自己做饭,洗衣,生活。
他只比我长几岁,却在我妈离开后像个大人一样,操持着家里的一切。
我妈在塑胶厂干了几年,落了一身的病。用血泪换回来的钱大部分都被我爸摔在了赌场上。
那几年,我爸风光得意,在赌桌上下的筹码也越来越大。
很多时候,我妈前脚汇钱回来,后脚我爸几把就输光了。
所以,即使我妈在外再拼命,我和我哥的日子依然艰难。
上学没学费,换季没衣服,一日三餐都靠运气。靠我爸偶尔的想起,他买面,我们就能吃面。
他买米我们就能吃米。
他什么都不买,我哥我就带着我在后山里刨人家地里的红薯,玉米,土豆。
一年四季,季季如此。
我们活得像孤儿。
我们这个家也像是一个无底洞。
我妈拆了自己的每根骨头,榨干自己的每滴血液,也难以填平。
我上初中那年,我哥考去了全免的封闭高中。
那时,春城里已经有了很多我妈的风言风语。
她们都说,我妈在外面做了不干净的事情换钱。
她们总冷着眼对我和我哥说,“*真能干。”
“你们家就靠*发财了啊!”
我和我哥都隐约明白她们话里有话,我哥耿了脖子,从不理会人家。
他也不许我理会。
可我哥不知道,他去读书后,那些与我同龄的孩子说出的话是怎样难听的。
破鞋,婊子,鸡……
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频繁和人打架,头破血流,满身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