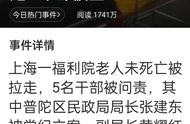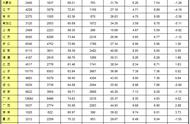高中的时候,学校里有间很迷你的图书馆。藏书不算多,对于当时除了课本什么都想看的我,已经是快乐源泉般的存在。在那里看到过两本书,时至今日仍然对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本是《黑镜头》,另一本是《人类尸体的奇异生活》。
后者以一种轻松幽默的口吻,讲述了人类近百年历史中,如何利用尸体推进科学发展,社会进步。当时莫名吸引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浏览,心中渐渐形成了对于死亡平和的认知。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的潜意识里就已经将自己的躯体单纯当成了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组合,老早就埋下了“死了也要拿这一百多斤干点儿啥”的种子。

《人类尸体的奇异生活》部分目录
然后到了大一,终于远离原生家庭的我拥有了脱缰野狗般的自由。
蹲在宿舍阳台上百无聊赖,对面就是北大医学部。我鬼使神差地想到了高中时看过的闲书,当机立断打电话过去要登记遗体捐献。接电话的阿姨诚恳又真挚,说你年纪还小呢,长大点儿再考虑这些也不晚。我懵懂又天真,说医生为什么啊,我就是想做点好事。医生叹口气说姑娘,遗体捐赠需要家属签字的,你爸妈给你签吗?你又没结婚,也没有老公孩子给你签吧?
肯定地摇摇头,就凭家里二老的脾气和思想,估计没等我捐献遗体,他们就会把我揍成遗体。

声明书,要拿去做公证的。
然后我就长大了,顺遂又平稳,完全是没有经受过社会主义毒打的小天真。直到去年,我作为一个非直系亲属,从最初去医院看病起,亲历了四舅病重,病危,弥留,去世,入殓,火化,下葬的全过程。一切结束后,四个月的疲累让我迷迷瞪瞪中摔伤了腰,也让我这个全程没有哭过的异类,总在午夜梦回,想起三舅撑着佝偻的身躯,在家人的搀扶下走进太平间,慢慢地蹲下,颤抖着嘴角,却发不出声音。他伸出手摸摸弟弟的脸,努力张了张嘴,却只撑得脸上的皱纹像是干巴了的橘子一样越发难看。
人都死了,擦身用凉水又怎样呢,没必要特意去接温水了。
你们再揉搓四舅的胳膊也没用了,你看那监护仪都直线半小时了。
穿寿衣?穿什么穿,反正都是要扫到裹尸袋里往太平间小格子一推,跟猪肉似的冻起来的。
你看我没说错吧,火化的时候,棺材里的尸体,衣服早就给脱了。
四舅妈您也不用拿着四舅的旧衣服一起去火葬场的,人家不让烧,到了也是扔进垃圾桶,一会儿就不知道被哪条产业链捡走了。
怎么还有酒席?一吃能吃好几天啊?吃给谁看,给四舅看吗?
守夜?为什么守夜,蜡烛灭了又怎样,人都死了点蜡烛干啥,大冬天的冻感冒了得不偿失。
也许像我这种人,美其名曰无神论,实际上只是彻头彻尾的魂淡。总是尝试着剥离自己最本能的感受,试图以一种貌似客观理智又睿智独立的角度去观察和体会这个世界。怎么,这样的自我感觉是不是很良好?是不是觉得自己比那些哭哭啼啼的人,那些为了灵堂的陈设和祖传的老礼儿争执吵闹的人,比他们都要高贵冷艳啊?
这世界上啊,多得是无用之事,不是做给死人看,只是为了活人心安。它甚至不是以安抚死者家属为目的,浩浩荡荡的排场,多半是摆给街坊邻居,三姑六婆,顺便附带让死者家属心安理得的作用。你看,你都死了,我还为了你花钱花时间花精力,我对你很好,我问心无愧。
人死之后的一系列操作真的是没什么意思。
大概是因为,那哭声太痛,墓地太冷。
以前有一个挺火的电影,叫《寻梦环游记》,大概是说人死了之后,只要活着的人不忘记他,时常祭奠他,那么他就可以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存在。如果所有人都忘记了他,那么他会第二次死去,彻底烟消云散。电影内核挺温馨,可惜打动不了我这种彻底没有信仰的魂淡。

我们纪念逝去的亲人,但或许可以让生命发挥更大价值。
如若真有死后世界,那么用最后的血肉之躯,为人类医学事业做贡献的我,这种高尚的奉献精神,是不是还得加分儿啊?没有墓地也得给分个阴间高档独栋别墅住住吧。
然后我就又想起遗体捐献这事儿了。
遗体捐献,大概分这么几步:
1.上红十字会官网下载表格,打印出来填好,找几个亲戚朋友签字画押,大意就是等到捐献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人;
2.带着表格和身份证户口本啥的,找个公证处办公证,免费的。有些公证处需要提前预约;
3.等个两三天,去公证处领公证书;
4.拿着表格和公证书去你要捐献遗体的单位登记,完事儿。
我是在北京做捐献登记的,直接度娘搜索“北京市红十字会 遗体捐献”。第一条搜索结果点进去,就是北京红会网页,有表格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