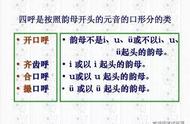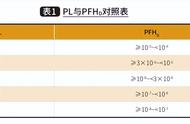从“烟胡”“麻镀”等语汇看涟水方言的韵母特点(上)
——涟水方言概说之二十五
□ 万洪勇
隔壁的堂兄娶了个黄营媳妇,这使我对黄营口音有了直接的感受。最突出的印象是,堂嫂子把“坐”说成“住”,把“锅”说成“姑”,感觉真的好新鲜。
“坐”和“锅”韵母都是uo,而“住”和“姑”韵母都是u。从uo到u,变化在于丢掉了韵尾。那么,在涟水范围内,这种将uo变成u的现象是不是仅仅存在于黄营呢?答案是否定的。
后来我发现,大东镇小南村的人会把萝卜说成“卢不”,“萝”之为“卢”与“坐”之为“住”不正是同一种状况吗?再后来我又省悟到,就是我们大东集镇上,也存在将uo变成u的现象。例如,大东人把“烟花”说成“烟火花炮”,而且把其中的“烟火”说成“烟胡”,说轻声的时候“烟胡”接近“烟乎”。再如,“花骨朵”我们大东人会说是“花骨堵”,“唾沫”会说成“兔沫”。“火”变“胡”、“朵”变“堵”、“唾”变“兔”,这跟黄营口音的“坐”变“住”、“锅”变“姑”规律相同。
涟东的黄营、大东有此现象,那么涟西也有吗?回答是肯定的——“麻垛”不就是被称作“麻镀”吗?至此可以确定,整个涟水都有把“uo”变“u”的情况,只是黄营比较突出罢了。
那么,我们涟水方言里为什么会有这种口音呢?这还得从源头说起。
《诗经》里的《硕鼠》大家都很熟悉。其第一章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这一章的韵脚在“鼠”“黍”“女(汝)”“顾”“土”“所”这六个字上。前五个字没啥说的,我们今天读来也完全合辙,韵母都是u,但最后这个“所”字,用今音读起来可就完全出轨了,它的韵母是uo。这就说明,我们涟水话里的“uo”之为“u”,其依傍可以回溯到遥远的先秦时代。
查《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的鱼部,可以看到“所”“顾”“汝”“鼠”“顾”“土”确实在一个韵部,这个韵部里还有“奴”“怒”“努”“虏”等字。有趣的是,这后四个字普通话韵母都是u,而在涟水话里韵母都是uo,“奴”说“罗”,“怒”说“摞”,“努”说“裸”,当然,“俘虏”就变成“俘裸”了。
再查《平水韵》七遇部,可以看到“醋”“错”“措”在一个韵部,但是它们在现代汉语里发生了分化,“醋”保留原味,“错”和“措”就“错”开来了,韵母变为uo。不过,在涟水话里,“措”还是放置在原位,和“醋”同味,“措施”听起来就是“醋师”。
由以上两部古代韵书里查看到的这些例字,更可以说明,涟水话里韵母uo和u相纠缠的现象是受了古汉语的影响。而通过查现代汉语辞书,我们会发现,韵母uo和u相纠缠的现象在普通话也留有明显痕迹。如“度”,辞书就给出了两个读音,一个韵母是u,一个韵母是uo,“揣度”“测度”“度德量力”,其中的“度”都注为duó。“数”除了韵母为u的两个注音之外,还给出了韵母为uo的第三个注音shuò,意为“屡次”,典型例句是《陈涉世家》里的“广故数言欲亡”。“朔”注音为shuò,以它为声旁的“塑”“溯”“嗍”注音分别为sù、sù、suō,而北京话里又会把“塑料”说成“嗍料”。“儒”“孺”“嚅”“糯”“懦”,都是以“需”为声旁,而前三个字的注音是rú,后两个字的注音是nuò。涟水话里形容口才不佳、说话不流利会用“罗”,其实就是“嗫嚅”的“嚅”。另外,涟水话里的“*猪驮”其实是“*猪屠”,“屠”韵母为u,而“驮”韵母为uo。这些现象都说明,普通话和涟水话里的uo变u以及u变uo,都是受古汉语这个大气候影响的。
另外,现代汉语辞书所收录的“撸”字,注音为lū,义同“捋(luō)”,并且标为方言字,这好像标的就是我们涟水话呢,我们一定都是说“撸山芋叶子”“把官职撸了”“撸起袖子”,而不会把其中的“撸”换成“捋”。我不知道黄营人是不是会把“啰嗦”说成“噜苏”,现代汉语辞书上反正说吴方言地区会把“啰嗦”说成“噜苏”,“啰嗦”的韵母都是uo,“噜苏”的韵母都是u,这说明吴方言也有把“uo”变“u”的情况,有可能比我们涟水话更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