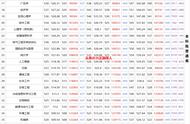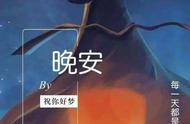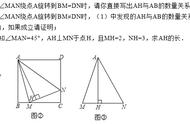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这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彭桓武在37年前信笔写下的题词。
字迹旁边的奖章与证书共同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两弹元勋”彭桓武的“集集体”题词。图片来源:中国核工业
这是大家干出来的
1984年,以彭桓武为首的10位科学家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按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可当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的同志把奖章送去时,彭桓武却坚决谢绝,并且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

2005年,90岁高龄的彭桓武作学术报告。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大家再三劝说,他才同意留下奖章,但他接着说:“奖章是我的了,我把它送给九所。”
随即,他提笔写下了10个字:“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此后每当有人提起他在核武器研究中的贡献,或者媒体采访时,他都在强调,这“都是大家干出来的”。
祖国需要我就去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内容,“集集体”题词正是这项精神的生动再现。
将历史的钟摆回拨到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的合作协议,全面撤走专家,停止供给资料设备。中国核武器研制彻底走上自力更生的探索道路。

1966 年10 月1 日,彭桓武(中)与 朱光亚(左)、邓稼先(右)在天安门城楼。
1961年4月初,彭桓武接到指令,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负责核武器物理研究工作。正如当初回国时的毅然与坚决,他说:“国家需要我,我去。”
当时,唯一可参考的资料是一个苏联专家口头讲述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作为核武器理论设计的领头人,彭桓武不迷信专家权威,将原子弹理论研究扎实推进,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缩短研究周期。
在原子弹理论研究过程中,彭桓武与邓稼先等科研人员用了近1年时间完成计算,光数据纸就有几大麻袋,扎实的理论设计为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奠定基础。
打响氢弹研制“百日会战”
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彭桓武敏锐地意识到,要迅速组织力量向氢弹原理的探索转移。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从1964年年底开始,彭桓武召集各种讨论会,群策群力,形成3个方案。他安排理论部的3位副主任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别带队,多路探索。

于敏在“百日会战”。图片来源中国核工业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创造世界新纪录
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军。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

1992年11月在中物院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于敏。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彭桓武、于敏均在列。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