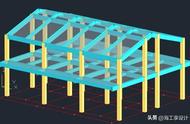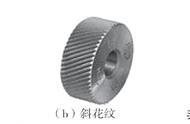“平原”三部曲,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记者:这些部分的确容易被忽略。很少有作家像你这么用心去创造词条,而且在多数小说里,这样的词条只能算是旁逸斜出,只是对故事情节发展起辅助性的作用,它们在你的小说里却无疑是重要的,就像方言也在你的小说里起到强化和深化背景的作用一样。
李佩甫:对,我的小说里会融入方言,但不是按原生态的样子放进去,而是经过了思维认知的转化。也就是说,进入我小说里的方言,都是修正过的。我写平原这片土壤,也有一个调试和修正的过程,围绕的都是对汉文化思维方向的观察和追寻这个中心。我想搞明白我们汉民族是怎么走过来,为什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有可能成为什么样子。
记者:就像你说的,语言就是思维,那我觉得方言更是思维。
李佩甫:相比普通话,方言更具象,它代表的是人们在某个阶段,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的认知。它的出现和发展是有过程的。像“互联网”这样的新词,也只有到了现在才可能出现,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出现的。
记者:也就是说,通过学习方言,写作方言,加深了你对平原这片特定地域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阶段的认知。
李佩甫:对,通过方言更能理解这块地方的生存状态。
记者:你的小说很少线性写一个人的发展轨迹,倒是比较多由一个人串联起一群人,或是先写一个人,再慢慢切入写整个地域。所以,你的小说偏于树型结构或网状结构,要做到形散而神不散是有难度的。
李佩甫:因为我主要写关系,写土壤和背景。马克思有句话说,人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人不只是人本身啊,他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一般人看不到的背景。有时候,我们评价一个人很难准确,就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后面站着什么,他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背景对人的影响真是特别大。我是主要写背景的,不是写单个的人,我们单个的人都是在这个巨大的背景中生活。我们有时觉得一个人的举动很荒诞、很突然,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后面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我是想把背景写出来,我个人认为,这背景的力量是巨大的,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还要大。
记者:那你会不会担心,用过多笔墨写背景,会不会反而把人物给冲淡了。
李佩甫:我把所有的人物,都放到我最熟悉的环境里写。不然我怎么写?像美国纽约,我只是去过而已,只有那么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我不可能深入骨髓去写。只有把人物放到我熟悉的情境里,我写起来才得心应手。
记者:从你的作品里,还是能读到上帝视角。这可能是因为你在小说里融入了一点近似神性的东西。
李佩甫: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点神性的。
记者:都说现实充满魔幻色彩,你着重书写的权力就更有魔幻性了,但你的小说却似乎和魔幻现实主义沾不上边。
李佩甫: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很大啊,我刚读到《百年孤独》的时候是相当震惊的。拉美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也有相似性,在近现代都处于被奴役状态。他书里有些带魔幻色彩的细节,像拉磁铁,跟我们童年时候玩的推铁环就很相似。当然他的描写,什么钉子、铁锅跟着满街跑是夸张的。但拉美作家在有些思想意识上是超出中国作家的,他们能穿越历史,穿越具象。
04
“文学不是用来经营的,进入文学深处,你就无处可藏了。”
记者:还是回来说说平原。你小说里固然写到一些充满进取精神的活跃分子,但尤其不能忽略的是那些承受者的形象,这其中以女性为主。
李佩甫:我写的都是平原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平原上的老百姓只有忍和韧,也没什么革命性。我和陈忠实写的也不一样,因为历史状况不同,写的地域也不同,他写的八百里秦川,站在黄土高原上是可以大声喊出来的,但在河南这块土地上,很多东西都是得咽下去的,所以我是写隐忍的。这样的隐忍靠一口气来支撑,很苦啊。但用“忍”和“韧”这两个字来概括中原文化是最准确的。我有时候觉得,河南老百姓就像土地一样沉默,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他们就靠一口气,一代代存活了下来。
记者:你受益于大量阅读,但读你的小说,看不太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你像是一直都坚定地走中国化、本土化的写作路子。
李佩甫:我的写作没和西方对接,算是比较中国化吧,比有些作家更本土,更传统一点。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其他作家一样,都拼命吸收西方各种文学流派营养,也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那时,我可以说也吃了一肚子“洋面包”,感觉很胀,消化不了啊。所以在写作上特别迷茫,有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像狼一样在街头徘徊。那时,我已经知道文学不仅仅是写好一个故事了,搞好写作需要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表达和认知方式。但“洋面包”好吃,我却长了一个食草动物的胃,所以特别痛苦。
记者:尝试过西方化的写作吗?
李佩甫:我学着写过意识流作品,但怎么写都觉得不成功,也没好意思发出去。这跟我当时还没找到认知的方向有很大关系。我觉得,认知或者说创造性地透视一个特定的地域是需要时间的,不光需要时间,还需要认识。我说过一句话,时间是磨,认识是光。磨和光都有了之后,我才找到写作方向,也才有了《红蚂蚱,绿蚂蚱》。当然这也不是说我完全回归传统,才找到方向。实际上,一些现代派作品,像普鲁斯特、乔伊斯,还有克洛德·西蒙等作家的写作,我还是接受的,也是对我写作有影响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记者: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佩甫:他们小说语言里那种声光色味,描写细节的准确程度等等,对我有影响。当然我写出来的味道,还是平原的味道。所以,我不像一些作家那样去仿制。你那样仿制,在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会沾一点光,新锐编辑喜欢,但长期那样写就不行了。我是觉得我们不能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也没这个必要。我们得写自己的生活,得把根扎在自己的土壤上。你在自己的土壤上,对这个地方熟悉,你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味道,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感知到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也只有这些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是别人夺不走的,所以我觉得不能一味学西方。只有找到你自己的领地,写你最熟悉的东西,才能做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反之,你会捉襟见肘,很难远行。
记者:你的写作总体看挺真诚的,比较少私心杂念,也比较少条条框框。
李佩甫:你说我真诚,那是我把自己放进去,在写作中把我对土地的理解都放进去了。我觉得,作家情感的真诚度对作品质量有很大影响。文学不是用来经营的,虽然现在文学场有了些变化,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仍然是相对纯粹的。文字骗不了人,刚开始写的时候看不大出来,靠编造也能蒙混过关,但等到进入文学深处,你就无处可藏了。你的心性,你的小伎俩,都很容易被内行人一眼看出来。所以写作不能有偷工减料的心理,文字这东西一旦滑下去就很难再上来了,你得咬住、坚持住。
记者:读你们这一代作家的处女作,再对比后来的写作,回看你们蜕变成蝶的过程会很有意思。你熟读西方经典著作,写的却是中国化的小说,倒是觉得你适合来谈谈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话题。
李佩甫:我不知道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但我知道中国作家都想写出本民族所期待的,好的文学作品。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文本角度,如何突破旧有的文学样式?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一个困境。从内容角度,文学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应该是“麦田的守望者”,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我们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落后于时代。如果文学落后于时代,作家仅仅是描摹现实生活贩卖低劣商品的“故事员”,那么我们的写作是有问题的。

记者:但另一方面,网络化时代全民写作。至少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写作似乎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多元。
李佩甫:多元化是好事,全民写作也是好事。但文学创作不只是写一个故事,或者说写一种经历。文学创作也不是生活本身,作家只有用认识的眼光照亮生活、用悲悯的眼光认识生活,用独一无二的方式表达生活,在作品中加入意义的创造,融入自己的思想,才能成就真正的文学作品。文学一旦失去了应有的水准和品格,失去了应有的境界和探索精神,失去了文学语言应有的思辨性和想象力,结果必然是庸俗化的泛滥。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的先导,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谈“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