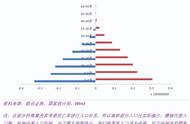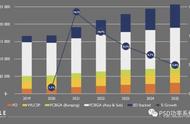人都喜欢听英雄戎马江湖的故事,但这不是一篇“讲古”罗大佑的文章。它想呈现(哪怕一点点)的是,63岁的罗大佑是什么样子。63岁的罗大佑刚刚出了新专辑,5月还将在上海、成都和广州三地巡演。

罗大佑接受专访。 澎湃新闻记者 薛松 图
1970年代的玉色琴心和1980年代的黑色剑胆,1990年代居香港一隅反思整个华人族群的命运,罗大佑抓住过时代的脉搏。
他想触摸到黄皮肤的集体宿命,想在历史的分分合合中找到不变处,想痛击荒谬和虚假,想保护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和血脉。
罗大佑的“古”确实精彩,那是过去数十年的华人共同记忆底色。
有整整一代人,罗大佑的歌常伴身边的时候是听不懂他的。这些歌与童年的和风细雨一起落入记忆深处,是当年大众文化里的异色。然而童年记忆影响一生,一旦记忆被唤醒,震动不可避免。
还有一代人,在懂事的年纪听他的歌。隐约觉得他的歌印证了什么,慨郁悲壮触动心底深处,原来和背过的诗词篇章与听过的民间传说精神相通。
但时间滑过,最后罗大佑湮灭成记忆里伸长脖子唱歌腔调古怪的中年人。《东方之珠》的主角是香港还是上海,《爱人同志》唱的是爱情吗?他们都忘了,但还记得如何哼唱“或许明日夕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恋曲1990》)。
罗大佑不是神秘主义的预言家,也不是冷眼洞察的小说家。他没有那么抽身冷静。他身上有旧时士大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愚顽和蛮勇,非要逼近问题的核心,然后用长句或短歌唱出来。
他唱歌的声音和姿态又怪异,常常把声音唱破,带哭腔,好像随时会哽住唱不下去,又有裂帛的飒然;唱歌时候前俯后仰地顿挫,台上的玩笑有时不好笑,关切又诚恳过头。
他说自己是孤僻的人。人前,他似乎不知道怎么充分表达自己,恨不得掏出心肺。但有时强烈的表达欲若不能抵达听众,则易感挫败而噤声。
某次听罗大佑的现场,他照例苦口婆心。说到一半突然觉得台下人没在认真听,一愣,一仰头抓起话筒立即开始唱。
罗大佑的本质是很古典的。关注国族命运和社会现实的人,到后来总会需要面对自己。上下求索,以超越生死。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任何一个单独的人类,都“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是我的一生”(《海上花》)。
但他没有自以为参透生死和时间,从此撒手赤足东南归。出走过几次,1980年代“扛不下去了”离台,辗转纽约、香港、上海、北京。“容易碰到很怪的状态”,都以探险的精神接受下来,还觉得有趣。

罗大佑北京演唱会
悲歌离歌写了好多首,即使梦中被悲歌惊醒,也仍能用仿佛新生儿般的惊讶目光注视种种现象。
就算罗大佑的情歌(数量还不少),也有凡人恋歌难以企及的旷远苍茫。“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不明白的是为何这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你的样子》)。当最基本的问题被生活掩盖,他问,听者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
同时罗大佑的音乐又是超前的。当然音乐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所谓的“先进”不是指音色或类型,而是适宜合时和永恒的灵光。
他的创作一直是曲先行,词的诞生极为缓慢,务求清晰达意。汲取过西洋老摇滚的养分,罗大佑和音乐伙伴们1980年代早期的编曲就远超同时代的华语作品。后来西洋音乐的编曲成为主流,罗大佑的音乐是很恰当的时代之声。
他又摸索出中文词曲嵌合的独特美感。他有这种功力,普通话歌、粤语歌、台语歌的曲式可以完全不同,以语言和文化背景为基础触摸音律的美和惊心动魄。又曾做过以同样的曲调配普通话、粤语和台语(《皇后大道东》和《原乡》就是这种尝试),类似古时同一支曲牌填不同的词,以此探索音乐和语言究竟有多宽广的空间。

罗大佑的老去是有路径是可循的。2017年他时隔13年的新专辑《家Ⅲ》好像突然变成温柔的老人家,而人人都留恋他激昂悲壮的年代和歌,忘记他早就唱过“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恋曲1990》)。
人都以为他老了,傲骨变柔肠,开始唱优美的疗愈之歌,教人如何在人世寻找幸福。其实只是透过时间,罗大佑发现留下的东西是美的。他(和林夕)把这句话送给所有人:“能返璞归真都因为情真/难返璞归真都因为情深/能返璞归真真的要感恩”(《Do Re Mi》)。
而作为讽世者的罗大佑依然存在,出现在《北西南风》《握手》《你准备要活两次》和《没有时间》。他仍在观察,血脉贲张,甚至《握手》的音乐都像《爱人同志》还魂。
但是,现在的罗大佑确定放弃了剖析时代脉搏的医生和异见者的身份。就像1980年代他不要做“抗议歌手”,和浪潮保持距离一样。他现在的歌只是表达“对生命的看法”。如果听起来觉得太平淡,过十年二十年再听试试。
和罗大佑聊了新专辑和这次的巡演(5.11上海、5.19成都、6.23广州),他对写方块字、电子音乐和网络新媒体的看法。还有“时间”,罗大佑始终没有搞明白时间,感叹“时间是神”,弹指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