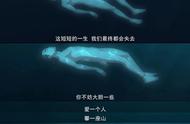《大鱼海棠》最开始的灵感来自于梁旋的一个梦,他梦到自己得到了一条鱼,小鱼不断地长大,最后他选择放大鱼归海。关于梁旋口中所说的“鱼”,有人觉得效仿了庄周梦蝶,是寻找“自由”的载体,是追求“无待”的人生。日本动画短片《让鱼告诉你怎么做》讲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男孩带一条鱼出门寻梦的故事,鱼告诉主人:我并不讨厌这里,但我想看一下外面的世界。男孩说,等你长得比海还大的时候,我就送你离开。

《大鱼海棠》在椿把鲲偷偷带回族内饲养的时候,也对鲲说过类似的话。可长大了,椿真的会放鲲离开吗?而族人又是否会放长大的椿鲲离开吗?这并不是观众所关注的问题,但其实“放行”的背后,还蕴含着一个原始部落的“个体自由”。
隐藏在《大鱼海棠》的客家文化--民族认同感自古以来,海洋文明崇尚自由,而农耕文明正如《天空之城》肯德亚山谷之歌所写的,根要扎在土壤里,与风一同生存,与竹子一同过冬,与鸟儿一同歌颂春天。无论你拥有多么惊人的武器,只要离开了土地就无法生存。
椿的“家族”也是在故土的信念中发展起来的,对家族的认同感和归顺是父母教给孩子的第一课,然而这种精神理念不单单存在少数人,而涵盖整个部落。
谈到原始部落,必然离不开喜欢田园风情的宫崎骏,在吉卜力工作室的众多作品中,更多的是对自然的赞美、对原始部落的留恋、对童真的歌颂。作为家的根基,部落带给了族人安全感和保障。可这种过度的保护又是否会扼*了个体的认知?
谈个体认知之前,我们先回到《大鱼海棠》的部落意识和部落存在。《大鱼海棠》中神所居住的“神之围楼”取景于福建的客家土楼,即福建省永定县的承启楼和南靖县田螺坑土楼群。历史上的“客家人”最早是集中在中原地区,后来受到战争和其他民族的侵扰经历了三次大型的“迁徙”。原为本地人的畲族子民,在被迫迁徙之后,命运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自古就有“主籍”和“客籍”之分,客是无法拥有土地的私有权,也不能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翻身。身为外族的“客家人”即使来到了一个新住所,短时间内也很难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围屋就是在抵御外侵、寻找自我这样的理念中诞生的,这种几乎完全密闭型的圆形或四角围屋,通过外在力量转化为内在动力,支撑了“客家人”在外地定居下来,并重新回归社会。
回归社会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得到了土地权,被社会认同了;另一种是主动走出来,并与其他部落民族和谐共处。影片只谈到了第一种,面对外族的态度,椿一家族还是习惯性躲,惹不起也可以躲得起。
福建客家的文化背景是《大鱼海棠》隐喻的那一部分,当观众得到这一层历史信息,族人一直警惕人类(外来物种)的心态就有了支撑点,整个故事变得也明朗起来。然而客家围屋只是代表“部落特色”的一部分,真正“原始”的一部分藏在影片的第一幕——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
在四十五亿年的世界里,地球只有一片海洋、一群古老的大鱼以及掌握人类灵魂和操控万物运行规律的“其他载体”,也就是椿的家族。所有年满16岁的孩子必须通过“海天之门”到达人类世界去完成他们的成年礼,这个“类自然”的任务无形中就暴露了这个家族的“原始使命”。

在《大鱼海棠》的世界观里,椿和族人的本体不是人也不是神,他们会面临死亡,但又不会真正地死去,这也印证了《逍遥游》中“生命不息”的说法,椿的奶奶最后变成了凤凰,爷爷成了海棠树。不会真正死去,其实也就是我们人类世界所理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然后“永生”的前提是没有入侵者,这也是为什么族人总在不停地强调远离人类。这片土地上,除了人类,不会再有给家族带来灾难的生物了。
鲲的存在促成了椿个体认知的觉醒--逍遥与拯救“人类存在”在影片中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象征了客家文化或者其他封闭部落文化对于外来者的警惕,即人与社会的关系;另一种陈述了人类对于自然界运行规律的干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前者促成了个人认知觉醒的机缘,后者则传递了道家“无为”的自然观和生死观。
椿是出生在自给自足的民族部落中,在这种高度警惕和排外的状况下,族人选择了“一刀切”的方式去阻断造成异变的可能。但成人礼却让很多三观尚未形成的少年少女们有机会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椿就是这群“年轻人”的代表。
影片中容易被忽视的是椿与鲲的这段相遇,在椿过往的认知里,神之围楼的话语权在高贵的长辈中,个体的认知是源于集体的认知。封闭的围屋和受限的人际关系,让椿对于“家族”出现了错误的归顺和认可。与鲲的这场相识,椿看到了亲情、看到了善意、也看到了温和。这跟以往所持有的理论知识发生了冲突,椿对人类开始有了好奇心,钻出水面看鲲和妹妹嬉闹也意味着她内心警惕的城墙逐渐在瓦解,真正将这面(偏见)的城墙拆毁是鲲救椿意外身亡了,这个以生命为代价的善意直接促成了椿独立意识的觉醒。这也是动画中个人认知与集体认知第一次出现了信息不匹配,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爸爸妈妈对孩子“说”了谎,孩子不再完全听从了,有了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