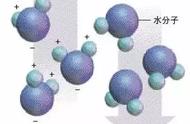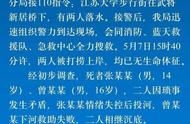作者:张越
那个戴眼镜的白胖子导演叫英达
1994年,那是一个春天。
我从北京师范学院(现在叫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在一个中专当老师。老师的工作和工资都喂不饱我,所以我兼职为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写喜剧、小品剧本,也在报纸杂志开逗趣儿的专栏。
一天,我高中同学贾乐松,当时该人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当编导,她对我说:
“我想从电视台离职。”
“为什么?”我很吃惊,那可是电视的鼎盛时期。谁舍得离开电视台呀!
贾乐松说:
“有个叫《我爱我家》的电视剧组,找我去给他们当切换导演,那电视剧特好玩儿。”
“再好玩儿拍个一年半载结束,剧组也就散了,中央台多稳定呀!”
“这我知道,”贾乐松又摆出上学时文艺女青年那副不顾死活的叛逆表情,“可是特好玩儿,我一看剧本就笑出猪一样的尖叫,我就想去干这个。”
“好玩儿”,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极高的价值标准。于是贾乐松就离开电视台,奔了《我爱我家》剧组玩儿去了。
又过了一阵子,贾乐松又找我:
“你能不能来一趟广播学院(即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跟我们导演见一面?”
于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招待所,我见到了那个戴眼镜的白胖子,唤作英达。一见这白胖汉子,我便心中一喜,这这这……这不是《围城》里的赵辛楣吗?须知《围城》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现在赵辛楣当导演了?那这个《我爱我家》还是很值得期待嘛!
遂与“赵辛楣”各据一床,盘腿而坐。听他聊美国一种叫“情景喜剧”的新鲜东西……那时候剧组通常都驻扎在一些便宜的单位招待所里,同志们在招待所标间的床上、地下各自盘腿打坐,开聊剧本,是创作的常见形态。
记得英达讲的是一个叫《我爱露西》的美国喜剧,大概就是一个胖胖的黑人妇女去不同的人家当保姆,遇到的各种好玩儿的故事。
“每集很短,但全剧很长,想拍多久拍多久。”导演说,“剧本一边写一边拍,现实生活中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随时写进去,跟做电视栏目似的,演员能从年轻演到年老,与观众互相陪伴、非常亲近的感觉。”
“那真新鲜。”我说。
“所以,我们要拍一个情景喜剧,你来参加写剧本吧。”导演发出邀约。
“啊……啊?我可不会写。”
“不会写怕什么?”导演很想得开,“反正谁都不会写,全中国也没人写过,试试呗。”
“可是我连电视剧都没写过,就会写小品。”
“所以我才找你呢,”导演说,“在电视台写小品的有个优点,快!固定栏目,每星期到点儿就播,剧本必须写好,不能拖活儿。我这儿现在边写边拍,剧本要得急,编剧忙不过来,所以需要找快手儿。我听人说你写剧本跟上厕所似的,蹲下扑通扑通,一会儿工夫就拉完了,站起来走了。”
我:“……”
后来我才了解这个剧组有句口号叫“宁伤交情不伤包袱”——说话必须有哏,为了哏伤了谁的面子都活该,不许生气。
暴走的编剧组负责人梁左
那天我跟导演要了几期已完稿的剧本,署名梁左,拿回家一看,我也笑出了猪叫声。兴奋得夜不能寐,索性不睡了,到第二天早晨写出了个上下集,叫《老傅病了》,后改名《真真假假》。就是老爷子为了刷存在感装病求关注,结果被医院误诊得了癌症,大受惊吓,留遗嘱,弄得全家人哭笑不得那个故事。
导演拿到本子,据说他也乐得睡不着觉。其实里面最好玩儿的段落,是老爷子吹嘘自己的伟大历程,如何与*、周总理并肩战斗,但吹得太厉害有点儿圆不回来……这场戏整个删掉没敢拍,怕被批评不尊重老干部,可惜了那些包袱。
这两期本子写完就算通过试用期可以正式上岗了。
“请你于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点,去红庙路边某某处对接编剧组负责人梁左。”我得到这个指令。
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接头方式,因为梁左老爸在《人民日报》工作,他家住红庙《人民日报》院儿里,所以每周定时在家门口马路边发活儿收本子。
那天,我到接头地点正赶上两个年轻编剧去交稿儿。好像他们拖期拖得厉害,已经到了马上要拍的时间点,他们的本子质量又不行。作为文学师的梁左应该十分焦虑,于是就暴走了,朝两个年轻编剧大声嚷嚷。我一看,当场就慌了,那时候的职场环境与现在不同,八十年代大学生很珍贵,尤其女大学生在单位通常都被领导同事照顾着,没挨过骂。面对这种有攻击性的激烈场面,完全不知所措,一句话不敢跟梁左说,扭头上了一辆公交车,去广院找导演辞职去了:
“导演,导演,我不参加了,你们的编剧太厉害,骂人。”
“他又没骂你。”
“万一他骂我呢?”
“有人耽误事儿他才骂的,你不耽误事儿,他骂你干吗?”
“那万一他骂我呢?”
“行吧,行吧,你进另外一个编剧组直接对接我吧。”导演勇挑重担。
具体来说就是有了两个编剧组,一组组长梁左负责差不多所有编剧,二组组长英达只管俩人儿,一个我一个梁欢。我的电视剧创作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每周一至周六导演在广院的棚里拍戏,周日回家休息一天。我就去他家谈出一期本子的构想,然后回家写稿。下周日再去他家交上周的本子领下周的构思。印象中他家住东城一个胡同的四合院儿里,我和导演在客厅聊剧本儿,宋丹丹在旁边儿炸饺子热菜,圆乎乎的小巴图在院儿里追跑打闹,时常要被提醒:
“巴图小点声儿,大人工作呢。”
有时英若诚老先生也过来聊聊天儿,逗逗趣儿。有一天他开心地显摆了一张卡:
“看见没有,这叫信用卡。有这个VISA的字样,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能用。”
我看得啧啧称奇,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VISA卡。
我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有一次,我们的工作节奏被打乱了。盛夏一个周四的中午,忽然接到英达导演的电话:
“写完了吗?”
我写得差不多了,还差两场,周日交稿毫无压力。忽然虚荣心大作:
“当然写完了,随时都能交稿。”
只听电话里说:“那你下楼来,我在你们家门口。”
我脑子嗡的一声,知道这回下不来台了,赶快救场:
“那个……门口太热,您去对门亚洲大酒店大堂,那儿有冷气,我两分钟就到。”
然后我拔了电话,关了寻呼机,趴床上就写,写得字要飞起。差不多一个钟头,赶完最后两场戏。
后来导演是这样愤怒控诉的:
“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电话也打不通了。我又不敢走,服务员都看我,这是被谁放了鸽子了?你们敢情都是小孩儿,无所谓,我好歹是一熟脸儿。”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把笔一扔,抓了稿子就往外跑。完全忘了由于天热,家里又没有空调,我穿着睡觉的粉背心儿绿裤衩儿,还在头上扎了二十来个横七竖八的小辫儿。按导演的说法就是:
“服务员都等着看我这儿等谁呢。嗨,敢情一精神病,还扎一脑袋小辫儿。”
后来我再也不敢说瞎话了。
偶尔,不用上班的时候,我也去广院现场看看拍戏。拍《我爱我家》是带几百个现场观众的,所有的笑声都是现场观众的真实反应。我就坐观众席跟大家一块儿傻乐,特高兴。
有一天又去看戏,远远就见墙根儿蹲着一人,穿着旧衣服,编俩麻花辫儿,脸蛋儿红扑扑的,还挽一包袱。仔细一看,这不是我的同学贾乐松吗:
“你不当导播改逃难的啦?”
原来该同志客串了一个不安分的小保姆,就是剧中那个与小桂竞聘上岗说一口河北话,四处拍马屁,挑拨离间,最后被淘汰的贾小兰。那口河北台词至今是我们同学之间的梗。
我进入这个剧组比较晚,承担的大部分是起承转合溜缝儿的工作。比如赵明明要离组,我就负责把她写走;蔡明要离组,我也负责把她送去海南;要回来,我就把她写回来。有一个故事我比较喜欢,因为英达是北大心理学系毕业的,一直对心理学念念不忘。我们就商量了一个心理诊所打广告写错地址,把病人都招到贾家来的桥段。不过我那时候真的不懂心理学,把心理疾病跟精神病混为一谈。后来王志文、林丛客串的心理病患怎么看都像精神分裂,这不科学,不过倒挺逗的。
《我爱我家》意外地成功。其后这拨儿人又做了好几部情景喜剧,我参与的有《临时家庭》《电脑之家》《候车大厅》等,还和梁欢一块儿写过一个哭哭啼啼的言情剧。哪个都未能再现《我爱我家》的辉煌。
1995年年底,我接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的邀请去当了主持人,就此改行。
20年后,一个叫郑猛的记者联系我,要求采访我20多年前的这段经历。还叫我去参加一个《我爱我家》播出20周年纪念会,说是《我爱我家》有一个全球影迷会,好几万人呢,大家都盼着20周年好好聚一聚。我没想到自己都快忘了的事儿,居然还有人记得。如约去了纪念会现场——鼓楼西剧场,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回来的影迷,以及影迷会会长凉油锅。他们差不多全是80后,是在这部剧的陪伴下长大的,在座的人几乎都会背台词儿,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说: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几百人一起铿锵:
“姆们、姆们、姆们……”
我真的惊了!
后来这样的纪念活动又搞过好几场,其中《三联生活周刊》的那一场,一个年轻女观众说:
“《我爱我家》我看过几百遍,但最后两集一直没看。只要不看,这个剧就没有结束,我心里就还有个惦记。”
我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在我短暂的编剧生涯中,第一次学着当编剧就碰到了英达,碰到了《我爱我家》,碰到这样一个剧组和这样一群观众,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张越)
来源: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