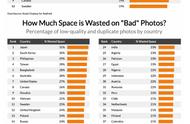那些拥有铂金包的上东区贵妇妈妈,也依然还是生活得充满焦虑。薇妮斯蒂向我解释说,上东区女性有一种“身体展示文化”,与好莱坞并无不同。
记者/孙若茜

薇妮斯蒂· 马丁
从街转角的超市出来,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晃着手里装着香蕉和牛奶的塑料袋,走在晌午空荡的人行道上。这时,一个独行的贵妇模样的女人笔直地向她走来。贵妇一直向自己的左侧靠,准备挡住薇妮斯蒂的去路,薇妮斯蒂则一次次地靠向右侧让路,眼看就要撞上几步以外的垃圾桶,但那个女人却继续向她冲来。她盯着薇妮斯蒂,双方对视时视线也丝毫没有离开,她故意用包撞向了薇妮斯蒂的左臂,并露出得意扬扬的笑,然后走掉了。薇妮斯蒂转身看着她离开的背影,不敢相信自己刚才遇到了什么,接着她意识到,自从搬入纽约曼哈顿上东区,她已经不止一次地遭到过这样的“攻击”了。
作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薇妮斯蒂开始留意这种特殊的社交行为,并把她的经历和观察都写在了《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原书名为Primates of Park Avenue,即《公园大道的灵长类动物》)一书里:在东七十九街,一天之内,她看到了近百起这样的冲撞。她一遍一遍地看着女人们差点儿相撞,看着一个女人“压”过另一个女人。当她花费了几周,累积足够多的观察后,她得出了第一个结论:上东区的女性,尤其是三十多岁以及正迈向老年的中年女性,她们对权力异常着迷。许多时候,都是年纪大的女性“攻击”年轻者。同时,她们的包包显然和这件事有关。
她发现,那些趾高气扬的女人,她们的肩上或是手上,都有一个“美到让人忘了呼吸,无论是做工还是染色都无可挑剔、价值连城”的包包。有的是蛇皮,有的是小羊皮,有的是鸵鸟皮,有的标识是双C,有的是F,有的是繁复的扣环。对于这些女人来说,一个好包就像是盔甲、武器或者旗帜。
这让她想起了黑猩猩迈克的传奇故事。1960年,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抵达坦桑尼亚的贡贝时,迈克还是一只新加入群体的年轻黑猩猩,它地位低下,遭到排挤,经常被年长、体型较大的黑猩猩欺负。突然有一天,迈克找到了几个被人丢弃的、有握柄的轻煤油桶。它手抓握柄,用桶敲击地面,然后像挥舞权杖一样,在草地上不断晃动它们。它站在黑猩猩们中间,把那些看起来非常神秘的煤油桶丢到一起,发出铿铿锵锵的恐怖声响。黑猩猩们立刻感受到了威吓,连它们的首领都害怕到发抖。即便贡贝的研究者后来很快收走了那些桶,猩猩们依然敬畏迈克,拥护他成为新任首领,统治部落整整五年。
薇妮斯蒂紧接着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她自己迫切地需要一个“煤油桶”,一个美国曼哈顿上东区版的“煤油桶”——一个爱马仕的铂金包。她相信这个在上东区地位最高的包会像个图腾一样帮她抵挡住来自其他女人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并不仅仅是马路上的身体冲撞。
当然,想要理解薇妮斯蒂需要“煤油桶”的迫切程度,也许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她的处境。她并不是为了人类学研究才搬到上东区的,因此,与这个地方保持客观的距离即便更有利于研究,也并不能令她自豪。她所需要的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她的目标是融入上东区的贵妇妈妈群体,因为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放学后连个玩伴都找不到。
在曼哈顿这个阶层分明的地方,阶层或许是隐形的,但它的确无处不在,令人焦虑。上东区更是有它自成一体的游戏规则,许多妈妈都是会帮自己的孩子安排玩伴的——他们只和有钱有势者的后代玩,以求往上爬。至于那些父母较为“低阶”的孩子,则想办法避开。反过来,在这里,孩子也是父母提高身份的方式。
在搬入上东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薇妮斯蒂把儿子送进教室,向其他站在走廊里的妈妈们打招呼,结果完全被她们视作空气,更别提为孩子找到玩伴,她发给儿子同学妈妈的短信和电子邮件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面对面的询问也几乎从来无法得到正面的答复。她将自己比喻成狒狒,在狒狒群体中,初来乍到的母狒狒地位最低。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她提到,在灵长类动物世界中,携尚未独立的后代转移到新群体的雌性个体是最脆弱的,加入另一个新的团体后,她们通常被压在阶级最底层,不是被当作可疑人士,就是被无视或*扰。
其实,在上东区几乎人人都是富翁,阶层之间的差别往往是存在于贵妇、有钱贵妇和超级有钱的贵妇之间的。薇妮斯蒂也并不是一个特例,她不是跻身富人行列的穷人,她新买的房子在上东区房价最昂贵的街道,孩子在念上东区最贵族的学校,他们出门时也有司机接送等等。问题也许是,她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里的游戏规则。
最初在上东区找房子时,她穿着马克·雅各布的衣服,一身时髦文青的打扮,结果被脖子上围着爱马仕围巾、全身上下都是高级品牌的对方中介问道:“你的老板今天会来吗?”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服装要升级了。在那里,卖方中介所穿的衣服要让外界知道他的客户有多尊贵,而买房中介的衣服则更要在气势上压倒卖方中介。要买房子的人,靠身上的衣服同时让买卖双方的中介知道他在认真看待这件事。
只有超级有钱的富太太可以随便穿,因为谁都知道她已经有钱到不必玩这一套,中介得穿上好的衣服巴结她。薇妮斯蒂形容,每一天,每一次看房,在每一间接待大厅都是一次服装大赛,而包包是重点中的重点。在她看房的第一天,四五间公寓的中介就几乎都拿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香奈儿包。她回到家,不得不半开玩笑地告诉先生:“如果想找到房子的话,我得先买一个新包包。”
房产中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贵妇妈妈们的世界。薇妮斯蒂观察到,上东区的女人除了会穿露露柠檬(Lululemon)的休闲装出现在学校接送区和游乐场,其他类型的打扮也都差不多,甚至撞衫、撞包。例如包包,大家都喜欢赛琳(Celine)、香奈儿、爱马仕,而华伦天奴的铆钉包就不会出现在上东区。在不下雨或没雪的月份,她们穿芭蕾平底鞋,浪凡(Lanvin)、香奈儿、珂洛艾伊(Chloe)特别受欢迎。如果是接送孩子的日子,又不需要匆忙赶到其他地方,那么浪凡以及伊莎贝尔·玛兰(Isabel Marant)的楔形鞋极受欢迎。下雨天,她们穿的一定是博柏利(Burberry)的风衣配五颜六色的璞琪(Pucci)雨靴或是香奈儿经典山茶花标识的雨鞋……
薇妮斯蒂向我解释说,由于种种原因,上东区有自己奇特的生态环境。在那里,对于女性气质还有着过于极端的要求。她把它称为“身体展示文化”,与好莱坞并无不同。而在一个非亲属也试图建立联系的社会背景下,“一致性”会作为一种捆绑策略。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一个地方度假,或者交换诸如最好的迪士尼指南以及找谁购买昂贵手表等信息——这些都是精英形成联系并令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
总之,在曼哈顿,也许不止曼哈顿,你所拥有的东西就是在告诉别人你属于哪个阶层,你有多少财富、人脉和力量,钱、关系和权势就是一切,你拿什么包,开什么车,就是在告诉别人你的身价。
铂金包就的的确确为薇妮斯蒂带来了曼哈顿人某种独特又扭曲的敬意。她说,曼哈顿是个奇妙的地方,它会把人心底的*暴露出来,你会看到*最真实的本质。凡是住在上东区的人,他们的*,他们的身份地位,都要看某几样稀有物品,看那些“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铂金包因此代表着很多意义——一个要价至少1万美元起跳的包包,居然要等人施恩,有时是要靠奉承、讨好店员才可以买到,而更多的时候,即便这样做也无济于事,你也许连排队买它的机会都没有。这种看似荒谬的过程,也是铂金包价值的一部分。它意味着即使富裕如上东区,也有诚心盼望、无止境的等待之后求而不可得的痛苦。曼哈顿女人想要铂金包的原因,也许正在于它的似乎触手可及,但又得花点力气。
薇妮斯蒂的一个专门研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英语系教授,曾经以美国小说家伊迪丝·华顿笔下的莉莉·巴特为例来解读曼哈顿女人为什么都想要铂金包。他认为,热爱流行商品的人,不只是女人,不只是某种社会阶层的女人,也不只是莉莉那一代的女人。问题在于,女性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女人在追逐昂贵的珍稀物品时,也是在重申自己的珍贵性,好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再次感受到她们的身份。
如果像薇妮斯蒂所说,铂金包对女人意味着最终极的身份地位,那么,能给女人铂金包的男人,连带也是最有权有势的人。曼哈顿临床心理学家史蒂芬妮·纽曼对铂金包的看法是:一个拥有铂金包的妻子,是自恋的成功男人绝佳的附属品。妻子有铂金包的男人,将得以证明自己有多厉害、多高人一等——他有能力给女人如此昂贵、如此稀有的物品。
但是,铂金包始终只是一个包包,或者一个符号。就像薇妮斯蒂最终融入上东区,靠的也并不是她费尽心力买到的铂金包一样,那些拥有铂金包的上东区贵妇妈妈,也依然还是生活得充满焦虑,其实,她们想方设法地买到一只铂金包,有时甚至可能恰恰是焦虑的表现。她告诉我,在上东区生活的女性,也清楚地知道她们的社区文化中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但她们被困其中。在那样的生态环境下,人们过分重视统一性与严苛的社会等级划分。绝大多数女性决定为之努力,并成为其中的“成功人士”。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太可怕了。因为在这样严格的等级社会中,孩子也将成为父母的延伸,父母希望他们进入名牌学校以提升自己的社会等级,他们的生活被过度安排,因此压力过大。虽然上东区的孩子长大成人后通常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地位,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最终,薇妮斯蒂一家搬离了上东区,选择生活在更加随和、友善,没有人会势利地为孩子挑选玩伴,不需要觉得自己的衣服丢人的上西区。到巴黎度假时,她为了一直发麻的手臂去看医生,时髦的巴黎医生坐在桌子后面,不只听清了她是个无法打字的作家,还看了看她穿的衣服,拎的包包。接着,他以法国人的口音重重强调,她的问题是背了太重的包包:“要不就选铂金包,要不就选写作,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