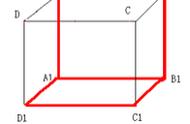文|江徐
想来苏东坡是个失眠多梦的人,而且有记梦的习惯。他晚年在海南,编撰了一部杂文集,其中有一辑,写的全是梦寐。
梦是对日常生活的炒冷饭,有时略微添油加醋。怎样的人,就会做怎样的梦。心中存有何种渴望,便有坠入何种梦境。苏东坡的梦中世界,是他白天行止的倒影,赋诗,饮酒,品茗,南来北往地走在路上。
有一天,他梦见老朋友参寥法师带着诗卷登门拜访。两人喝茶,品诗,一如往常。醒来追忆,他记得有这样两句:“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他在梦中还问法师,为何过了寒食清明,连泉水都是新的了?法师告诉他,很多地方,有清明淘井的习俗。
我想起乡下很多人家有井,但从未看到,也从未听说清明前后谁家请人来淘井。
一口井,一打好,一劳永逸地用下去,岁岁年年,生生死死。
外婆与兰侯家交界处有一口井,当初两家合打。我有一张童年照,倚井而立,井到人的胸高。冬天,身上的棉袄又厚又硬,双臂向外支开。背后是乡间泥路,行道树兴许是新栽的,稀稀拉拉,瘦骨伶仃。稍远处,田野,房屋,看起来同样光秃秃,模糊的黑白色调更显其荒凉。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一辆自行车正好经过,后座还驮着个人,大概“从街上回来”。
舅舅年轻时候对画画、摄影很感兴趣,几年后,同样的位置,同样是冬天,舅舅又给我拍了张照片,这次照片变成彩色的了。小人儿身着粉色衣裳,头扎粉色绸带,身后,白墙黑瓦红对联,大概是新年期间吧。
虽然有井,夏天淘米洗菜汰衣裳还是去河边,小姨走在前面,我捧着一只米箕,跟在后面。那时,农村还没安装自来水管,逢到落雨天,大人就会取出木盆水桶,排在檐下,等雨。他们不说“雨”,而是说“天雨”。“囤点天雨”。
大雨停歇,井水浑浊。但很快,它自会澄清如常。

我对这口井最深的记忆集中在童年的夏天。用网袋兜一瓶啤酒、一只西瓜,吊上半天。傍晚捞上来,酒瓶刚擦干,立马全声冒“汗”。再擦干,又一身“汗”。一瓶酒,正好够外公外婆每人一碗,启瓶时的泡沫归我享用。将泡沫嘬完,用筷子飞快搅拌,以便“生”出更多泡沫。
外公把啤酒瓶盖一只只收集起来,扣嵌在檐下,整整齐齐,像瓶盖方正队伍。——这样可以防泥土被雨水冲刷。一个夏天过去,两个夏天过去,这队伍也没有如我暗自期待中那样壮大。
捞出来的西瓜自然也是全身冒“汗”。一刀切开,那爽脆的声响……再一口咬下去,那沁人心脾的冰凉……不知该如何形容。后来读到汪曾祺先生的相关描述,觉得再贴切不过:“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岂止眼睛,连身边的空气都变凉了。
井水体贴人,夏天冰凉晶沁,冬天,洗衣、洗菜时虽然说不上多么暖和,可那份柔和的微温足以给人慰藉。
渐渐的,那口井在时代的变迁中被弃用了。前几年开始,偶尔回去,发现井内壁长出一圈蕨类植物。老邻居兰侯一直在住那儿,但已经看不到她到井边洗衣、淘米,总归是嫌脏,嫌麻烦。
每次回去,我都会趴在井沿望一望。从来没有淘洗过,倒也不浑。有一次望下去,映出一小块湛蓝的天,像遥远的镜中风日。

今年十一回去,小住几日,早上用井水汰衣裳 ,井水触在皮肤上,和小时候一样凉快,只是水面漂着枝叶碎屑,掸不了,有点恼人。井内壁的蕨类越发丰茂,绿幽幽的。
舅舅早就不画画,迷上了钓鱼、拍短视频。那天舅舅又去拍井,这一次他让我配合着,他拍井,我拍井。钓桶放在井沿,水滴淋漓。我想拍出井水一滴一滴,慢慢滴落下去,声音与水滴被放大的那种特写镜头,可是不能。
前几天,睡前读到谢灵运的一句“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一念忽闪而过——如果,将这两句转化成梦中的场景……常常做梦,知道梦境是将潜意识场景化的过程。可是,梦怎么可能就如此轻易听从我的安排……所以,只一念闪过。
那天照样做梦,梦里在赶路,夜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夜。慌张害怕中,我忽然听到一种声响,凝神辨认,是水滴声,嘀——嗒。过了一小会儿,又一传来一声,嘀——嗒。一声一声,明晰,清澈,抚慰孤单的流浪者。
醒来后反刍梦境,咀嚼那水滴声,依然感到焦躁不安的心灵像是服了一剂清凉散。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之后某一刻,我终于回过味来,那不正是放大、放慢的井水滴落的声音么?

【作者简介:江徐,80后女子,十点读书签约作者。煮字疗饥,借笔画心。已出版《李清照:酒意诗情谁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