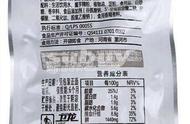手语里的“我爱你”酷似摇滚的手势,仿佛将一切的温柔握在手心里,每每看到都觉得心头暖呼呼的。
“长长的路的尽头是一片满是星星的夜空。”听着陈绮贞的《华丽冒险》,我坐在公交车上,往家的反方向缓缓驶去。
长途巴士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成为我最爱的交通工具之一,它有着一股陈旧的味道,还有365天都运作的倔脾气。
穿梭在城市偏僻的街巷与紧凑的高速公路上,巴士仿佛贯彻着一种平淡而充实的生活气息,每个座位都预留几分遐想。
坐在靠后的位子,我看见前排的上班族拥着书包酣睡的模样,看见怕生的小孩用好奇且有戒备的眼神看周边想逗他笑的大人,也看见带着耳机的人对窗外放空仿佛被不停切换的风景狠狠甩进回忆里的某个片段,无处可躲。
而他坐在寂静与喧哗间,腼腆的笑着。耳朵上挂着的助听器现在垂在肩上,他熟练地用手语与身旁的人交谈,豪不在意别人对他投以异样的眼光,那都是太伤人的关切。和煦的阳光照在他脸上,没有任何的不堪或难受,只是静静享受原本就属于他的天生安宁。
我把视线挪开,为自己过于炙热的凝视感到羞愧。大二加入大学福利社开始定期为聋人服务(WSC Regular Service for Deaf Community)后,就理解直盯别人用手语交谈是个大禁忌,等同于躲在角落偷听别人说话一般的不敬。但也许按捺不住好奇心的怂恿,我还是时不时用余光偷窥他们两人的互动,想起自己在社团里的活动。
一开始为失聪小孩补习时,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担心自己笨拙的手语无法表达内心的想法,又害怕自己过于小心翼翼反而适得其反。所以当那个四年级小女孩用她调皮的眼神望着我时,我故作镇定朝她笑了笑,安然度过第一天。
接下来的每个星期,她的情况时好时坏,脾气来的时候无论谁也劝不住,噘起嘴仿佛全世界都令她感到委屈,我也只能无奈地随她而去。后来才明白,助听器里的杂声过大,会使他们容易感到烦躁,造成心情起伏不定。
然而,我教的小孩是幸运的,还能通过助听器学习每个字的发音。那些先天性耳聋的小孩却面临种种问题。听觉与语言能力紧紧相扣,儿童时期我们无意识复制大人们口中的单字,迷迷糊糊说出令人雀跃的“爸爸”与“妈妈”,再慢慢累积更多单字,组成完整的句子。
机缘巧合下,去年社团请来一位母亲与我们分享她自身的经验,她说目前的学前教育并不适合这些小孩,以至于他们上了小学后,语言能力严重落后其他同年龄的小孩。说起这个话题时,激动之余却是更深沉的无奈。
“我希望有一天,聋人也能被正常的看待,像是我和你都是不同的人。仅此而已。”她把这句话抛在那狭小的空间里,看似无意的一句话,没有人能预料它会扎根在谁的心上,肆意膨胀成一股无可反击的动力。
就在今年,我的朋友开始一个名为Sign2us的活动,在社交媒体上上传关于手语的短片,希望让更多人理解聋人的世界。这是第一步,渺小而坚定。
手语里的“我爱你”酷似摇滚的手势,仿佛将一切的温柔握在手心里,每每看到都觉得心头暖呼呼的。
那男孩与朋友下了车,巴士转进一条人烟稀少的工业区,而车上的乘客也收起他们的视线。空调寒冷的风沁进手心,我搓了搓手,再换到靠窗的位置。太阳不温不热洒进巴士内,乘客们依旧各顾各的。
或许他只是短暂的片段注定会被人遗忘,也或许这一幕也种在某个乘客的心里静静膨胀。但这也无所谓,有些路必须走,而漫漫长路我们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