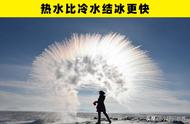黄荣明的胸口藏着秘密。
他时常生病,不敢运动,走路都会大喘,动辄全身乌紫。为了藏住秘密,即使在南方潮热的夏季,也要穿两层T恤,遮住胸膛正中的凸起。那里是怦怦搏动的一团心脏,蜷在一层纤薄的皮肤下,脆弱而又危险,带给他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病痛,还有死亡的威胁,以及如影随形的自卑。
这个秘密黄荣明揣了25年,2012年,为了筹钱治病,他将这颗罕见的心脏暴露在镜头前。
社会各界的捐款源源不断汇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医生们费了许多力气,最终为这颗畸形的心脏矫治,将它安置回胸腔,并填补好缺损的胸骨。
黄荣明终于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跑步、骑车、大口吸气。直到2022年,胸口的皮肤突然感染、化脓、溃烂,露出几个红黑色的孔洞。他不得不回到10年前手术的医院,找到曾经的医生,着手筹措又一轮医药费。
一场新的救治开始了。

2012年以前,黄荣明的心脏在胸腔中间,肉眼可以看到心脏的律动。受访者供图
外露的心脏
4月的一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孙家明照例开诊。眼前的年轻人白净、瘦削,他只觉得眼熟,直到那人撩起衣服,露出微鼓的前胸,皮肤下隐约可见一块长十三四厘米、宽八九厘米的矩形板子。
“你是那个心脏外露的孩子。”孙家明一下记了起来。
2012年年初,这个叫黄荣明的年轻人就曾来医院就诊。这是十分罕见的病症——本该长在左侧的心脏长在胸骨正中下处,只盖了一层皮肤,胸骨和两边的肋骨缺损,肉眼就能看见心脏怦怦跳动,甚至可以看到器官的轮廓。医生们将它诊断为先天性心脏外露,他们记得,那时医院心外科已成立30多年,仅收治过两例,其中一例还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黄荣明能活到25岁,已经是奇迹。
对于黄荣明和家人来说,这个奇迹是由9000多个谨慎而忧虑的日夜构成的。
母亲张元凤第一眼看到黄荣明时,只记得儿子“一头黑发,脸蛋真漂亮”,但她很快就注意到了异样——透过婴儿胸腔薄薄的皮肤,能看到一处黑色的血块不停地蹦。
亲戚朋友赶来恭喜她生子,她不敢讲出实情。“别人生的孩子都十全十美,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一两年过去,村里人才慢慢知晓黄荣明的情况。

2020年左右,黄荣明(左)与妹妹在广东。受访者供图
照顾这样的孩子,张元凤和丈夫必须格外精心。洗澡时用毛巾沾水,轻轻擦拭;做家务时把他放在木制的椅架上,以免撞倒;睡觉时总是起床查看,生怕儿子的心脏在无意中被压住。他们常叮嘱他多穿点衣服,走路时手里不要拿东西,千万不要撞上硬物。
从记事起,心脏就成了黄荣明的负担。
他必须慢慢挪步,偶尔跟朋友去河边翻翻螃蟹、捕捕小虾,也只能在途中被远远落在后面。他几乎无法吃猪油和鱼肉,身体消受不了,会喘得厉害。
为了生存,他养成了许多习惯——从不趴着睡觉;预感到危险,就立刻用手捂着心脏;尽量仰着摔倒,实在要面部朝地倒下,就赶忙用手撑住地面,但摔下的一瞬间,还是感到恐惧。与外露的心脏相伴的25年,这些已经成了本能。
艰难地长大
因为这颗异样的心脏,黄荣明直到9岁才上学。三四公里的上学路,母亲背着他,一走就是五六年。
那时的张元凤十分瘦弱,身高1米6左右,体重只有90多斤。半个多小时的山路,一天走上4个来回,对她来说,“就像拉练一样。”
他们常常早上六七点就要出发,走到一半,身后就会有一群群的学生赶超上来,看到小伙伴蹦蹦跳跳去上学,黄荣明多少有些羡慕。
张元凤也很羡慕。她身体并不好,有时累得喘不过气,两腿直往下坠,因此路上大部分时间,他们是沉默的。
她偷偷哭了很多次,一次实在受不了了,就把背上的黄荣明放到地上哭,可看到孩子,她的心又软下来:“孩子怪可怜的,我们只能慢慢把生活过下去。”
父母的辛苦,黄荣明都看在眼里。
天气实在太差,他会待在家里不去上学;有时母亲来不及接他,他就自己一点点蹭下坡。好心的高年级同学看到,也会背他走上一段。五年级即将结束,一向好脾气的他强烈要求不再上初中。
父亲黄保江还记得那天,妻子准备送黄荣明上学,儿子躲着不肯出来。“家离初中六七里路,你们受罪,我不上算了。”黄保江很生气:“将来你自己后悔。”他听见儿子信誓旦旦地说:“我不后悔,现在我自己走路都困难。”
可黄荣明舍不得学校。他喜欢和同学在课间捉迷藏、翻花绳、抓石子,喜欢同学向他请教数学——这是他学得最好的科目。他感激同学们对他的照顾,感激老师们从不惩罚他的调皮,尽管他并不愿意被区别对待,但他始终记得这份关照。
辍学后,黄荣明再没回过学校。他学着父母的样子照顾刚出生的弟弟,做些轻松、简单的家务,偶尔也会翻翻以前的课本,温习学过的知识。

今年手术结束后,黄荣明回家休养,有时也会做做饭。受访者供图
2008年,21岁的黄荣明已经习惯了这颗心脏,可张元凤的身体却差了起来。她常常感到疲惫,头晕,患上了糖尿病。
母亲治病,弟妹读书都需要钱,村里又总有人议论他,在小姨的陪伴下,黄荣明坐上硬座火车,一手捂着心脏、一手提着背包到了佛山,去舅舅开的小卖部打零工。后来,他又陆续托老乡在佛山和东莞的鞋厂找了几份工。
在鞋厂工作并不轻松,考虑到心脏,他只能在流水线上轮值,刷胶、折边、组装,从早上8点工作到深夜,有时还会加班到凌晨,一个月只有一天公休,鼻腔里全是皮革混着胶水的气味,口罩也挡不住。
休息时,他就躺在床上,琢磨怎么学门技术,多赚点钱,但很快就被身体否决了。“挣钱不容易,我只能在流水线上工作,无论做多久,都是一个月800元。”黄荣明很无奈。
但好歹,他能养活自己,也能孝敬父母了。赚到的第一笔工资,他大多数汇回了家里,这往后成了一种惯例。打电话时,他听到了父母的哭声。
“他很不容易。本以为他能养活自己就行,没想到他还想着我们。”黄保江说。
独自在外打工,除了信得过的老乡,连朝夕相处的工友都不知道他的病情。黄荣明把自己的心隐藏得很好。他从不当着大家的面换衣服;冲凉时要么第一个去,要么拖到最后;即使到了夏天,他也坚持套两层T恤;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却还是主动提出分手。
他怕别人看见自己一跳一跳的器官,受不了异样的眼光。2011年年底,黄荣明回到家里,郑重地和父母提出要治疗。“年龄越大,心理压力就越大,做什么都自卑,以后可怎么办?”
求生
过去的20多年,黄荣明见过许多医生,但那时医疗水平不高,难以治疗。
黄荣明读小学一年级时,亲戚曾寄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心脏外露手术成功的新闻。黄荣明的父母觉得有希望,便将情况写在信里寄去医院。不久,他们收到了医生的两封回信。对方邀请他们去上海检查,但告诉他们至少要准备两三万元。
为了筹钱,张元凤背着儿子走了12所学校,希望能帮忙组织捐款,忙了一个多星期,一分钱也没筹到。治疗的计划只能中止。
2012年年初,黄荣明再次求医。但二三十万的治疗费,对在河南农村务农的一家来说,无疑是巨资。这次,他将自己藏了25年的“缺陷”暴露在媒体的镜头前,向大众讲述自己的经历,以求得社会捐助。
捐款源源不断汇来,100元、500元、1万、15万……爱心人士们一点点帮黄荣明凑齐了手术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医生发现,除了心脏外露,黄荣明还有严重的心脏病——右室双出口、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造成他始终缺氧,一旦保护不当,很可能心脏破裂,危及生命。
为此,医院前后共组织三次大型会诊,全院上下包括心外科、整形科、麻醉科、超声科、肝胆外科等五个学科共同参与讨论,制定手术方案——先麻醉开胸、纠正心脏畸形,再将心脏移回胸腔,最后进行胸壁缺损修补和胸廓重建,使黄荣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