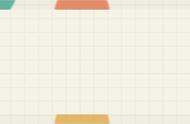不久前腌制了一坛青萝卜。十几日后,拿出来切成丝,在清水中浸泡半个小时,之后沏干水,加点青红椒丝,放点味精,调点香油,一尝,清脆可口,咸淡适宜,让人进食*大增。于是便将这款自己亲手制作的“美食”推荐给孩子,可谁承想人家吃了一口遍悉数吐出,“又咸又涩,有什么好吃的?!”
一瓢凉水浇在头上。难道我们长着不同的味蕾,心里有些气不忿地暗想,“你们这些‘甜奶系’的人有本事不吃咸!”
我腌制的咸菜俗称“咸菜疙瘩”,原料不外乎萝卜或芥菜,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民间传统“硬菜”。从小到大,我对它的喜欢从未改变,可以一日无肉,可以一日无酸辣甜,但只要有它,吃饭就会香。对咸菜疙瘩情有独钟,不仅仅是因为饮食习惯上的偏好,更是源自对儿时清贫岁月一份难以释怀的永恒记忆。一定意义上讲,在我心中,它是标识那段岁月的一个特有的甚至是图腾式的符号。
儿时记忆中,大多数老百姓都家境贫寒,吃饱穿暖就是生活中的大事,想吃好点、穿好点实在是难上加难。特别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吃穿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那时的农村,绝少大棚蔬菜这个概念,冬日里能吃的蔬菜基本是储藏在地窖里的大白菜和萝卜。对于家家户户来说,还有应对冬天吃饭问题的一件“法宝”———咸菜缸。
依稀记得,六七岁时,父亲买了两口高过我头的大缸,一口盛水,一口则腌咸菜用。当时,母亲腌好咸菜后,把我拉到大缸的跟前郑重告诉我,这缸里腌的是咸菜疙瘩,腌好的咸菜可以吃好几年,所以平时千万不要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往里面放,要不会把可以吃好几年的咸菜给毁了。
看到母亲严肃的表情,我明白这个咸菜缸是不能随便碰的。后来,我还记得母亲为了加深教育,专门给我讲了老姥姥家“咸菜王”的故事。她说,老姥姥家里人口多,咸菜缸里腌了很多咸菜,其中里面专门腌制着一个巨大的萝卜,是“镇缸之王”,除了老姥姥之外,谁都不能动它,但是有一天,她的一个儿子擅自掰了一小块偷吃了,结果被老姥姥知道后狠狠打了一顿,棍子都打折了。
母亲讲的“咸菜王”的故事,让幼小的我对咸菜缸有了一层神圣感,每次看到母亲往咸菜缸里放萝卜的时候,我都在一旁好好地端量着,看看哪个大萝卜像我们家的“咸菜王”。我非常爱吃母亲做的咸菜,特别是每次母亲蒸窝窝头时,切好一大瓷碗咸菜疙瘩,放上些红辣椒,挖一勺猪油在里面,等饭熟了,一掀开锅,哇,熟透的咸菜香扑鼻而来,顿时让我垂涎三尺。
这种让我百吃不厌的咸菜疙瘩一直吃到上高中。
虽然上高中时生活质量好了些,但咸菜依然是我们很多学生的“主菜”。因为住校的原因,母亲每次都给我带上一大罐头瓶用猪油蒸好的咸菜疙瘩,正好够一个星期吃的。当时,有生活条件稍好的同学带的咸菜是伴着肉丝炒的,我们一些馋的受不了的同学,便在吃饭时打着聊天的幌子,吃上几筷子人家带来的咸菜解解馋,让人无可奈何。
现在想起那时的情形,有些酸涩,但当时就是那种艰苦的生活状态。
那时,因为贫穷,咸菜缸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而吃啥啥腻的现在,大咸菜缸恐怕在每个家庭里是很少见了,有的恐怕也就是个腌不了多少咸菜的小坛子,并且曾经作为主菜的咸菜也成了调剂饭菜的附属品,再也成不了饭桌上的“主角”。
喜欢吃甜、油炸和外来食品的孩子,感受不到我对咸菜疙瘩的深厚感情,但是让他懂得珍惜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珍惜每一粒粮食,实在很有必要;在生活中,对每个人来说,拒绝铺张浪费更应大力提倡。
人,要对我们劳动所得的粮食心存敬畏之心,要知道咸菜疙瘩也可以养活一代人。(2014年12月19日《烟台日报》作者杨新刚)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我要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