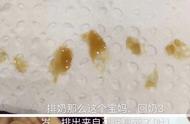拙文献给年过半百的70后。
--叽哩咕噜的鸭子
青春痘
(一)
应该是1988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大召乡通往小吉乡唯一一条公路上没什么人,一眼望去,路的尽头向右弯曲,满眼又被青纱帐那枯燥的绿色盖住,沉闷而单调。
天气闷热难耐,几声蝉鸣也是有气无力,叫两声就歇歇。胡图仁低头丧气地骑着车。这辆“永久牌”自行车是上初一的时候妈妈卖了两大包棉花给他买的,可以说是倾尽全力购买,除了家里的缝纫机,这辆车是最值钱的物件。自行车也和胡图仁一样没精打采,链盒没有了,曾经清脆的响铃也没有了,整个车子发出节奏性的“塔拉”、“塔拉”的声音,回响在闷热的空气里。
自行车穿过焦枝铁路大召营道口,来到孟姜女河桥上。他停下来,一只脚踏地,另一只脚仍踏在脚踏板上,熟练地从绿军装的口袋里抽出一根烟,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火柴点着,吐出的浓烟飘向河岸。
这时,河边走出刚给玉米撒过化肥的一对老夫妇,男的肩扛锄头,老伴手里拎着空化肥袋子,肩膀上、头上落满了玉米的花粉。蒸笼一般的青纱帐让老两口的衣服湿透,有的地方已经干了,呈现出青一块黑一块的难看的色调。走过胡图仁的身边,盯着他看,脸上好像写着“鄙视”。
这也难怪,胡图仁十三四岁的样子,乱蓬蓬、微卷的头发弄了个中分,苍白的一张瘦脸上长满粉红色的青春痘,光着身子穿了一件迪卡绿军装,只扣了一个扣子,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脯,下身穿一件蓝色的迪卡大档裤,麻杆一样的腿和没肉的屁股藏在宽大的裤裤管里,都不知道屁股在什么地方。周围长出黑黑茸毛的嘴唇单薄而苍白,满不在乎地张着,表现出标准的无知和迷茫。但这张嘴抽烟很老练,深吸一口,还会从略微带点鹰钩的鼻子里分批次喷出。
“这都成啥了,恁大一点的小孩就学会吸烟了。要是咱哩孩我一脚就把他跺河里了!”老汉对老伴说着,声音很大,胡图仁想不听到都很难。
要在平时,胆小腼腆的胡图仁会马上把烟扔了。他也知道现在他这个年龄抽烟,不管哪个大人训斥或打他一顿都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他身边的大人都是抽旱烟袋,很少有人买得起烟卷,除非是个别“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一个小屁孩抽着烟卷,相当于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要成为一个混混,来打我呀”这么让人讨厌。但今天胡图仁像没有听到一样,还是在认真地抽。看着桥下齐腰深的河水出神。一群白条游过来,裸露着黑黑的脊背。它们也没有引起胡图仁的兴趣,反而眉头皱了起来。
这条河在学校和村子之间,两边都是相距3里地。胡图仁觉得三年来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条叫做孟姜女的河,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不知道。从哪里流来,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也没有想过。后来他知道孟姜女哭倒过长城,便天真地认为此河是一条伤心之河,是从长城脚下流到这里的,他逢人便说喝过孟姜女的眼泪。殊不知各地都有孟姜女的传说,而太行南麓,黄河北岸这块地方没有长城,就好像院墙不会砌在院子中间一样。只好把以前的认知羞涩地藏起来,不敢再胡说。
从初二他开始逃学,慢慢地上了瘾,老师家长两头哄。每天早上出门,喊一声“妈,我走了哦。”妈妈老是那一句话:“好好学,给我争口气!”每次听这句话他就很内疚,但自行车一出村北的那个变电所,看见钟慧峰和史菲铭俩人已经叼着烟卷等者,所有愧疚好似远处太行山上的白云飘到了天边。三人弯腰弓背,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大撒把飙车。不约而同地把车放到孟姜女河桥洞旁边的机井房里,简单商量一下就撒开了花玩起来。
钟慧峰每天到河边的程序不变。只见他先解下腰间常带的一把剔骨钢刀,先做100多下俯卧撑。热过身就脱掉上衣,露出发达的胸肌,像电视上的健美运动员一样一下一下用力,让那两块鼓鼓的肌肉一动一动的,自己先欣赏一番。这时胡图仁就会走上前去,抚摸那个部位,做敬佩状,夸奖一番。然后钟慧峰要把自创的武术套路打一遍,再用胳膊猛击河边的一棵柳树1000下。久而久之,这棵柳树相比旁边的树要赢弱的多,看来什么经常挨打都长不好,树也一样。把这些活动做完以后,他走到河北边30米处的铁道旁,耐心地等着,若有一辆火车开来,此君就会大叫着和火车并肩狂奔,说要和火车赛跑,增强体质,这让胡图仁和史菲铭很是费解。但因惧其体魄,害怕遭其无故殴打,也要在钟慧峰和火车赛完跑之后连连夸奖才能过关。
史菲铭和胡图仁则没什么目的,只是玩,主要是想办法找吃的。夏天就沿着河往西走,最远走到获嘉,为什么不往东走,谁也不知道,只是向西走。胡图仁走在河的南岸,史菲铭在北岸,钟慧峰在河里趟着水。河里水草丛生,不仅会有鱼虾鳖等物,还会有蚂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钻到身上,半截黑细的身子蠕动令人恶心河恐怖,两个胆小的坚决不下,只有钟慧峰担当此任。河边杂草弥漫,也是有些阴森可怕。那个时候附近鲜有工厂,只有农业,河水还算清澈,除了庄稼就是树和草,走得远了人迹罕见,四处静悄悄的,偶尔会听到火车的轰鸣,别的什么声音也没有。三个人一直向西走,好像是野兽巡视领地。
三人各持一根木棍,河两岸的人若在草从中发现青蛙或蛇,就用棍驱逐,大部分时候它们会跳或爬到河里,想在水里隐藏。这时钟慧峰早已手持木棍等在那里,刚一入水便遭到迎头一击,不死即瘫。钟慧峰操刀,是青蛙则只留其腿,去皮后放到身后的布袋中;若是蛇便会费些功夫,先去头,挂在树上,整皮剥下,除去长在一侧黑黑的内脏,只剩下一段红肉,也放到布袋中。奇怪的是,若把这段红肉放在河水里,仍会游动,经常令三人迷惑不解。
一般不到获嘉县便收获颇丰,蛙腿蛇肉加上一些鱼虾,可以生火备膳了。史菲铭解下腰间的一个小包,拿出油盐酱醋等物,再把一个铝制饭盒放到三个石头上,胡图仁拾柴生火,就这样煎炒烹炸开始了。吃完了一抹嘴,看看西边日头的方位,三人就各自回家了。
回家后还说一说今天学校怎么怎么样的一大堆瞎话。冬天难熬,便在学校旁边村子里四处游逛,趁人不备,用砖头砍翻一只鸡,后来三人干脆配合着到农家院里鸡笼里偷只鸡,一路狂奔到河边。简单去毛后用泥巴糊了,放在火上烤。往往由于盐没有浸透,鸡肉虽然紧实鲜嫩,但吃几口就索然无味,没有河里的水产美味。多年以后胡图仁才知道这种做法叫“叫花鸡”,新乡市胖东来生活广场就有卖的,和那个时候自己做的一模一样。
初二那年的夏天,一次他们三人在河边巡视。红红的大太阳已经西下,远远看去,好像是落在了大召乡唐马村一样。周围的云彩被熏染得通红,折射出油彩一样的色彩。夕阳挣扎着透过云层,过滤之后的红光射出来,把河水、树木、庄稼染得想撒了一层血一样,三个人互相看看,每个人也是红彤彤的,特别是钟慧峰咧嘴一笑,连牙齿都是红的,面目狰狞。看见奇异的天象,胡图仁胆小,就提出今天要不就算了,回家吧。钟慧峰一扬手中的棍子,胡图仁便不敢吭气了,继续走。走到平时大快朵颐的那个地方,三人还是一无所获,正纳罕时,河北岸的史菲铭一声惊呼,手中木棍胡乱挥舞,好像是见鬼了一样。
“咋胡个球!”钟慧峰也有些忐忑。
“那是啥?是条长虫吧?还是两条!”河南岸的胡图仁指着钟慧峰身边的河水叫了起来。
钟慧峰顺着胡图仁指的方向一看,敢跟火车赛跑的他也愣住了。只见两条长虫向他游过来,这两条和以前见过的花蛇基本一样,但仔细一看还是有明显不同。只见一只质绿而黑环,另一条白环,主要是个头吓人,以前看到的不到一米,但这两条其中一条足有铁钎把那么粗、那么长,另一条小一点,但也远远超过了以前看到过的。这个地方头枕太行,脚踏黄河,是地地道道的中原地区,蛇类无毒,三人也没见过蟒,只是听说过。但这两条是什么东西?实际情况是,在我们叙述这么老多的话的时候,那两条长虫已经游到了钟慧峰的身边,奇异的红光照在两条巨蛇的身上,显得极其诡异。
关键时刻还是要看钟慧峰的,只见他嘴里“呀、呀、呀呼嗨”乱叫着,舞动木棍劈头盖脸朝两条长虫打去。随着他的木棍舞动,河水泛起浪花,水质也污浊起来,两条巨蛇上下翻滚,场面惊心动魄。强壮的钟慧峰终于累了,连棍子也举不起来了,他停下来低头四处寻找。过了好大一会儿,两条长虫浮上来,肚皮朝上,是金黄色的。这个时候,胡图仁猛然想来,自从他看见两条蛇,一直到蛇被乱棍打死,它们自始自终都是在一起的,好像是受过训练一样有序,它们一起游下来,一起游向钟慧峰,一起受死,想到这,胡图仁冷汗下来了。正想着,钟慧峰已经满身是水拖着两条长虫上了岸。
当蛇已经成肉段,放在河里洗刷刷的时候,三个人愣住了。蛇肉在河水里仍在有力地游动,令人惊恐的是,它们还是并排游着。这还不算,让人最惊心的是 :一只蛇肉是乌黑色的,另只是雪白的。“这真是见鬼了!”以武士自称的钟慧峰也慌了。因为他*蛇无数,肉都是红的,哪见过黑的和白的?
那一餐蛇肉吃的态度很暧昧,大家都不愿意多吃,蛇肉不仅硬咬不动,而且味如嚼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