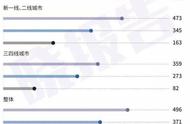俗语有云,“是药三分毒”,同时又有“有病治病,无病养生”用中药的说法。关于药毒,近些年屡有中药或中成药某些有毒成分产生毒害作用的报道,一些国家对相关的中药采取了限制措施。在临床上,也常会有病人问起,某种药能不能长期服用,有没有副作用。那么,中药到底有没有毒?或是哪些药有毒?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到底该怎么认识中药的“毒”呢?
1从“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传说谈起作为自然物质的中药亘古即存,其特殊效用被发现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先民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主要靠大自然,而药物就在大自然中存在着,契机就在赐予和危机中悄然来临。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人们在采集和猎取食物的过程中,一些特殊的“食物”被区分出“利”与“害”:利者可以用来疗疾、强身,即早期的药;害者轻则致病,甚则害人性命,即需当避忌的“毒”。这时的“药物”仍然停留在偶然发现的阶段。
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又经历了漫长时间的积淀,先民们似乎已经发现了“草药”这条治病愈疾的道路,开始主动地去发现和尝试各种草药。其中,流传最广、最具传奇色彩的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神农氏

神农尝百草
神农氏,因五行相配之德为“火德”而为王,故又被称为炎帝,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神农氏翻山越岭,尝试了多种花花草草,寻出了许多的药物,并用它给人们治病,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氏在尝百草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毒草。 神农氏寻药的过程中,遇毒药无数,常用自己寻到的草药解毒。传说有一次,神农尝到了一种开黄色小花的草,就是传说中的“断肠草”,毒性很大,还未来得及解毒就殒命了。
《淮南子·修务训》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即使是传说,也可以知道“毒”与“药”自发现之时,就缠绕在一起。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神农氏一日而遇的七十毒,“毒”药所占比重是很大的,这些“毒药”是被弃用了还是也找到了它的用途?答案显而易见。
2“毒”与“毒药”的两种含义“毒”广义而言,是对药物偏性的概括,狭义而言则是指药物的有害性。
(1)药的偏性为“毒”,药皆称“毒药”
在早期,用来治病的“药”,都称为“毒药”。《周礼·天官冢串》言:“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供医事”。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也有相关记述:“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素问•异法方宜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素问•脏气法时论》)唐代的王冰注解指出:“药,谓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虫鱼鸟兽之类,皆可以祛邪养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谓之毒药。”“毒”是逐邪驱病的“药能”,是药物产生疗效的基础,故“古者以药为毒”。毒药,最早是用来逐邪驱病的。
随着药物不断被发现,以及生产力和物质生活的逐步提升,人们对药的需求已不仅仅是治病,也有了养生防病的需求,一些具有调理、补益养生功效的药物被广泛使用。“毒药”之总称,也已不合时宜。
药有一气之偏,故有治病之能
不同中药各自所具有若干特性和作用,即药物的偏性。以药治病,即是以药物的偏性纠正人体阴阳气血偏盛偏衰的疾病现象,恢复人体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即“补偏救弊,调和脏腑”,也可简称为“以偏纠偏”。
《医医病书·二十二、论药不论病论》言:“天下无不偏之药,无不偏之病。医者原以药之偏,矫病之偏。”
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丹砂》指出:“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
唐容川《本草问答·卷上一》也讨论了中药治病的原理,其论曰:“问曰:药者,昆虫土石、草根树皮等物,与人异类,而能治人之病者,何也?答曰:天地只此阴阳二气流行,而成五运(金木水火土为五运),对待而为六气(风寒湿燥火热是也)。人生本天亲地,即秉天地之五运六气以生五脏六腑。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以生,特物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故神农以药治病。”
可见,中药治病虽常被冠以“调理”“调和”之说,其背后的机理是“借药性之偏,以调人体的偏盛偏衰”。药大都是有偏性的,皆是对疾而为用,即使未冠以‘毒’字,也非日常常用之物。所以,“有病治病,无病养生”的用药观念并不值得推崇。治病讲究对证,养生也讲究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所用药物也非一律。诚如吴鞠所讲:“如对症,毒药亦仙丹;不对症,谷食皆毒药。”
药偏性有大小,良毒善恶宜以病分
药物中,有偏性大的,也有偏性小的。早在《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中,就有了对药物大毒、常毒、小毒、无毒的区分,而《神农本草经》对药物“三品”的区分,也考虑了这一点:上药主养命,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宜于养老延年;中药主养性,无毒、有毒,斟酌其宜,宜于欲遏病补虚羸;下药主治病,多毒,不可久服,宜于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其中,上品药中有一些重金属类有毒之物,被视为养生延年之品,是受了道家炼药服食的影响,与事实不尽相符。
药自身有“良毒善恶”,但于治病而言,其有毒无毒就在病而不在药了。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有毒无毒,所治为主。”
(2)药的有害性为“毒”,易产生毒副作用
毒,指药物因气味性能峻猛而偏性大,容易产生有害性,也就是毒、或副作用。本草典籍中多有“大毒”“有毒”“小毒”的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也将有毒中药做了“大毒”“有毒”“小毒”的不同标注。一般认为,大毒者,偏性最大、毒性剧烈,使用较小剂量,即可迅速发生中毒损害、甚至死亡。药如生川乌、生草乌、马钱子、红粉(HgO)、斑蝥、砒霜等。有毒者,有一定的毒性,日久蓄积、或用量过大或使用不当,较慢的发生中毒症状,严重者也有可能造成内脏损害,甚至死亡。药如白附子、附子、生天南星、生半夏、蟾酥、洋金花、雄黄、木鳖子、千金子、……硫黄等。小毒者,毒性较小,用量较大或久用蓄积会产生一定的毒副作用,一般症状轻微。药如红大戟、苦杏仁、鸦胆子、急性子、蛇床子、川楝子、土鳖虫、艾叶、……吴茱萸等。
几年前,在网络上就流传着“中药毒副作用一览表”,列出了大量中药及中成药。如:马兜铃、关木通、天仙藤等含有马兜铃酸,为肾毒素可导致肾衰;雄黄导致砷中毒;板蓝根长期服用能损害肾脏;肉桂过量使用可能对肾脏有毒;全蝎可引起过敏反应、血尿、糖尿、蛋白尿;川楝子能使心、肝、肾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能导致中毒性肝炎,等等。这类药物,是不是因为它的某个或某些化学成分“能导致器官损害、机体功能障碍,甚至导致死亡”就需要避忌呢?首先,论药不论病,无异于胶柱鼓瑟。再者,拆分为一个个化学成分的中药也已不再是中药。
有毒之药,用之得当是治疗疾病的利器。日本医家吉益东洞,曾发问:“毒药易害人,是固可畏矣。而医之良者,用毒愈多何也?”他将毒药比喻为利器,指出“盘根错节,非利器则不断;痼疴难瘼,非毒药则弗除。……物有非常之性,而有非常之能。”(《先哲医话集·二三利器毒药》)《珍珠囊补遗药性赋•用药法》也指出:“然有大毒之疾,又须用大毒之药以劫之,如古方感应丸,用巴豆、牵牛同剂,以为攻坚破积之用。四物汤加人参、五灵脂以治血块。二陈汤加黎芦、细辛以吐风痰。丹溪治尸瘵莲心散,以甘草、芫花同剂,而谓妙处在此。”
中药之毒是可以有效趋利避害的,用之得当的确是没有毒副作用。
3“趋利避害”用中药《吕氏春秋·尽数》谓:“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中药的利、害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医“药以治病,以毒为能”(张景岳语),是在辨药之“利”的基础上,对其“毒”进行利用或转化利用。
(1)有毒无毒,所治为主
用药必先识病,然后方可论药。药是用来治病的,必然有其针对性,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用之得宜则病可愈,显示出的是功效,即使含有毒之药也不会有毒副作用。如乌头有大毒,但却是祛痼寒之良药。《尚书·说命篇》云:“药弗瞑眩,厥疾弗廖。”喻嘉言在《寓意草·先议病后用药》一文中,评价说:“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是能用药者。” 如张仲景乌头桂枝汤治疗寒疝腹痛,以“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恰是因毒而效。
若不论病、不问虚实,但以药品贵重、药性补益为虑,则无毒者亦毒。尤其,在养生方面,前车之鉴多矣。《冷庐医话·卷一·慎药》载两则医案:
沈赤文年二十,读书明敏过人,父母爱之,将毕姻,合全鹿丸一料,少年四人分服,赤文于冬令服至春初,忽患浑身作痛,渐渐腹中块痛,消瘦不食,渴喜冷饮,后服酒蒸大黄丸,下黑块无数,用水浸之,胖如黑豆,始知为全鹿丸所化,不数日热极而死。同服三少年,一患喉痹,一患肛门毒,一患吐血咳嗽,皆死。此乃服热药之害也。
黄朗令六月畏寒,身穿重棉皮袍,头带黑羊皮帽,吃饭则以火炉置床前,饭起锅热极,人不能入口者,彼犹嫌冷,脉浮大迟软,按之细如丝。此真火绝灭,阳气全无之证也。方少年阳旺,不识何以至此,细究其由,乃知其父误信人云:天麦二冬膏,后生常服最妙。遂将此二味熬膏,令早晚日服勿断,服之三年。一寒肺,一寒肾,遂令寒性渐渍入脏,而阳气寝微矣。是年春,渐发潮热,医投发散药,热不退,而汗出不止,渐恶寒,医又投黄连、花粉、丹皮、地骨皮、百合,扁豆、贝母、鳖甲、葳蕤之类,以致现症若此。乃为定方,用人参八钱,附子三钱,肉桂、炮姜各二钱,川椒五分,白术二钱,黄芪三钱,茯苓一钱,当归钱半,川芎七分。服八剂,去棉衣,食物仍畏冷,因以八味加减,另用硫黄为制金液丹,计服百日而后全愈。此则服凉药之害也。人之爱子者,可不鉴于此,而慎投补剂乎?
虚证或体虚病后,当视脏腑阴阳气血之所偏而补之,以为调理或善后;养生服补剂,当审体质之宜,不可偏一致害。这一点,在当代而也有同样的意义。比如,近几年掀起了一股用三七养生的热潮,在大众间流传着“每天一勺三七粉”调和气血的说法。三七兼具行血、止血、补血的功效,常用来治疗血证,当代在保健养生方面拓展用来调理三高症及祛除瘀滞色斑等。三七虽行血不伤血、祛瘀不伤新,但也是有一定偏性的,治病也好,养生也好,必然是“出血”“瘀滞”类的病证或体质才适合。人以气血调和为贵,无故用之,会有“损血”之虞。即如《得配本草》言:“能损新血,无瘀者禁用。”
总之,药之有毒无毒在于其用,药用对了,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就是药;药用错了,用在不需要的人身上就是“毒”。《医灯续焰•卷二十(附余):医范》曰:“用之不善,则无毒者亦毒,……达造化性命之理,则虽毒不毒”。郑钦安在《医法圆通·用药弊端说》也指出:“病之当服,附子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 参芪鹿茸枸杞皆是砒霜。”一言概之,用之得宜,毒皆为药;用之不善,药皆为毒。
(2)有毒无毒,服药有约
中药治病,以“扶正祛邪”为基本原则,追求使人体阴阳气血归于和平,因此在服药用量上讲求“药病相宜”,在服药时机上讲究“进止有度”。因为,药不及病,则邪气不去而效微;药过于病,则容易伤正气而变生他患。
治病用药,皆须量宜
中药服药有常规的原则,一般而言,病重者宜大,病轻者宜小,无毒者宜多,有毒者宜少,耐毒者宜多,不耐毒者宜少。
对于有毒中药而言,药性更为峻烈,并且起效剂量与中毒剂量往往比较接近,针对这一问题,中医也有自己的解决方法——渐加试用。《神农本草经·序》言:“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什之,取去为度。”古代医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有很多的记述和实例可参考。但是,中医始终是以人为本的,还是强调“虽有此例,更合论人老少虚实,病之新久,药之多毒少毒,斟量之,不可执为定法”。(寇宗奭)
中药用量很多是不精确的、没有定量的,因为它需要根据药的毒性大小、病的轻重缓急新久、病人老少虚实及体质的耐受程度等等斟量。如《灵枢·论痛》就对人对毒性药物耐受能力大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对此,张景岳解释的很透彻,他说:“胃厚者脏坚,色黑者表固,骨大者体强,肉肥者血盛,故能胜峻毒之物。若肉瘦而胃薄者,气血本属不足,安能胜毒药也。”
有毒无毒,无使过之
《内经》将药分为大毒、常毒、小毒与无毒,去病有六分、七分、八分、九分之约。
《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道理十分明了,要点有二:一是“毒药攻邪”当知止,避免用药蓄积而产生偏绝、矫枉过正而伤正气;二是,宜以“谷肉果菜”正性者培养正气而除余邪。
中医治病,毒药攻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视调动和利用人体正气达邪的能力。相对于现代医学“除恶务尽”凌厉攻势而言,这种给正气助一把力、给邪气一个出路的治疗原则以及“除恶勿须尽”用药方法,就“人本”了许多。陆广莘先生曾指出,“除恶务尽”模式,不是一种积极的医学模式,中医的健康医学思想、提高自身抗病能力的思维方法应该大力宣扬和推广应用。反观临床,比如当今多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等,被看作是终身服药的疾病,用长年累月的服药来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与中医的理念相去甚远。
有故无殒,亦无殒
妊娠病用药对于峻利、有毒之药一般是需要避忌的,但当疾病威胁孕妇或胎儿安全时就另当别论了。在《素问·六元政纪大论》黄帝向岐伯请教了这一问题:“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答:“有故无殒,亦无殒也。”讲的是妇人怀有身孕而有大积大聚影响胎儿的情况下,有毒的药该用就得用了。《周慎斋遗书》解释认为:“盖妇人重身,有故则无损,毒药无碍也。大凡因胎而有病,安胎为主;因病而胎不安,宜治病为急。所以重身可用毒药也。”需要注意的是,岐伯在解释其原因时,还提示说:“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故妊娠用毒药攻邪,病衰其大半,便当止药,以免胎儿受伤。
(3)炮制、配伍,减毒增效
中药减毒增效,主要有2种方法:一是炮制减毒,降低或消除中药的毒性;二是中药配伍减毒,两种或多种药物配伍,达到减毒增效的目的。《圣济总录· 卷第一百四十六·杂疗门·中药毒》:“神农尝百草,一日而七十毒以辨相得相反相恶相畏,至于有毒无毒,各有制治,然药无毒,则疾不瘳。内经所谓知毒药为真者,乃用药之要也。昧者误有服食,当究其毒以制治之。犹巴豆之用黄连,半夏之用生姜是也。”减毒增效,是中医专业的常识问题,无需赘述。
总之,中药有毒无毒,所治为主;对疾为用,知约、知制、知伍则可趋利避害。

文/张立平 本文曾发表在2018-10-18,中国中医药报4版,文字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