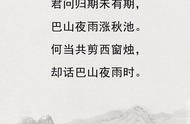作者:叶 子
立秋时节,虽夏意正浓,却已能见到金黄色的梧桐落叶,这是阴阳在悄然间彼此转化。盛夏的黄叶,冬至的花蕾,它们都是意在言外之物,没有违背时令的逻辑,只为传递季节的真谛。窗前月光,长河落日,诗的言外之意,也是这样。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以缠绵悱恻、哀怨动人著称。他的七绝《夜雨寄北》初读似有违诗人的创作逻辑,而细细品之,则似乎更甚其他隐晦之作。
《夜雨寄北》
李商隐(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夜雨寄北》作于李商隐滞留巴蜀之时,约851年左右。诗的风格一改诗人惯常的婉转凄美,在渲染心绪上显得很克制。每一句,都似乎在为之后的情绪做铺垫,期待中的抒怀并不是直接出现,而是笔锋一转,似乎在顾左右而言他。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诗人在阐发心境的同时,把对自我人生的论断、对人生记忆的追寻,以及对未竟之事的抱憾,都纷纷掩藏在了其中。
第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远方的故人在问归期,某君可能是友人,也可能是情深意笃的妻子王氏。何日返回国都长安,连诗人自己也不知道。但这个答案不仅是给北方的亲人,也是李商隐写给自己的。与其说无法给出确切归期,生发的是无奈或歉意,不如说诗人借这番问答,给自己当下的处境甚至一生的不得志,下了一个断言。同为断言,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表达的是对人世的态度,对象其实是外部世界,而非自我;而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看似在定义自己,其实期待的是未来有更多的作为,是开放性,而非盖棺定论式的断言。李义山在这里,似乎用一个看来寻常的答复,当作对自身命运的认定。李煜《相见欢》里的那句“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其中的“锁”字正如这里的“未”,也是对自我当下处境的断言。无论是李义山的“未”还是南唐后主的“锁”,里面自然都是有不甘和不平的,但更多的却是对人生实况的白描。在不如意的环境中,对外界进行价值判断已无多大意义,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力,是智者自处的方式。
第二句“巴山夜雨涨秋池”是对生活环境和时节的描述,没有点明前一句似乎就要牵扯出的心情,而是在控制情绪流露的同时,把对自我的剖白收敛起来。这甚至不是寄情于景,不是“天凉好个秋”,或“寒塘渡鹤影”。此句是在为诗的第四句埋伏笔,这里只是先提出,然后就搁置到一边。巴蜀之地潮湿多雨,秋日池水上涨,这本来没什么特殊的。一个“秋”字,似乎再次令人惆怅,但这也非诗人本意,写诗的时节就在秋日,在此也无非是客观而已。
第三句是全诗情绪的制高点,“何当共剪西窗烛”,一个“共”字,无论对象是友人还是爱人,都是至真至爱的真情流露。剪烛自然是在夜晚,如果是友人,则是秉烛夜谈的交情,若为爱人,则是伉俪情深的写照。那么,何时才能与君一起,在夜晚的窗边,剪去蜡烛的灯芯,让小小火苗把彼此的心照亮呢?这番期望如此寻常,但在归期未知的现实世界里,又显得那么困难、那么无望。这种无望的期望里,或许就有诗人最真实的自我。并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不是“无故寻仇觅恨”,只是一个理智而清醒的人,在把自己的愿望向故人也向自己,坦然呈现。此句虽然是全诗最显情绪之处,但情绪表达依然是极为克制的,李商隐诗文的隐晦,或许也在于这种对情感的隐而不发。
第四句打破通常七绝不重复用词的“潜规则”,再度出现了“巴山夜雨”。“却话巴山夜雨时”,“却”字与第一句的“未”和第三句的“共”构成某种张力,诗人不愿明言或难以明言的真实自我,在其中找到了落脚点。“未”是无奈的否定,正是这一否定让自我陷入困顿;“共”是无望的期望,但自我不得不被寻找;“却”是强劲想象之下产生的虚拟现实,与故人的相会如今只存在想象里,但诗人已经想好了要说什么,就说今日的夜雨和秋池吧。想到此处,自我突然有了着落,仿佛未能如面之人已在眼前。后世晏殊的“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曾经的赏花人如今已多不在;在李商隐这里,正因为他深感在真正的未来,今日想念之人也未必能见,所以便让故人马上来到眼前,共听巴山夜雨。
《夜雨寄北》的第四句是全诗的诗意所在。到这里,清醒的诗人终于抛却了清醒,投身于自我创造的虚构之中。这种从绝对的现实和理性,直接跃入想象世界的笔法,或许是为理性寻求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此诗写于王氏去世之后,所以历来多有人认为是诗人写给友人而非妻子的。但从全诗对情绪的克制,以及相会的虚构来看,难道不更像是一种悼亡吗?正因为亡妻不可能再见,“未有期”便是写给彼此今生的断言,而“巴山夜雨”既是真实的此刻,也是回忆中永恒轮回的时光。李商隐的这首七绝,看似直白,实则依然隐晦。这种隐晦不在于“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茫然未明,而是在显然已经虚构的跳脱时刻,诗人依然保持着清醒。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博士)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