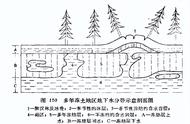杨早

庄秋水


主题:在民国元年想象民国
时间:2022年2月12日14:30
地点:雍和书庭
嘉宾: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庄秋水 媒体人、纪录片人
主办:后浪出版,雍和书庭
判断一件事在历史中的影响度,不能只靠后来通约化的史书
杨早:今天(2月12日)是个很特别的日子,110年前的今天,清廷宣布退位,从那天起真正开始进入民国。
庄秋水:正好我以前写过一篇长文章,题目是《帝制中国的最后时光》,就是把2月12日这一天作为时间切入点,讲在此前后整个帝制是怎么倒的。所以我先来做一个引子。
大家刚刚过了年,我们过的这个年现在叫春节,而阳历年元旦是1月1日。其实中国以前是没有阳历这个纪年方法的。我印象中应该是在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摄政王载沣引咎辞职。他辞职之后同一天,清廷发布命令,准许人们剪辫子,还有就是改成阳历纪年。在此之前,围绕纪年在当时争了很久。比如革命党,就是同盟会这帮人,主张用黄帝纪年;还有人主张用孔子纪年,就是从孔子诞生那天开始纪年。
大家知道,中国讲“定正朔”,非常注重历法,因为这代表着你从上天得来的法统。1912年正式开始推行公历纪年,很多人不接受。当时有一个对联特别著名,好像在长沙土地庙,上联叫“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下联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后大力推行过阳历年,1月1日,但到那天也就挂挂国旗,政府宣传一下,民间仍然要过我们现在的农历年,也就是春节。
整个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但在1912年2月12日前后,有很多东西马上要改,激起反响最大的是“剪辫令”—— 1912年3月份大总统令,要求命令到达地方20天内必须执行。我记得梁启超说他们家的厨子辫子被剪之后痛哭流涕。当年满清入关,叫“留发不留头”,现在又要把这个辫子剪掉,它其实是非常大的事情。有些东西可以用一纸命令强制推行,但有些东西可能一百年都没有断绝。这些杨早师兄《元周记》这本书里都写到了。
杨早:我现在不管聊书还是聊别的什么,都不是很愿意用那些大的概念去统摄一切。因为我们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可以推想,即使同属一国,大家的关注点仍然天差地远,每个人的点是不一样的。倒着推想一下,110年前,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判断一件事情在历史当中的影响度或者震撼感,不能够只靠后来通约化的史书,因为任何史书都会遮掉一些东西,突出一些东西。
使用阳历纪年,中国开始进入现代
杨早:现在史书里说到民国元年,说到辛亥革命,一定会强调国体的变化、政体的变化。但是站在民国元年来看,某些事对某些群体的影响,可能还大于国体、政体的变化。比如上海县的城门不关了,这件事对上海影响很大。因为在清末,一到晚上城门一关,你就回不了上海县城了,只能住在租界。所以四马路那边的妓院有一个名词叫“借干铺”,意思是说并非我想在妓院里留宿,我只是因为城门关了回不去,所以我在这里借宿一晚。“干铺”,就是不发生任何别的事情,就是住一晚上。但是不是真的“干铺”,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么个说法。现在城门不关了,大家就失去了这个借口。这就对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产生冲击,这种影响就可能超过了皇帝退位。
那从帝国转换到民国,对所有当时的中国人都会产生巨大冲击的是哪些事呢?一个是时间,我们的时间观念被改变了。大家可能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新历与旧历转换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你想想,不说过端午、过新年这种节庆,就说以前的商户,是习惯于三节结账——端午、中秋、新年,这三个时候去上门结账。平时基本都是赊账——这是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就像我们现在用“花呗”。到了过节的时候,商铺会上门很客气地说:“您要是有余钱,再借给我点儿?”他是债主,但他要说“您借给我点儿”,当时就是这样的商业习惯。
现在时间改了,那商家是新历的8月15日来要账,还是旧历八月十五呢?这是个巨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国引进了财年——财政年度的制度。那这个财政年度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用新历算还是旧历算?跟世界各国怎么接轨?这是很大的问题,对整个国家的财政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时间的改变不仅仅是过不过旧历年那么简单。
庄秋水:从大的方面来说,为什么当时改用阳历年?就是我们要跟世界对接。包括晚清使节出使去国外,没法跟别人的时间对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从上海海关开始,在近代引入了新的时间概念。纪年改变好像有点“时间开始了”的感觉,我们进入现代了。
杨早:我们研究历史的,看书上写到的任何一个日期,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阴历还是阳历?尤其是清末民初,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就得通过前后文来判断,相当麻烦。
关于使用阳历,民元前后大家基本上有共识,连清廷都愿意用阳历,虽然不乏反对者。而从什么时候开始纪年呢?清朝一定还是叫宣统三年;如果用章太炎的说法,那就是黄帝四千六百九年;如果用康有为的说法,就是“孔子降生2489年”。最后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各省代表团表决通过使用阳历,称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这就是时间的改变。时间对当时人影响太大了,出现各种问题。包括我在《元周记》里也写到,武昌那些公务员,新历的5月5日他们偷偷放假,后来被别人查处了。到旧历的五月初五又放一天假,一年过两次端午节。
三百年来,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自由
杨早:第二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就是身体,也就是刚才说的剪辫问题。剪辫子说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复杂,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别讲究礼仪和符号化的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比如说在座各位,现在还在正月,谁去理发了吗?谁家有舅舅敢去理发的吗?你可以不在乎,但是舅舅很在乎。
庄秋水:北方特别讲究正月不能理发,一理发就死舅舅。
杨早:我前两天去理发,特别好约,以前约不到的师傅都随便约。礼仪看上去没那么重要,比如过年回家,说起来很多年轻人都不太愿意返乡,但是一旦真要“就地过年”,很多人还是会心中非常歉然,因为回乡过年是一个强大的民俗习惯。头发也是这样,一开始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剪着剪着,到了二百多年之后,就变成让我剪我都不愿意剪了。
庄秋水:当时清朝入关的时候,在江南激起巨大的反抗,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多尔衮下的薙发令。当时很多江南士族没法接受这个事情——我可以投降,但是你让我剃头不行。
杨早:有好几个县已经投降大清了,但是一听说要剃发又不干了。因此身体对一个人的选择影响,那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我最近在说另外一个道理,其实我们要这么看,从二百多年前清军入关时候“留发不留头”,到1912年剪辫令——其实这条命令并没有真正那么严格。像杭州很典型,杭州下达剃发令,说旧历年前必须都剃掉。结果呢,像鲁迅小说《风波》里七斤那样的农民就不敢进城了,进城就要被剪头发,在乡下还好。他们不进城,后果是什么?杭州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杭州所有的垃圾运不出去,粪便也运不出去,就完蛋了。在这种逼迫下,军政府也不得不改口表示,“那好吧,这个剪发令推迟到年后吧”——这就说明剪辫令在推行过程中已经没有那么的严格了。这个过程说明什么?说明三百年来,我们的发型还是在往自由的路上走,还是会越来越自由。
但是其实中间会有反复。比如在上世经70年代,那个时候走在成都的街头会被剪裤子的——一旦看谁的裤子过宽,直接上去就剪掉,而且剪得很深,搞得那些女孩没办法,在街边哭。
庄秋水:剪的人是谁?
杨早:就是一帮义愤的群众,觉得你这样有损市容,所以要剪。很多女孩就只能拿手绢把它绑好,赶快回家换裤子。那时候出现这种笑话。
总的来说,这三百年来,我们的发型,包括对身体的处置,还是往自由的方向在转型。我们想染发就染发,想挑染就挑染,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在走向进步。身体的问题跟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关系到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有没有信心处理我们自己的身体。
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才彻底消除裹脚陋俗
杨早:但是民国元年有一件事没能反掉,那就是裹脚。这一点是不是说明,男的身体改变比女的改变要容易?
庄秋水:其实在1904年还是哪一年,慈禧太后已经下令了,要求废除这个。
杨早:满清是一直不裹脚的,满人不裹脚。
庄秋水:他们入关的时候就反对裹脚,后来发觉禁不了。跟后来要求剪发一下剪不掉一样,也就承认了——我们满族人不裹脚,你们汉族人要裹脚随你们便了。
杨早:当时裹脚还可以作为一个民族气节的象征,有一句话叫“男降女不降”,就是男人没办法,要穿清朝的衣服,要梳辫子;女性服装不变,裹脚不变——汉族妇女的自我伤残,还变成一件好事。很有意思。
庄秋水:后来国民政府曾经也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推行,彻底要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消除落后的、落伍的、愚昧的象征,到1930年代,中国社会才彻底消除裹脚的陋俗。由此可见,真正涉及到人的社会生活和身体层面的很多东西,其实它是最顽固的。
缠足这个事,从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就把它视作是非常残忍的,是整个社会愚昧的象征。传教士们走上层路线,找李鸿章这些大员做说服工作,也在社会上办杂志、到处宣传“中国女性裹脚、不接受教育,这都是造成中国愚昧落后的重大原因”。直到后来像康有为他们才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改这一点,在国际上没法翻身,名声太差了。
康有为和维新人士组织了放足会、天足会等。但是你想多难。当时为什么女性会选择这种残害自己身体的行为呢?因为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如果不裹脚你就嫁不出去,或者嫁不到好人家。所以后来“放足会”就有一条会规——我们的子女在这个圈子里面通婚,我的女儿和你的儿子结婚,这样就没有婚姻的后顾之忧了,才可以放心大胆去放足。用了好几十年、近一百年的时间,缠足这件事才算彻底消除掉。
也是发生在1912年,当时宋教仁和蔡元培他们组织了一个社会改良会,一共提出36条。现在看这36条,涉及有特别重大的社会议题,比如不再纳妾,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再嫁自由;也有很小的方面,比如不要打骂你家里的佣人,包括不再磕头,用作揖或者是鞠躬代替磕头。大到后来民法里面《婚姻法》规定的方面(1949年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小到我们人际交往中的一些礼节的变革,在当时是很全套的东西。但这些真正发生变化,也是要几十年,有些东西到现在也没有彻底废除。
现在发型自由、穿衣自由,但是观念上,仍有可进步的空间
杨早: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晚清最初主张反对缠足的这些人,全都是男的。女性是后来才加入的。
庄秋水:女性是不愿意的,后来推行放足的时候有女性要去自*呢,因为让她放脚她不干,觉得“这样我还是个女人吗?”
杨早:而且这些人主张放足的理由,现在看来也很奇怪——并不是说缠足伤害了女性的身体,对女性构成了压迫,而是说缠足让中国一半的人失去了劳动能力和行走能力。
庄秋水:还有一个就是“种强则国强”,认为缠脚会影响血液循环和分泌好的高质量的乳汁,对培养下一代不利。
杨早:所以,重要的是女性缠足以后,第一她不能当一个劳动者,第二是她不能当一个好的母亲。注意到没有,放足的出发点是这个,是女性不能够很好地履行国民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来反对缠足。
这样一个思路,到了民元的时候体现为什么呢?在1911年底的时候,上海就成立了女子北伐队,号召女性参与北伐。但是到南北统一以后,在北京举行大会,同盟会跟其他几个小党联合成立国民党,在这个会上他们宣布一条规章,说我们不接受女党员,女子没有投票权。这个事特别大,因为当时沈佩贞、唐群英她们这些老同盟会员就火了,上去就给宋教仁一个耳光。其实这条也不是宋教仁的主张,之前在南京唐群英她们已经找孙中山闹过了,就是为什么不给女子选举权。民国成立以后,一直没有同意给女性选举权。
庄秋水:一开始主张的时候是这样宣传的,说你跟我们一起干革命,将来就有选举权,妇女有各种各样的权利。
杨早:那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吗?所以在民元时候,女性不是一个热的话题,但它是一个潜在的,甚至是全球性的话题。如果你仔细看报纸,会发现在英国正好也爆发了强大的女权运动,英国的中产阶级女性为了唤起整个社会对女性的重视,她们不惜走上大街去打烂商店橱窗,暴力毁坏公共建筑,用这种方式来引起大家的注意。
庄秋水:对,就是争取选举权。
杨早:还没有谈到被选举的问题,只是选举权,都要采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在争取。所以这件事上中西是呼应的,1912年,女性都在争取权利。
庄秋水:全世界女性是同步的,相当于女性的第二波觉醒年代。英国最终是1918年女性有了选举权,但是给划定了一个年龄——30岁以上,可能认为女性30岁就成熟了或者有见识了。
杨早: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很大原因是因为1914-1918年的一次世界大战,大量的男性在战场上牺牲了,需要女性去工厂做工来填补这个空缺,这种局面加速了女性选举权的获得。
1912年,看上去好像很远,已经110年了。但是你看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这些问题到现在解决了吗?我觉得我们还在路上,还在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现在确实可以发型自由、穿衣自由,但是在观念上,我们能不能自觉地去呈现自己对社会改良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能不能体现在实践中?我和秋水都很看重教育,我们怎样能够通过教育去让中国下一代的观念有所转变,而不是教育只是教知识,让下一代观念依旧。
对于历史整体关照而言,“常”比“变”更加有用
庄秋水:1912年3月5日,当时的《时报》对于新旧的快速变化有一个总结,它说:“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这篇文章名字就叫《新陈代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史料。
感觉仿佛新旧一夜间,而事实上,很多东西的变革已经持续了很久。比如1912年秋天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共和国教科书》,那套书其实从废科举、推行新教育体制之后就一直在编。它编辑理念的第一条,就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共和国公民的人格,一切要以儿童的本位来出发”。这跟传统的教科书就很不一样了。之前传统蒙学读物,大家都知道是“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都是要背诵。虽然也有通识教育比如历史的成分,也有一些植物学、动物学的知识,但总体来说比较远离小孩子的天性。
后来到19世纪末期,慢慢有一些新东西进来了,受西方教育体制的影响,才开始编教科书。这是一个过程,包括改编《三字经》为《时务三字经》,把五大洲、东西半球这些传统读物没有纳入的地理知识,包括西方历史,都纳到这个体系里面去。从教育体制和教科书的改变,能看出其实从晚清以来,社会上就在缓慢改变。
杨早: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的特点之一,是它对时事的反应非常快速——四月份发生一件大事情,到八九月份出书的时候,就已经编进课本里去了,而且是足足两课的内容。什么事呢?泰坦尼克沉没。速度之快,我觉得现在都很难想象。对于1912年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是要教给小孩子知识,更多的是要把教科书当成一种传播启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重塑一种民国的观念。
庄秋水:后来到三几年的时候,叶圣陶和丰子恺编写的那套开明书局国文课本,就是完全的白话文了。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到编教材这个事情里了。
杨早:是这样的。我觉得教科书是我们研究国民心态和国民知识、国民常识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一辈子所有的知识,都从教科书里来的。像《开明国文讲义》那套书,编出来本来也不是给中小学用的,而是给每天上班的“社畜”们自学用的,给那些没有接受到太多正统教育的店员或工人自学用的。因此也编得特别的实用灵活——切实地教人怎么写文章,怎么用字词,怎么写信函,是真正塑形一个民族心理特别重要的因素。反而比教育部发布的教材更加影响深远,现在也成为了经典。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用抄《申报》的方式来结构《元周记》原因。作为历史写作者,我们都知道,写“变”比较容易,一个大变革时期,辛亥革命也好,“庚子事变”也好,太多的资料留下来,大家也喜欢看到这种“动”的感觉。比较难写的是“常”,就是日常的生活。为什么1980年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引起知识界巨大的震撼?就在于这本书写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年份——1587年,这个年份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但是往前往后,能看出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
所以写“常”比写“变”要难,“常”也没有“变”那么好看,但对于历史的整体关照而言,“常”比“变”要更加有用。变的时候,根本不会在乎后面会怎么样,光复、革命、改朝换代,一切都是打碎了重来。但到了1912年,问题就都出来了,我们怎么重新设计这个社会?我们怎么重新运行日常生活?每个人都因此产生对民国、对共和不同的想法。
整理/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