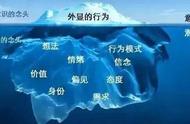我的童年是在姥姥的陪伴下度过的,那是一段充满欢笑的时光。在那简单的岁月里,我像一棵小树苗一样,在姥姥家的院落里茁壮成长。那里有我无数美好的回忆,那些关于姥姥家的童年故事,仿佛就在昨天,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时候,每天早上,当第一缕阳光洒进窗户,姥姥就会轻轻地叫醒我,给我穿上她亲手缝制的衣服,带我去灶间品尝她做的美味早餐。姥姥家的灶间靠墙砌着灶台,一口大铁锅位居当中,周边散放着零散柴火,那些柴火都是姥姥步行老远捡来的。
我喜欢拉的风箱,就在灶台下面。喜欢拉风箱的理由很简单:帮着干点活,就能得到一个甜蜜的奖赏——烤地瓜。大锅做好饭,锅底的明火还没完全熄灭,这个时候埋进去一个地瓜,用柴火的余温慢慢烤熟,用烧火棍掏出来,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抓,太烫,只能在两个手里倒来倒去。用嘴咬开皮,里面的黄瓤冒着热气,直接下口,经常被烫得呲牙咧嘴,手上嘴上全是灰。
蜂窝煤炉子摆在堂屋角落里,可以做点便饭,还可以取暖,不过比较多的时候是用来烧水。我曾跟着妈妈用板车去煤厂拉煤,回来后掺一些黏土进去,用模具制成蜂窝状,在地上晒干。引煤球是个技术活,弄不好就会满头大汗和满脸煤灰。晚上还要用铁签子把煤渣掏出来,睡前得把煤炉封上。
姥姥家有一棵大枣树,每到枣树成熟时,我喜欢在煤炉上烤枣子吃。晚上饿的时候,也烤过馒头,还要撒上晒干磨碎的干辣椒,吃得津津有味。那个时候,感觉什么都好吃,吃什么都很满足。生吃西红柿都是件特别快乐的事。我一般先掰开,里面露出浅绿色和浅黄色的籽,吃到满嘴汁水流淌,那种滋味令人啧啧称赞。跟姥姥去集市,西红柿一两毛钱一斤,跟那时不少低到几分钱的蔬菜比起来,也算是“奢侈品”了。
有时候,姥姥会从卷着的手帕里捡出五毛钱。我攥着钱端着碗,从街东头走到街西头,去王奶奶家的小店买两块红豆腐,一毛钱一块。每次姥姥都嘱咐多要一些红汤,可以留着蘸馒头吃,我也曾因此摔倒,汤洒了一身。顺道再到刘大叔那里买两个烧饼,这就是我和姥姥的晚餐了。烧饼一毛五一个,又大又厚,表面是用蜂蜜抹上去的芝麻,中间一层层的,夹着五香粉等调料。
童年还伴随着捉虫子的快乐,印象最深的是捉蚂蚱。这是一件需要技巧和耐心的事。我和小伙伴们通常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飞舞的蝴蝶和野花的香气中,在原野里奔跑,惊得蚂蚱四处乱蹦。一旦发现目标,我们就悄悄接近,轻轻地在草地里合拢,再迅速伸出双手,将蚂蚱捉住。蚂蚱非常敏捷,它们总能迅速跳开,让我们捉个空。不过,我们并不气馁,反复尝试。每捉到一只,我们就将它放在罐头瓶子里,拿回姥姥家,成为大公鸡的美食。
年龄越大,就越是怀念过去的日子。与其说是思念,不如说是想念那个时候的简单,那种单纯又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时没有WIFI,没有平板,没有智能手机,却五彩缤纷,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让人忍不住再三去回忆,去回味。成年人的世界酸甜苦辣,保持一颗纯净的心,才能在纷繁复杂中坚守一份从容。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也曾指出,成年后的任务之一,恰恰是弥补童年缺失的品质,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每当心情阴暗时,我总会回忆童年故事,就像用一根丝线把自己拉回那个简单纯真的年代。瞬间,就如这冬季突然飘飞的漫天雪花,带来快乐和幸福抚慰内心。那些故事就像涓涓泉水滋润我干枯的心灵,抚慰情绪、抵御焦虑,给我勇气、激发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