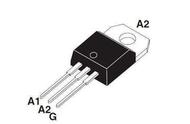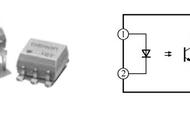徐长才
我小时候,家庭很穷,很长时间,我家租居在一位亲戚家里。刚解放不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去世之前,还带病为家里在分得的田里,做了三间草屋。我家与姓程的一家为邻。程家是大户人家,是殷实之家,除夫妻外,还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是家中强壮劳力。这家的女儿与我在小学同学。我家则大不同了,是祖母、母亲、我与年仅三岁的弟弟相依为命,母亲是家中的顶梁柱。
因为家穷,所以我儿时几乎是吃不到猪肉的,至于牛肉,我都没有见过。家里看了鸡,母鸡下的蛋,母亲也舍不得给家人们吃,要拿去在街上卖掉,换得食盐,用作烹饪的调料。鸡蛋卖钱,这就是当年人们戏称的乡间“鸡屁股银行”。逢年过节,母亲*只鸡,全家人能吃上一点鸡肉,打个“牙祭”,解个馋。

我家前面有口大塘,在这口塘下面有口更大的水塘。两塘之间,筑有一道高高的且厚实的堤坝,也就是塘埂。这条塘埂上靠北的一边长着一排高大的树。我家旁边有条淌水沟,下雨时,雨水就顺沟流到塘里。我就用泥巴做成一个小坝,把从练潭街上买来的一个叫小笼子的渔具,安放在小坝中间,雨水就通过小笼子流向塘里。泥鳅性喜“生水”,它们就从塘里向淌水的地方游来,钻进了笼子里。它们一旦钻进了笼子里,就休想逃出去了。这样,下一次雨,我就能靠笼子弄得一至两碗泥鳅,让家人吃上一顿肉食。笼子里有时也会钻进一条火龙蛇,俗称“泥蛇”。我往木盆里倒出泥鳅时,一旦发现有蛇,立即把它弄掉就行了。
我父亲是位优秀的木匠,能做各种家具和农具。他生前给家里做过一个专打老鼠的器具。器具下面放点谷物,老鼠去偷吃时,弄动了机关,很重的木块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地落下来,把老鼠压死了。早晨,我就取出老鼠,利用剪刀,剪开一道口子,把鼠皮剥掉,用盐淹制,再晒干,然后再蒸熟或煮熟吃,都好吃。据说,苏轼在逐放到海南儋州时,也吃过鼠肉以充饥。

当年,菜子湖冬季是枯水期,春季有满湖的湖草。这种湖草能作肥料,且是极好的绿肥。春三月里,我家一家四口人都下湖去打湖草。我用一种叫草镰的工具打湖草。我们把它晒干了,下午,我就把湖草捆好,我与母亲各挑一小担,四人一道回家。有一次,我很幸运,在湖草滩上逮到了一只老鳖。第二天,母亲把鳖煮熟了,全家人美美地打了一次“牙祭”。
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成灾。高赛河埂破堤了,洪水淹到了我邻居程家的门口。他家有几个劳力,在门前筑了一道坝以挡洪水。我家门前的下面那口大塘也被水淹了。我家分得的一些田地也被水淹了,所种的庄稼也都泡在水里,绝收了。那一年,全家人就靠吃救济粮度日子。
一九五六年,家乡又遇上旱灾,塘里的水没有了。那一年的夏天,我家门前的下面那口大塘也干了,只剩下一点水。那口塘的乌龟很多,那是在一九五四年洪灾时,乌龟从高赛圩和田野里爬游进了这口大塘里。水退后,这些乌龟也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乌龟在靠塘的田埂下面筑有不少洞穴。水干后,好多乌龟就要从塘水里和洞穴里爬出来,在滩上晒太阳。我就趁此机会,拎着布袋,在中午顶着烈日,在滩上追逐乌龟,捉住它,把它装进布袋里。我去一次,都能逮上六七只或十来只乌龟。回家后,我母亲就把这些乌龟去壳去皮,弄熟了给家人们吃。那一年夏天,我真的吃到了不少的龟肉。那真是一种好吃的肉,据中医说,龟肉很有补性呢。

我小时候,也吃过鱼肉。那都是小鱼小虾的,却没有吃过大的鱼肉。记得有一年,父亲搞了些小鲫鱼,煮熟了,作中餐的菜。我吃了,不幸被鱼刺卡了喉咙,还是父亲小心翼翼地把鱼刺弄了出来,我才破涕为笑。
父亲去世后,每逢春季,我在高赛河的浅滩处摸过鱼。小鱼藏在小小的凹处,能摸到它。摸到几条小鱼,煮熟了吃,我和家人们就可以打一次“牙祭”。
如今,祖国富强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们也过上了美满的日子。我现在旅住海口市,我小儿子和小儿媳经常带我去一些酒店饭庄,让我吃到了各种各样的肉的美味。儿时的肉的滋味只能留在记忆中了,也只能让它留在我的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