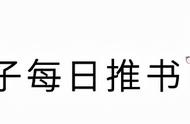采写 /郑丹 郑欣悦 张涵
编辑/刘汨

正在跳伞中的安安
在安安生前,她的朋友圈内容对于同学们有着十足的吸引力,那种总能滑翔于天际的生活是大多数同龄人可望不可及的,“她很酷,和我们好像不在同一个世界。”
意外发生之后,羡慕逐渐被质疑取代。“这是玩命,是不负责任”、“这是有钱人才能玩的运动”,一些非常尖锐的声音甚至把矛头指向了整个翼装飞行群体。
对于安安最后那段偏离航线、迅速下落的视频,圈中的同道好友大多不愿做出评论和分析,但他们还是想纠正一些人的认知:极限运动要付出的不只是金钱,相比挑战更重要的是规则和经验,冒险之后是对生命更大的尊重。
一次失败的翼装飞行带走了安安年轻的生命,留下的则是人们站在各自位置上,对于“极限运动”的解读与争论。

安安最后一次飞行消失前的视频截图
翼装女孩的坠落李玥最后一次见到安安是在4月15日,安安从迪拜跳伞基地回国,刚在上海结束了14天的隔离。
李玥去她的住处帮忙收拾行李,在各种零碎的日用品和衣物中,李玥一眼就看到了那两件“与众不同”的衣服,一件是彩色的、一件黑白相间,两件衣服的双腿、双臂和躯干间缝着大片结实的布料,像被安上一对巨大的“翅膀”。有跳伞经验的李玥很快认出来,这是两套翼装飞行服。
“我告诉她,虽然翼装飞行比较酷,但是危险系数很高。”对于好友的嘱咐,安安只是笑笑,说不用担心,自己心里有数。但安安没有告诉好友,她的下一个挑战目标,是众多翼装飞行爱好者向往的、难度系数极大的张家界天门山。
作为跳伞运动的分支,翼装飞行从飞机、峭壁等高处一跃而下,运动员凭借肢体动作来掌控滑翔方向,用身体进行无动力飞行,在到达安全极限的高度后打开降落伞着陆。
相比于传统的跳伞运动,翼装飞行停留在空中的时间更长,速度也更快。运动员以每下降一米前进三米的速率滑行,即使初学者也可以达到时速一百公里。在天空中快速俯冲,以自己的身体操控一切,头部的偏转可能改变方向,手臂的角度则会影响速度。这是一个需要一直心无旁骛的过程,直到最后,身体感受到降落伞撑开时的巨大冲力,才意味着一次飞行即将安全结束。
一位翼装飞行教练向深一度记者形容,“那种感觉好像在高速路上开车,轻微碰下方向盘都可能偏移很多。”
安安参与的是一家传媒公司在天门山取景拍摄的极限运动纪录片,按照计划,5月12日,她将从天门山上空约2500米的直升机上跳下,控制翼装进入绕山路线,在飞过几个山顶的摄影机位后,打开降落伞着陆在山脚停车场。
事后,有资深翼装飞行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安安的方案,从2500米高的直升机上起跳,属于高空翼装飞行范畴,原本难度和危险相对更低。但因为她计划飞过几个山头的机位,又要进入低空翼装飞行区域,这就加大了完成难度。同时以安安300次左右的飞行次数,在国内算不错的水准,但放眼国外,仍然属于新手。
5月12日和14日,李玥两次在微信上联系安安,都没得到回复,她有些担心,以前安安再忙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几天后,李玥看到了新闻,一名女翼装飞行员在天门山偏离航线后失联。新闻的照片里,那件黑白相间的翼装飞行服又一次出现在了李玥眼前。
李玥的的朋友圈有二三十个和安安的共同好友,安安失联后,很多人都发文祈祷她能平安归来。但最终没有好消息传来,5月18日,安安的遗体在一处密林内被发现,经过现场核实,她的降落伞处于没有打开的状态。

安安在滑雪场的留影
极限之路多位朋友回忆,和许多极限运动爱好者一样,安安是从门槛较低的滑雪开始的自己的挑战。
2015年,安安来到河北崇礼,一开始她就选择了对初学者要求更苛刻的单板。安安在运动上的天赋和勤奋在那时开始显现,一般人需要三天掌握的基础技巧,她半天就能学会。安安通常会出现在雪场每天第一班缆车上,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一个冬天后,她就适应了不同难度的雪道。
安安也不害怕运动带来的伤痛,在一次尝试高难度动作时,她摔得手骨错位,为此养伤两个月。一位雪友记得,安安没哭也没抱怨,反而说:“受伤可以证明自己的经历,还挺开心。”
滑雪之后是难度更大的潜水,安安依然适应得很快。19岁那年,她在巴厘岛学习水肺潜水,考下OW(开放水域潜水员)和AOW(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潜水证,能深潜30米。20岁时,她学会了自由潜和冲浪,还通过了AIDA自由潜最高级的四星考核,能够在水下闭气3分30秒。
开始接触门槛更高的跳伞运动,安安仍然在展现着自己的天赋。首先是学习基础的伞控、降落知识,若想在空中做出技巧性动作,还要经过模拟高空中气流环境的室内风洞练习。身处其中,训练者就像是“一只被扣在玻璃杯里的苍蝇”,极难掌握平衡。安安在21岁开始玩“风洞”,也完成了自己的二百次独立跳伞。22岁,她参加全国风洞锦标赛拿到了第三名,并且正式开始学习翼装飞行。
从北京出发,飞行10个小时跨越6700公里,前往迪拜沙漠基地,那里是全世界最大的跳伞基地,这是过去几年安安常走的路线。
“我们之中只要有人去,就会问一下跳伞圈子里谁有时间一起。”翼装飞行爱好者夏禾曾几次和安安一起去迪拜跳伞,同行的几位朋友提前合租一间公寓。其中安安的年龄是最小的,却很懂事,每天早起为大家准备早餐,“长的漂亮,情商高,交际强”是大家对她的普遍评价。
夏禾能感觉到,安安很想在这项运动中“拔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安安会珍惜每一次练习跳伞的机会,甚至会早上五点就起床去基地训练,连续完成八跳甚至更多。天黑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公寓,她还要回顾当天的飞行视频,总结不足的地方,跟同行前辈请教。
陈彤和安安认识了3年,一直没见过面,安安羡慕陈彤会攀岩,一直说要找他学习。从这个女孩身上,陈彤能看到对极限运动十足的热爱。
安安曾问陈彤,认不认识奥地利红牛集团的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极限运动赞助商,但在中国国内,极少签约运动员,“这是很多人看来遥不可及的梦,她却敢想,这个女孩真挺酷的。”
陈彤没想到安安会去天门山进行低空翼装飞行,他此前知道安安接了一个极限主题的纪录片,以为只是拍摄潜水、滑雪和高空跳伞,“天门山这个地方还是太危险了,国内飞过的人不多。但仔细想想,这确实符合安安的性格。”

安安朋友圈最后定位在张家界
风险与规则夏禾没想到,安安的离去,会让舆论把更多矛头指向翼装飞行运动,“死亡率30%”、“玩命儿”、“不负责任”,连串类似的评论让整个圈子都受到了震动。夏禾想解释极限运动不是大家认为的那样,其中当然有风险,但也有规则存在。
成为翼装飞行者的前提是积累足够多的跳伞经验,通常经历200跳才可以进阶尝试高空翼装飞行,跳伞以及高空翼装飞行累计400次才可以尝试低空跳伞,低空跳伞累计100次才能尝试低空翼装飞行。
相比从4000米起跳的高空翼装飞行,从山、桥等较低处起跳的低空翼装飞行更有难度,垂直距离不同,容错率也不一样。低空翼装贴近山壁、飞行速度很快,所以对开伞速度要求更高。
路线高度、水平落差、障碍物、天气和风力,一系列因素都被纳入前期准备工作的考量,一名翼装飞行教练形容,这好像在进行一项“工程”,要做的调研有很多。
跳伞和翼装飞行次数累计300跳经验的夏禾表示,翼装飞行作为跳伞进阶,对人的身体承受能力以及学习悟性都有更高的要求。他承认,很多人尽管具有200跳的经验,也达不到翼装飞行的水平。
为确保翼装飞行者的安全,初学者必须从小翼装穿起,随着技术的进步,才可以飞更大的翼装,这不只是简单飞行次数的累积,而是能力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展现,“相比小翼装,大翼装的飞行速度会更快,伴随着风力,越大的翼装越难控制,安安这次使用就是大翼装。”夏禾说。
在天上也有些明确的规则要遵守,两人有相撞风险时均向右转、严格按照规划的路线飞行、不轻易去穿越云层等等,“能走到这一步都是脚踏实地慢慢积攒的,跳的越多,越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也要对身边飞行的好友负责”,夏禾说道,“网传所谓的30%死亡率其实不真实,顶多可能出现概率在3%-5%的小问题,但是都可以解决,因为这套装备已经非常先进和完善,可能出现的问题有限。”
陈彤已经完成了198次跳伞,距离翼装飞行的门槛只有一步之遥,他也想用自己的实际经历解释,看似“玩命”的运动背后,有着一套严谨的流程。
陈彤说,接受专业跳伞训练的人员会先在地面进行足够多的模拟操作,直至形成肌肉记忆,教练会反复提问跳伞突发应急问题,登机前所有人都需要接受四次全面安全检查,每个人都有主伞和副伞,若发生突发情况导致主伞未打开,副伞会在800m左右的位置自动打开,“除了装备问题和地形中的不可控因素,跳伞安全性极高,想自*都很难。”
陈彤记得自己第一次站在直升机舱门前,因为恐高,吓得面目狰狞不敢下跳,教练直接让他挂了科。他用半个月时间不断练习,直至前八级跳伞全部合格,才拿到跳伞执照,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安安已经进行了器官捐献登记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至少在大一那年,同学眼里的安安还只是一个打扮略成熟、相貌出众的女生。一位同级的朋友回忆,15年9月她们一起军训,休息的时候,安安会坐在操场边分享高中时偷溜出去买吃的或是逛街时的趣事,那时安安朋友圈的内容与同龄女孩没什么区别,自拍、逛街,以及生活中的小吐槽。
改变始于安安开始接触职业运动,在同学嘉伊看来,安安是年级里耀眼的存在,但明显和大部分同学“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太合群,特立独行,很酷的存在”,年级里的男生都称安安为“安姐”,每当安安在朋友圈更新动态,都会引来一阵讨论:“快看!安姐又发了照片。”
嘉伊也经常会关注安安的朋友圈,那里有她向往却很难抵达的世界:在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如风一样高速掠过,溅起一片飞扬的雪雾;从几千米的高空一跃而下,以上帝视角俯瞰迪拜苍茫的沙漠;在海里优雅地扬起脖颈,几串水泡缀在周围,背后是错综的海底岩石......
嘉伊觉得安安不怎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只想要自己的“快乐与自由”。矛盾的是,以她在极限运动上投入的精力似乎很难兼顾学业,但在大一大二时,安安缺课还不是很严重,一周能来上三四天课,在学习滑雪和潜水的同时,还能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一个不错的分数,“其实她很聪明,突击复习几天也可以拿下考试。”直到大四,安安因为学分不够,被学校延毕一年。
安安离去之后,引发的另一重争议在于,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参与极限运动,丰厚的物质基础似乎是绕不开的门槛。这也是夏禾想反驳的一点,他算了一笔账,从零基础开始学习翼装飞行需要200次跳伞经验,每次200元,一套降落伞的成本大概在5万左右,总计大概10万元,继而学习翼装飞行的课程费 2000元人民币,一套翼装的价格在1万到1万5不等,结合交通费,整体下来花费十几万元。
相比金钱,还存在着一些隐性的投入。在迪拜训练时,夏禾能明显感觉到安安作为一名大四学生的不同,她要兼顾学习与运动。“去年安安要准备考研究生,白天跳伞,晚上复习功课”,于是夏禾和几位研究生毕业的朋友去为安安寻找资料,帮她分析如何复习。
这与陈彤观察到的圈里人类似,他曾见过有人为了攀岩,一家三口从北京搬去大理卖包子;有人为了每天能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选择去海边卖鱼;而陈彤自己则拒绝了一份月薪2万的白领工作,带着团队开始创业。
回到学校,安安为极限运动的付出更多与伤疤有关。几次在楼道里遇见,嘉伊能看到安安身上又多了几处创口贴,膝盖上还有块半个巴掌大的伤疤。嘉伊没有听到过安安的抱怨,她只会自己一个人安静的给伤口消毒、缠纱布,手法娴熟。偶尔她会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下自己受伤的照片,但也会很快删掉,“她在朋友圈里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比较美好的瞬间。”
在嘉伊的视角里,安安还有着“小女生”的另一面。她喜欢小猪佩奇和皮卡丘,一次高空跳伞,出发前,她用佩奇布偶的鼻子轻轻碰了碰镜头,然后抱着粉红色的布偶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有一次朋友抓了一袋子娃娃给她,她挑了几个分给舍友们,剩下的都摆在了自己床头。
安安还喜欢化妆,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化妆品,只留下了一张A4纸那么大的空地,她从不吝啬把自己化妆品外借,会对舍友说“尽管用”。
嘉伊在去年毕业,已经很久没见过还在上学的安安了。两人不常联系,看到天门山翼装女飞行员去世的新闻时,嘉伊和朋友们都觉得不敢相信,“怎么可能是她?”
再三确认学校、照片等信息后,嘉伊有些难过,更多的是惋惜,“我们以前开玩笑,觉得她是能一直蹦迪到40岁的那种人。”

电影《极盗者》中的翼装飞行画面
余波2016年,夏禾刚开始学习跳伞,摇摇晃晃慢速下降的时候,看到远处空域出现了几名翼装飞行员,他们以编队的方式从夏禾眼前疾速划过。那种感觉像是看台上的观众,看着一辆赛车从弯道上呼啸而过,一股强烈的速度感扑面而来。“200公里每小时,那不是飞机,那是人!”
夏禾的初心也是如此,他觉得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在天空中飞,是件挺开心的事,“翼装飞行飞到最后,就是在飞自己。”
夏禾说他已经看过了安安事发时的全程视频,但目前他不想分析或评论什么,“一切以最后的正式报告为准。”夏禾现在更想强调的,还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和规则:不同水准爱好者之间相互的切磋交流,以及大家对生命的尊重,一起飞行时,没有谁会随便乱动别人的装备。
他不喜欢“挑战”这个词,因为大众习惯了用“挑战”解读极限运动。在夏禾看来,这个圈子普遍具有强烈的目标感,面对问题死磕到底。“我们之中没有人会拿生命去冒险开玩笑,我们会设立一个目标,投入时间、精力、金钱、体力,我们的笔记本记满了知识点,需要反复琢磨视频,不断的总结,一步步实现目标,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是挑战。”
26岁的女孩多多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正在练习跳伞,翼装飞行是下一个目标。多多不认识安安,但一直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极限运动让我变得更加热爱生命。”多多解释说,因为有过失去,所以变得更加珍惜,比如她在一次跳伞降落时伤了脚,她原本是脾气很急的人,登机时却要一瘸一拐的从残疾人通道经过。那时她才意识到,靠着两只脚顺顺利利走上飞机,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只有活着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只有活着才能当大神,我想跳伞跳到80岁。”
多多所在的跳伞群里,大家几乎不再讨论安安的意外。多多认为,在极限运动爱好者这个不大圈子里,这是一种刻意的保护,“即使我们说了,外界也没法完全理解。”
安安离开的第七天,多多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If I Die Young(如果我英年早逝)这首歌,还有她想对安安说的话:“对于极限运动的热爱,活着的我们会好好延续,血的教训也会牢牢记得。”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本文由作者【北青深一度】创作,在今日头条独家首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