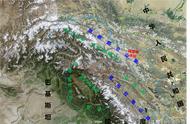阳台上七八个花盆,靠墙边一字形排开。每个花盆,都换上了新土,种上了加兰菜、香葱、韭菜、茄子、番茄、小米椒等。天气晴好,阳光和煦,宽阔的阳台上增添了几抹新绿。
母亲蹲在一个大花钵前,端祥着花钵里细细的土。几天前,她在这个最大的花钵里,将黝黑饱满的丝瓜籽点播在土里,母亲说,用丝瓜囊洗碗,比铁丝囊、洗碗布好使多了。
没想到我出差只走了几天,家里的露天阳台就变了一个样。
“妈,那些花盆,我可是准备种花的呀。”原本在阳台上种些茶花、米兰、杜鹃、兰花什么的,看书累了,也好舒活舒活筋骨,养养眼。
母亲笑了笑,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还是种菜好,花只能看,又不能吃。”

只要母亲开心就好。母亲已年过八旬,下城居住也十多年了,可她一直还闲不住。我知道,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离开了土地,会闷得慌。
“如果旁边有个菜园就好了。”母亲几次这样喃喃地说。
可这不是乡村,而是县城,房子又临街,寸土寸金,别说园子,就连院子,按统一规划也难于安排,哪来的菜园呀?
我知道,母亲又想她的菜园子了。 记忆中,母亲最早的菜园是家里旁边的那块宅基地。那时还是生产队时代,土地是集体的,各家都没有自留地,也不允许私自去开荒种菜,家里旁边的那块约四五十平米的老宅基地,便被开辟成了菜园。记得那年冬,母亲搬开依墙堆放得小山似的柴火,领着姐姐从远处挑来一担担土,用鸡粪、草木灰等拌好,把土伺弄得像过了筛一样细,为防止鸡鸭狗之类的来侵扰,门口安放了一道用竹片扎成的篱门。母亲房间里的桌子上,一个个小玻璃瓶摆放得整整齐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蔬菜种子。母亲没念过书,认不出几个字,但对这些蔬菜种子,却分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母亲带着大姐、二姐在菜园里忙碌开了。开行、施肥、培土、浇水,母亲将一把把蔬菜种子撒进土里,将红苕、板薯、芋头等插入土槽,培上土。一枝桃花从墙角斜伸过来,几只蝴蝶上下翻飞,风里带着花和青草的香。母亲在点播过南瓜仔的地方撒上草木灰,轻轻培上土,再在土上摆放几枝杉树枝,说这样既可遮阳,又能防止鸟或老鼠把种子偷吃。没过几日,菜园的土里便钻出了鹅黄的嫩芽。花生、玉米、梅豆、南瓜、丝瓜等发芽了,点播的行列整齐,撒播的万头攒动。一颗颗南瓜芽钻出土面,芽的顶端还夹着灰色的瓜子壳,如举着帽子欢呼呢。南瓜秧的叶子绿白相间,油光发亮,没几天,便长出了毛茸茸的叶片,二片、四片,这时候,母亲便把土上的杉树枝挪开,说要给南瓜苗腾空间了。梅豆、四季豆的苗开始伏地的时候,母亲便将梅豆秧牵到墙边的木条缠好,又从山上砍来小山竹,分别插到每株四季豆苗旁,拦腰用一根竹子将每根竹子固定好,四季豆便开始沿着竹杆往上攀援,土里很快就长起了一道绿色的“屏风”。等到初夏时节,菜园里早已葱绿一片,热闹非凡。梅豆、丝瓜爬上了一旁的矮墙,花生青翠的叶间缀着米黄的花儿,玉米已长得袅袅娜娜,南瓜也爬满了早已搭好的木架。辣椒、茄子开着白花和紫色的花,青葱的黄瓜藤缀满手指大小剌突突的小青瓜。白天,蜜蜂、蝴蝶在这里飞舞;夜晚,蟋蟀、蛐蛐在这里欢唱。小时候的我,常邀上小伙伴,到菜园里捉虫子,挖蚯蚓,用饼干屑引蚂蚁,提水灌老鼠洞。菜园,成为我童年时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