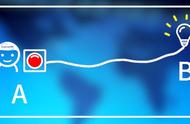“我吃你买的东西,
花你的钱住医院,
我没有做好叔叔交待的事情,
但我会回报,
爸爸说过,
得到就要有所付出。”
珏城凤台大道拐进西环路刚走五百米,是距离城区最近的王屋山森林公园,过了夏天,枫叶纷飞,但气温不降,人们依然可以在刚见到太阳的时候来散步晨练,东口走到西口也就五公里。
我们在半山腰一处隐秘的茂密林中挖出一具尸体,腾寅,男,九岁孩童,被掐死,身上多记击打伤,这些伤口形状各色各样,有藤条、晾衣架、鼠标、擀面杖,巴掌印和脚印就更不用说。我国每年遭遇意外死亡的儿童特别多,这些小死者中有三分之一死于凶*,三分之一死于家暴,你没听错,是家暴。

半山腰一处隐秘的茂密林
警方在半天内就找到了凶手。
当时,他们正在自己的小区房里开着派对,酒还没醒就被捕,那个一边说着“青春万岁”一边唱着民谣披头散发的女人还吐了我一身。男方是孩子亲生父亲,二十来岁,没工作,整日游手好闲,沉迷绝地求生,热衷夜店轰趴,被女方供养,女方是个人民教师,和男方认识两年,与死者没有血缘关系。
可笑的是,在警方的盘问下,男方率先招供,掩面流泪说自己那天和女朋友喝醉酒大吵一架心情不太好就对孩子下了手,可惜女朋友下手太重,把孩子掐死了,只好连夜开着车悄悄埋在了就近的山里。女方却一口咬定孩子是男方掐的。
这肯定是死罪,我们都以为事情很快会结束,然而我们忽略了身份背景的重要性。几日后,才得知女方的父亲是当地化工集团的总经理,雇了批优秀的律师,把罪责降到了最低,由于被告双方各执一词,证据又不太充分,但孩子家暴致死的原因是毋庸质疑的,最后俩人判了十年,女方缓刑五年。
说到这里,我知道大家都很想骂脏话。像是这样类似的案子,有很多根本无法结案,因为警方不是第一时间发现死者,而是通过某地区邻里间“酗酒父亲、吸毒母亲打死了孩子”的这类传言,往往知晓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甚至取证都非常困难。而那些罪魁祸首会以受害人的身份抱着被*死的孩子遗像在出殡当天大哭,希望他们是真的在对老天爷忏悔,以便他们活够生死簿的记录在牛头马面的行刑下给他们一个全魂。
作为一名协勤警,我忠心祝愿他们活不过生死簿的记录,成为孤魂野鬼,被人间的阳气日日拷打。
1
受过家暴但并没获得拯救的孩子,此后余生注定与寻常人有着一条鸿沟。这些孩子要不是致死,要不精神崩溃,变成一个病人或者一个疯子,哪种结局听起来都是那么地不入耳。这是我亲眼看过腾寅的尸体后才明白的道理。所以在经过凤英社区上坡口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
那个女孩经常站在这个风口,无论风从哪个方向吹来,都会经过这个小十字,她就立在那里,穿着条棕黄色的针织长裙,脸上不算干净,但也不脏,头发很油,像是个流浪儿童。我因为工作调动刚搬来这个社区不久,街坊都说她是上坡第三家的女儿,不上学,因为脑子有问题。我没怎么在意,或许她只是喜欢在深夜吹风,当然那时我也没有往家暴的方向想,毕竟我在她的身上没看到任何伤口。
刚上坡没几步,我看了看第三家,没有灯光,门是虚掩着的,估计他的父母已经睡了,怕她进不去家,专程开着门,我看了眼时间,凌晨一点,这个怪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路灯下,怪让人担心的。我没再走,身子贴在墙上点燃了根烟,以免被误以为坏人,我拿出证件走向女孩刚要开口,女孩怯生生地看着我说:“叔叔,可以给我一根吗?”
我抽口烟皱了皱眉说:“未成年人不能抽烟。”
“我很饿,但是我听爸爸说你们大人抽这个就是为了抗饿。”
“你晚上没吃饭吗?”
女孩看着我不说话,我挠挠后脑勺,站在第三家的门口敲了几分钟的门,没人应,只好折返回来问女孩:“你家里人呢?”
“爸爸出去工作了。”
“所以你晚上没有吃到饭,就跑到这里喝西北风?不对,还没到冬天,吹得还是东南风,小朋友,大晚上待在户外很危险知道吗?赶紧回家,翻翻冰箱什么的,里面你爸应该给你留了吃的。”
“家里没有冰箱,也没有吃的,我翻遍了厨房。”
于是,我大发慈悲心,带着女孩吃饭。没走太远,就近的小吃城,俩灌饼,一盘炒米,一份肉丸汤,她很快朵颐结束,抱着那份奶茶迟迟不愿插管,我问她怎么不喝,她说这么甜的东西要藏起来,痛的时候就喝一小口,这样就不会那么痛了,她露出一丝僵硬的微笑,耸起肩,领口太大,左边落到了肩上,这才发现在她肩背部的几条伤痕,经验告诉我这是长方形条状物击打造成,我帮女孩拉起衣领,喝光了那罐啤酒。
把她送回家后,我停留了一会儿,没怎么翻动,却拍了许多准凶器,有条皮带甚至还带着干涸的血迹。女孩脱下袜子,脚颈是绳子勒痕,我迅速按下快门,闪光转瞬即灭,女孩还以为是流星,兴奋地跑到窗边,可惜乌黑的天空什么都没有。
2
凤英社区正好在我们所的管辖范围,当我把这些拍来的照片放在今天的晨会时,被同事群起攻之,骂得狗血淋头。因为这有可能落下一个非法取证的罪名,没有收到报案,就不能当作案件处理,我昨夜的行为在他们眼里算是一种越界。

拍下来的照片
我努力跟他们说照片中的女孩有着充分的被家暴虐待嫌疑,他们却不这么认为,说我作为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对待事物太过敏感,告诫我这只不过是一个父亲在教训自己不听话的女儿,至于绳子勒痕,他们一致认为这些伤口很浅,不是穿劣质鞋子的原因就是玩跳皮筋的原因。去他妈的,这个年头,在一座被智能手机和科技教育融化的城市中还有孩子会玩跳皮筋?
我可不会蠢到和他们吵架,情绪激动会显得不理性,一旦失去理智,说出的话可信度会更加降低。
为了不强迫自己受气,我选择擅自离岗,免得坐在办公室里看他们喝茶自个堵心。所长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我自由,反正这公益岗位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政府对失业青年的一种救济。
我这人生活其实很单调,但又想追求丰富,不停地去挤进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永远都在边缘,随时都会被挤出去,所以在我打完麻将喝完酒唱完歌后,夜色终于变深,疲劳让我恋睡。
醉醺醺地走回社区巷子,懒得睁眼,走了百遍,即便我五官丧失,都能凭着记忆爬回去,直到我听到有人喊我,迟钝的神经变得敏锐,摇摇晃晃地转过身,面前是那条斜坡,半坡上站着个男人,手里拿着杯奶茶,我皱皱眉站住,男人主动走过来把奶茶揣进我的怀里,不是热的,很冰,他抬起头看向我,默默地点燃根烟,抿了口说:“你昨天带我女儿去吃饭了?”
“什么?”
“我女儿吃坏了肚子,拉了一天,你看看怎么处理这件事?”
我把奶茶盖掀开喝了口,液体刚落嗓子眼,就感到剧痛,全吐到了地上,这下彻底清醒,我看看奶茶,再看看男人,指着他说:“你就是那个打孩子的爹?”
“你说啥?”
我揪起他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以后要是再让我见到你打自己的女儿,我就把你抓起来,和强奸犯关在一起。”
“神经病吧你!”
接着,我挨了记拳头,两人就厮打到了一块儿,惊扰到附近的住户,窗户纷纷亮起灯,大家穿着睡衣披着外套踩着拖鞋来到巷子,没人拦,就站在旁边拿着手机看戏。也许其中有人报了警,不然后来我也不会坐在所长面前,一脸享受地迎接他的唾沫星子。
一番谩骂后,所长有些累了,坐下来重重喘气,啤酒肚一凹一凸,有些可笑。他喝了口茶,把吐出的茶叶扔向我说:“你小子笑什么笑,堂堂人民警察公共区域打架,真丢脸!”
我嬉皮笑脸地从身上把茶叶捡掉说:“所长,那人是个罪犯,他就是我今天早上说得那个虐待孩子的父亲。”
所长指向大厅内坐着的男人说:“你瞧瞧人家,西装革履,戴着眼睛,文质彬彬,再看看你,穿个花衬衫,整个爆炸头,谁像罪犯啊,你身为一名执法者业余时间注意下自己的形象,还好人家不追究,不然你就惨了。”
“那我待会儿是不是可以审一审他?”
“啥玩意儿?审什么审!滚蛋!”
3
当晚的口供笔录,让我得知这爷们叫付建树,在当地一家洗煤厂做管理,有个老婆,因为病重,五年前去世,留下个脑袋有问题的女儿,叫付小余,那天站在巷子十字口吹风的女孩就是她。我十分笃定,她在那个家庭正在遭受非人的待遇,可惜得到的证据并没什么用处,我确实想过放弃,但在周六的下午,睡醒的我出门又见着付小余,依旧站在那个风口,穿着脏兮兮的针织裙,脸上多了块淤青,蔓延了大半个眼。

洗煤厂
付建树这个畜生!我抓起她胳膊,踢开了门,恶魔早已逃之夭夭。
我双手掐腰,看着一脸漠然的小余,抬起手有些心疼地摸了摸她头说:“你是叫小余对吧?”
她没有回答,我又说:“小余,你在家里待着,哪也不要去,现在叔叔要去办点事情。”
我刚要转身,她就抓住了我的衣服下摆,回过头,看到她驼着肩,另外一只手捂着肚子,像是要哭出来,我问她怎么了,她迟疑半天,说了句:“我饿了。”
我控制住怒火,走入屋子拐进厨房,果然没有冰箱,翻箱倒柜半天才找到块过期的面包。看到面包的她脸色略显欣喜,指尖按着酒窝控制着自己不自觉的笑,我拿着面包摇摇头,把它扔进满是酒瓶和外卖盒的垃圾桶,她满眼不舍地看向垃圾桶,我无奈叹口气,脱下外套披在她的身上,把她带了出去。
坐在车里的她十分紧张,不安地看着那个导航传出的语音提醒。我发觉到异样,关闭掉导航,打开歌单想要找找有没有适合孩子听得歌,却只有一堆的DJ和情情爱爱,管她呢?反正也听不懂,随便点一首了,只要是音乐就能缓解压力,这是首上世纪的曲子,叫《追梦人》,节奏悠扬,旋律有那么一丝悲伤,小余痴痴地看着音响,流出了泪。
我计划带她吃顿大餐,因为我马上要去见一个姑娘,父母介绍的相亲对象,叫周钰,见过几次,还算谈得来,正逢周末,约饭约在家火锅店。我放不下爱的天性,更放不下善的责任,我决定带着小余去见那周钰。
把车停在家购物中心的地下车库,我想我应该先给这孩子买身体面的衣服,可惜整层的童装店让我眼花缭乱,随便找了几家,却因为小余个子太高找不到大码,我索性带她去了四楼的女装区,导购员乐此不疲给小余试了一件又一件,最后我冲那件粉色的风衣点了点头。

粉色风衣
火锅店不远,就在这里的六楼,周钰见我带了个小女孩,有些鄙夷地看着我,我说这是一个证人,她便让我和小余坐了下来,周钰看了看我放下的手提袋嘲笑我说:“你的眼光真差。”
小余不会吃火锅,看着滚滚的热汤拿着筷子大眼瞪小眼,我只好把煮熟的食物夹在她面前的碗里,在我夹第三次的时候,她抓住我的胳膊,自己伸手夹了块豆腐放进了我的碗里冲我发出胜利般的微笑,周珏用筷子敲了敲锅沿说:“田焰,她幸亏是个孩子,要不连我都觉得你俩有一腿儿,你看那含情脉脉的眼神,哎吆吆,你要是对我也像对证人这么好,我戒指都不要就嫁给你。”
我夹起碗里的豆腐吃进去喝了口水说:“你懂什么?我这是父爱泛滥,就等着你给我生儿子呢!”
“流氓!”
三人用餐非常愉快,还看了场动画电影,小余特别开心。本来今天顺顺利利,周钰完全可以在这个晚上成为我的女人,奈何我带了一个小女孩,只好心甘情愿地把周钰送回家,再开着车回到那个犹如迷宫般的社区。把车泊在停车区后,我和小余并排着走,走着走着,她就抓住了我的手,我装作毫无察觉。直到看着她回到家中,那灯没有亮起,代表混蛋至今未归。
我没有回家,而是开着车去了一趟派出所,在付建树的笔录中找到了那家洗煤厂的地址。我的车跨越了半个珏城,经过坑坑洼洼的山路,期间还复习了多次半坡起步,终于到达这家洗煤厂。煤在皮带上划过,融进深邃的夜色,运煤车的轮胎放了个屁,付建树挨了我一手铅。
4
下场显而易见,我被停职,事后周钰得知前因后果,骂我多管闲事,我果断与她不再往来。
自打那日起我再也没有见过小余,站在风口等了几天,按耐不住,闯进付建树的家,空空荡荡,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我叫喊着小余的名字,在屋子里寻遍了所有的房间,都找不到她的身影,不安感让我推开了卫生间的门,她在里面,整个人缩在浴缸中,只穿条底裤,遍体鳞伤。我取下浴巾披在小余身上抱起她,她被惊醒,不断地挣扎,发现是我后,便开始大哭,哭得我彻底心碎。
付建树推门而入,看到我并不惊讶,把手里的酒和花生米放在茶几上,摘下眼镜,坐在沙发说:“你想带我女儿去哪?去医院吗?你知道你的行为属于非法诱拐吗?”
“你个王八蛋!你把你女儿打成这样扔在卫生间就合法吗?少用法律威胁我,我才是执法者!”
“你停职了,没资格了!有本身你现在就带着她走,我立马报警!”
小余抓抓我的衣领说:“叔叔,把我放下吧,我没事,我喝点热水就好了!”
“警察同志,还不走?我女儿都请你离开了!”
我把小余放在地上说:“小余,你告诉叔叔,爸爸有没有打你,有没有对你做过分的事情。”
小余看着我摇摇头说:“是小余犯错了,爸爸才会惩罚小余,没事的,叔叔。”
“说实话啊,小余,你现在说了实话,叔叔马上就可以带走你爸爸,让他不能再打你。”
“没事的,叔叔。”
“小余你——”
付建树喝了口酒说:“警察同志,你该走了,我不告你非法擅闯民居就不错了!”
“我告诉你,付建树,我会在门口站着,如果我听到屋里传来响动,我会马上闯进来将你绳之以法!”
我庆幸自己是个警察,还有个刑警队长朋友。
离开后,我直接去公安局把赵焕拖了出来,跟他索取设备。听我一番讲述后他说:“老田,你疯了?你要偷拍人家?以前我允许你为所欲为,是因为事件已成案件,现在这种事情,道不清说不透的,我怎么帮你?”
我从衣兜拿出手机,打开相册,一张一张地给赵焕看,看到一半,他推开手机,扶着额头踢了脚身旁的汽车开始原地徘徊,最后把头歪向天空点了根烟说:“田焰,设备我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乱来,这事你也别找你们所了,有了证据我给你抓人!”

偷拍设备
隔日,我带着设备守在了付建树的家门口,等着他离开,却意外看到他带着付小余一同出了门,她穿得漂漂亮亮严严实实,把伤口全都挡在光鲜的衣服下。
付建树害怕了,因为我,他虐待孩子的事情传遍了整个社区,有时候普通人的舆论要比执法人的警示管用,他在做戏,想要用实际行动来挽回自己在街坊心中的形象。人啊,如此活着,连苟且二字都不配。
守在电脑前,日夜看着他家传来的监控画面,付建树演戏演得终于累了,在付小余打翻杯子后,他动手了,光在监控里看着就很惊心,那晾衣架硬生生给打断,小余躺在地上直哭喊。见状我扔下泡面,穿着拖鞋就冲出了家。
门被换了锁,怎么撞都撞不开,我太着急了,蹦上了院墙,下的时候还摔了跟头。正在施暴的付建树看到我,先是一愣,紧接着,拔腿就跑,我顾不上追犯人,我得先救人,小余的整个腰部被打得鲜血淋漓,我抱起她跑出巷子外,拦了辆出租直奔医院。
5
付建树很快被赵焕抓获,我懒得去审讯他,现在全心全意想要照顾身心支离破碎的小余。赵焕拿着我录制的视频与付建树对峙了整夜,没能让他招供,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在教育女儿,又加上了喝了酒,才下手重了点,还装作悲痛欲绝的样子在审讯室大哭,让赵焕无可奈何。
这招行不通,只能寄希望于小余的供词,我和小余促膝长谈几日,她才答应我同意指证父亲对她实施暴力虐待的指控。因为家庭暴力这个罪责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在赵焕呈报给上级后,打算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可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和一个施暴的父亲该如何调解,这太魔幻了,我不答应,便去了趟儿童保护机构,他们答应我对付建树提起法律诉讼。
开庭当天,我作为证人参与庭审,因为证据充足,进程特别顺利,直到小余坐到证人席位上被律师逼问得说不出话。这就难办了,因为这场庭审只需要小余一个肯定就可以令付建树得到法律制裁,可是,小余什么话都没说出口,转头看着我不停地说:“叔叔我怕。”
庭审被迫延期,我有些沮丧,让护士带着小余回医院,拉着赵焕喝了顿酒。散场的时候,小余用医院电话打来说想吃汉堡,我只好去肯德基买了份全家桶。回到医院的时候,小余正在看电视,动画片,名侦探柯南,是我专门在平板里下载的,她对我说将来一定要做个侦探,像柯南一样,像我一样。我说我又不是什么侦探,她说我和柯南一样都是在抓坏人,我把全家桶放在她的小桌板上说:“你现在敢说你爸爸是坏人了,为什么在法庭上不说呢?”
小余正咬着汉堡突然就不咬了,她说:“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一直在用那个眼神看我,我很害怕,他只要有那个眼神,就会打我,就会对我做过分的事,特别疼,特别痛。”
“没有人敢打你了!有我在他不敢打你,也打不了你!下次在法官爷爷面前一定要说知道吗?”
“可我还是怕。”
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扶扶额头,情绪失控地说:“你怕什么啊!现在你在我身边好不好,我这么让你白吃白喝供着你,怎么就一点都不给叔叔长脸呢?”
小余忽然用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看向我,让我有些发憷,她放下汉堡,从病床走下来,挪到门边关严了病房门,回身站在我的面前解开了病服上的扣子,我满脸疑惑地看着她说:“小余,你干什么呢?”
“我吃你买的东西,花你的钱住医院,我没有做好叔叔交待的事情,但我会回报,爸爸说过,得到就要有所付出。”
我抓住她将要解开第二颗扣子的手说:“你爸爸真的这么说过?”
她点点头。
“怎么可以这样。”
我帮她紧上扣子,想要把她抱上病床,这一刻,却变得迟疑,我只好有些无力地说:“早点睡吧。”
走出病房,我推开了主治医生办公室,翻出小余的诊疗纪录,事实被应验。
6
带着某种预感,我委托医院做了亲子鉴定,确定付建树和付小余没有血缘关系,赵焕得知消息后骂了整整两分钟。
在小余的身体上取到付建树性侵的证据样本后,他的罪责终于落实,可是仍旧存在疑点,如果俩人没有血缘关系,那么付建树和付小余究竟是什么关系?
“十二年前我老婆*,九个月后顺利诞下一个女儿,取名叫小余。可惜好景不长,小余发高烧夭折了,我老婆痛不欲生,开始自言自语,就像疯了一样。某一天她出去后带回来一个女娃儿,跟我说小余找到了,我猜她应该是买来的。我很爱我的老婆,不想让她伤心,就配合她。但亲生女儿的死,我比老婆还要悲伤,只是没表现出来而已。两口子要是都垮了,那家就不是家了。后来这个女婴一直用着小余的身份,日子就照常过了下去。
五年前,老婆得了病,没得治那种,不到三月就走了,留下我和这个女孩。其实我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个女孩,一直以来的伪善只不过是在迁就老婆。但是老婆死了,只剩下了我,我还有什么可迁就的。我不想养她,想过各种办法把她从我身边支走,可她总是能找得回来,我没办法。就算不让她上学,不给她饭吃,揍她,可她还是一直叫着我爸爸,真的很烦,让我越来越讨厌,但我又不敢*人灭口。
其实我是个性欲挺强的人,特别喜欢去风月场所,玩过很多女人。有一天我喝了酒回到家,抽了两口茶碱,看到她从卫生间出来,穿得很少,我就扑了上去。那时候她很小,所以没进去,后来又试了很多次,直到我可以进去,再后来,呵呵……”
这是付建树审讯时说的原话,我没听下去。后来我没再跟进案子,法律终会给出应有的判罚。
小余健康出院,被暂时安排在了儿童救助机构,闲暇的时候我会带着玩具和零食去看她。她说她喜欢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对她很好。但她依旧喜欢站在风口吹风。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喜欢吹风,她说小的时候妈妈给她讲过一个童话故事,故事里说,风是最干净的。
(文/田烨然,本文系“人间故事铺”独家首发,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