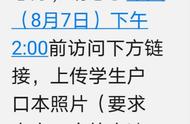佛国,是敦煌的另一个名字。即使是在当代,敦煌城市的建设者们也着力将这里打造成一片神佛相会之地。佛陀说法时洒下漫天花雨的飞天,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十字路口的雕塑、路灯上的装饰、酒店的大堂,饭馆的招牌,乃至道路上的画砖。她们轻盈飘然的曼妙身姿,飞扬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仿佛裟椤双树下的佛陀特意从印度跨越时空赶来,面对这里的游客讲经说法。
所以,无怪乎今天来到敦煌的旅行者,大都会带着一种瞻仰奇迹的朝圣心情。朝圣的中心,就是莫高窟。雄浑连绵的崖壁上,布满佛龛的莫高窟如今已经是敦煌的象征。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敦煌》中,莫高窟几乎等同于敦煌。这座千佛汇聚之所,让敦煌成为名副其实的佛国。但就像前面已经描述的那样,敦煌并不只有莫高窟。同样,在敦煌,莫高窟也不是惟一的千佛洞。与它相隔一座鸣沙山的地方另一端,同样有一座布满洞窟的崖壁,被称为“西千佛洞”。
撰文 | 李夏恩
01
西千佛洞
尽管“西千佛洞”这个名称,很明显是以“千佛洞”莫高窟为中心的陪侍。但根据文献记载,它的开凿时间比莫高窟更加久远。初唐时期的《沙州图经》援引一本魏晋之际成书的《耆旧图》称“汉……造一佛龛,百姓渐更修营”,似乎在汉代,这里就已经有人开始修造佛龛。魏晋之际,敦煌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西北地方的佛国。《魏书·释老志》里这样描述晋末十六国时代的敦煌:“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公元400年,高僧法显一行抵达敦煌,在敦煌修养一个月后,西出大漠,开始了他史诗性的西行求法。

西千佛洞
在法显记述其求法旅程的《佛国记》中,曾经多次提到一种佛教圣迹——石窟。这些石窟是当年佛陀坐禅入定和阿罗汉结集经之处,它们有些是自然的洞穴,但也有人工开凿的石室。在佛陀寂灭后,这些作为圣迹的石窟往往会供奉佛影或是佛像。这种凿山为窟的风习同样也通过中亚传播到敦煌地区。西千佛洞的开凿,或许正是法显所见到的石窟在敦煌的复刻版本。只是它早在法显西行之前,就已经开工。而后,公元366年,也就是法显从敦煌西行求法的34年前,由一位叫乐僔的法师首先“造窟一龛”,接着,又有一位名叫法良的禅师自东来此,“于僔师龛侧,更即迎建”。开启了敦煌的佛国时代。
然而,西千佛洞的参观者或许会对这里感到失望,尽管这里的风景比莫高窟更加秀丽,古木苍天,长河蜿蜒,更符合人们心中的佛国净土形象。但经过清点,这里的洞窟只有16个,最早的第7窟建造于北魏末期,比莫高窟现存最早开凿北凉时期的275窟要晚出将近80年。而这还算是西千佛洞仅存的硕果。来访者会发现西千佛洞的崖壁上有许多洞穴,里面积满碎石沙土——它们是昔日的洞窟,千年来的风沙侵蚀本就让它们性命危殆,夏季暴雨导致的洪水,则给了它们致命一击。许多洞窟被冲毁,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文献中记载的那个开凿于汉代的佛龛。

西千佛洞周边的自然景观。
但纵使如此,西千佛洞仍然保存了一些莫高窟难以得见的微妙细节。在第7窟的顶部角落里,居然留下了画了一半的飞天,朱红色的轮廓仍然留在墙壁上,但画师却没有给它添上眉眼衣着和颜色。这片古怪的红线草稿就这样留存千年,同样未完工的,还有一尊塑了一半的佛像,充当骨架结构的木棍和稻草从包裹的泥胎中滋露出来,龇牙咧嘴地望着困惑不已的参观者。这些半成品固然让人可以了解那些美不胜收的敦煌壁画绘制的初始过程,但对富于想象力的参观者来说,它们倒更像是不情不愿的工匠在罢工示威,对他们的不公待遇表示抗议。

被洪水冲垮的洞窟。
默默无闻的匠人,可以说是敦煌石窟工匠们的群像写照。在石窟的壁画中发现人名并不稀奇,壁画下方那些供养人的旁边总会有块带颜色的长条榜题写上他们的姓名。除非岁月侵蚀磨灭了这些墨迹,不然他们的名字终会留存于世。但他们只是投资人。真正的营造者却很少留下姓名。在莫高窟的290窟的壁画中,出现了辛仗和、郑洛仁这两个名字,现代学者们认为他们应该是画匠的姓名,但这些姓名并没有正式地写在供养人的旁边的榜题上,而是被覆盖在壁画层的下面,这多少能让人感到一种面对自己的作品想留名而不得的无奈。惟一一个大胆的画师,有个霸气凌人的名字:“平咄子”。他很大方地把姓名签在了莫高窟303窟一幅僧人供养像的旁边,字写得比画像还要大:“僧是大喜,故书壹字。画师平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