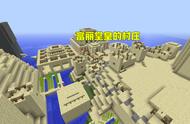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明代董其昌晚年时,将《富春山居图》以高价卖给了宜兴收藏家吴之矩。吴之矩的三儿子叫吴洪裕,酷爱收藏到了不愿做官的地步。吴之矩临死前,将《富春山居图》传给了这个儿子。
吴洪裕花巨资为《富春山居图》造了一个楼,唤作“云起楼”,楼中藏图的那间屋子当然就是“富春轩”了,这里,也成了吴洪裕一生最爱的地方。
然而,人总是要死的,吴洪裕也不例外,但他就算要死,也放不下《富春山居图》。于是,他作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要此画为他火殉。
吴洪裕奄奄一息的时刻到了,他授意侄儿取来《富春山居图》,火点起来了,画被投入火中,吴洪裕带着满足的笑容渐行渐远……说时迟那时快,他侄儿迅速从火中偷偷捞出此画,往火中投进另一幅画,偷梁换柱。
从此《富春山居图》起首一段就被烧去,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并断成一大一小两段,前段较小,后人称为“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后段画幅较长,后人称为“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国宝再也无法完全复原。
与《富春山居图》比,我国另一件著名国宝《平复帖》要幸运得多,说到《平复帖》,必然要说到张伯驹先生。《平复帖》传世一千七百年间,大多时期是在皇家,最惊险的时候是大收藏家张伯驹保管它的那段民国战乱期间。张伯驹为了保管它,经历被绑票、险些丧命、破家逃难种种艰辛,为之担当风险二十年,最后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历代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这个张伯驹,如白驹过隙,不留一痕。这在那些利字当头的俗人看来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一个《平复帖》,一个《富春山居图》,同样是国宝,命运却如此不同。《平复帖》何等幸运!在它有着最大风险的时候,遇到了张伯驹这样的收藏家,这不止是《平复帖》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而《富春山居图》却遇到了吴洪裕,留下的遗憾也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时局动荡,如果没有张伯驹,《平复帖》《游春图》等国宝很可能落入贪婪宵小之辈手中,甚至可能流落海外,成为中国文化的又一段伤痛。
当张伯驹将其收藏的《平复帖》《游春图》等重量级“国宝”义无反顾地捐献给国家后,他说起此事,话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这些东西不一定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重要的是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同样是收藏家,吴洪裕和张伯驹相比,其境界之高下简直如云泥之别。
说到收藏家,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认为收藏家是钟情于收藏情趣的人;也有人认为一个成功的收藏家要敢于掏钱,收藏家是掏钱掏出来的;还有行内专业人士给收藏家的定义是必须有N件公认的好藏品,其藏品的价值,应该在数N万元以上。
在笔者看来,一个人,无论是被称之为收藏家,还是收藏爱好者,其收藏的成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收藏。收藏者的动机决定了他们对待自己拥有藏品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有人是出于专业的特长发挥,也有人是为了得到社会的关注及尊重,还有更多的人将收藏当作资本投资或时髦的文化潮流。这些虽然都可以使收藏者获得一定的外在成就感,但每个收藏者因其境界不同,对其个人以及家庭的命运,甚至国家民族的利益产生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
有人说收藏其实是一种占有欲,甚至可说是一种恋物癖,此种说法虽显得刺耳,但某些收藏家的确表现出这样的心态,例如《富春山居图》的遭遇正反映了一个藏家至死不渝的强烈占有欲。其实,一个人恋物,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但若只知恋物却不知爱人,就成了恶癖,体现出来的自然是一种自私和狭隘的恶俗境界。
《荀子·修身》中云:“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即君子可以控制对物质的追求,小人只能被物质所左右;北宋诗人范仲淹也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思是君子的修养要能够抵御物质的诱惑和内心情绪的影响;《韩非子·喻老》中记载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春秋时宋国边远的地方,有人得了一块宝玉,将其献给宋国的执政大臣子罕,子罕坚辞不要,献宝人说:“这是一件宝物,应该佩戴在君子身上,我们百姓消受不起。”子罕回答:“你认为这玉是宝贵的,而我认为不接受你的玉才是宝贵的。”
可见,安之若素,顺其自然,以平常心面对得失,才是自古以来高洁之士所持有的人生态度。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收藏界的立场,也不代表收藏界的价值判断。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全文如下: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
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
不善在身,菑①然必以自恶也。
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虽欲无进,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谀者亲,谏诤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②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③成;厌④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远矣。

当今时代,科技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人可以“使”的“物”与日俱增,“使物”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为物使”的人却也日益增多。然而,“物”本来就是用来“使”的,人要主导、驾驭,而不是被“物”所“物”、所“累”、所“役”,如果相反,“物”便会成为负担、累赘,心为物役,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
今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也应成为我们处理人与物关系的一剂“良药”。人人都有喜好,但要正确对待五色、五音、五味等等,做到有尺有度,不被物所使。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越是物质丰盈、越是诱惑增多,越要学会正确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学会游于物外,如此才不会被物所累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