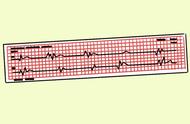作者:孙文辉
幼时无书可读,便常常对着墙上的日历簿出神。大人们看日历,主要看“宜”和“忌”,我则喜欢读每一页日历边沿的句子。早期的日历收录的多是农谚,诸如“夜来三潮雨,暗天十八日”“头伏萝卜二伏菜”之类。这些句子上通天时,下谙农事,每一个生长于大地上的人都有亲切的体会。
有段日子电视上播《联林珍奇》,主人公叫凌大岫,他自小擅长对对子,在或令人捧腹或催人泪下的故事中,我记录了不少奇对异联。譬如,同音对“鸡饥盗稻童筒打,鼠暑凉梁客咳惊”,变音对“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拆合字对“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生烟夕夕多”等。面对着这些成双成对的句子,谁会不震撼于汉语的神奇呢?我开始明白,每个句子的对面都有它的影子,这相当程度上定义了我日后的用语思维,甚至也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说来也有意思,我用掘黄花地丁赚的钱买的生平第一本书,也是关于句子的,书为《古今中外格言大观》,里面洋洋洒洒上万个句子,就像一座座句子累积起来的泰山,果真是“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这本书一度成为我的随身卷子,学堂里自不必说,回到家在灶根间烧火的间隙,也会映着火光念上几句,心里随之亮堂起来。周日去地头帮大人干农活,实在乏味得慌,就去茅草舍里喝口水,读几段句子,心情也会舒畅不少。那些年,我就是用这些长针似的句子,一点一点刺破贫瘠生活的巨幕,接收到些许精神的阳光。
看的句子多了,自然养成了一种鉴别力。《格言大观》上记有“满招损,谦受益”的句子,似太平正了,力道不足。我在别处读到“天欲使其亡,必先令其狂”,不觉一震,原来变换句式可让句子的潜力迸发出来。后来接触了巴尔扎克的“傲慢是一种得不到支持的尊严”,还有斯宾诺莎的“骄傲看似与自卑相反,实际上却与自卑最为接近”,发现一个概念放在相近或相反的概念里会获得更好的定义,产生某种复调的效果。一个句子就像一个魔方,有时稍稍旋转一下,就会组合出惊人的表达形式来。王维有诗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每次念来,都感觉眼前一片明艳,无限美好。后来我看到顾城把“红豆生南国”拆解成“红豆生出了南国”,不禁跳了起来:这是何等壮观的春啊!
高尔基说:“开头第一句是最难写的,好像音乐里的定调一样,往往要费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它。”既然如此,优秀篇章的第一个句子就很值得关注。顺着这个思路,我果然发现了不少经典的句子。如鲁迅《秋夜》首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以一种吊诡的语调敞开了一个不确定的文本世界,令人满怀期待;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首句“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还无法忘怀,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将未来、现在与过去神奇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时光弯曲、重叠的迷幻气氛……我贪婪地收集着这样的句子,一面暗喜,一面惊叹:这哪里是句子,分明是一颗颗奇异的灵魂,它们操着各自独一无二的语言,言说着自己所见到的特异世界。
读周作人作品的时候,我邂逅了日本的俳句,一下子被其吸引了。小林一茶有句云:“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这样的心境何其细柔,何其素朴,五六岁时在盒子里小心翼翼地养苍蝇的感觉,在我体内复活了。由小林一茶很自然地见到了松尾芭蕉,以及他那无与伦比的《古池》:“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这是一种因“无相”而有“无数相”的句子,可以直抵人幽深的心性。莎士比亚说人生“充满着喧哗与*动”,而在松尾芭蕉看来,人生是古池塘中发出的“扑通一声响”,极其短暂,但又永久地回荡在永恒的静寂之中。
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地收集着各式各样好玩的句子,欲罢而不能,原本枯燥落寞的日子因此充满了内在的光芒。等大学毕业千回百转与语文结缘后,我才对着大大小小的摘抄本,恍然大悟:原来这成堆的句子已为我完成了一场盛大的语文启蒙。此后凡有人问我该如何学语文,我总会颇有心得地回复:收集别人的句子。人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便又问怎样才能写好作文。我借用海明威的话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人们依然以为我在敷衍,殊不知,我已说出语文学习的全部秘密。(孙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