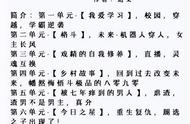如果一切都是命里注定好的结局,那么,这个盛夏的天空,那场匆忙绽放在向日葵田里的爱情,注定要在下一季的跃迁时凋亡。——楔子。

[一、夏子伊——我该如何许你一个灿烂的盛放。]
浅薄的天空下。草绿的山坡上。
抬头,便可以仰望到蓝的清澈的天空。
眺望,眼前是一片没有栅栏的向日葵田。
这是夏子伊的秘密基地。
他总是背着画架,带着几盒250ml的牛奶,来这片向日葵田写生。
盛夏的向日葵,开放的比任何一个季节的都要绚烂。
强烈的光线打在每一朵金灿灿的花盘上,在有风的空气中,浅浅的浮尘也缓缓的落在花盘的罅隙里。
眼前的盛夏,匆忙的绽放在这片天空下,颜色极其的强烈:蔚蓝、金黄、葱绿···复杂的交错着。
这和夏子伊的画,形成了这个夏天最刺眼的反差。
无论眼前的色彩多么丰富,多么有诱惑力,夏子伊的画永远都只是灰白色。
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个素描爱好者。
只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是灰白色的。
天空灰白色的,风灰白色的。
只是因为,他是个孤独的孩子。孤独到作画便是他生命的全部。
他在心里为自己筑起了一座透明的琉璃城堡,里面住不得王子和公主。
每次他总是在这个秘密基地可以呆上一下午。悠闲的作画,累了就躺下来发呆,阳光也总是很慷慨的铺满全身。他有恋空情结,常常喝着牛奶看着天空发呆,然后不知不觉把吸管咬到变形。
然后在夕阳把影子拉的很长很长的时候,才会收拾好画架,踏着那些嵌在花田里,被数十年风化而变得光滑的石板路回去。

[二、陌半夏——我该如何予你一段完美的忧伤。]
在回去的路上,经过了一条又一条繁华喧闹的大街。在这种繁华落尽的城市里,他总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他突然停下来了。有一种声音,一种在这吵杂的车水马龙中隐隐覆盖的另一种喧闹。或者说,是一种积蓄了灵魂所有力量吟唱出来的声音。顺着声源,渐渐的靠过去,后知后觉。
广场上,有一个穿着白色衬衫,打着黑色领带的男生,挎着一把黑色的吉他,在演奏着Guns Roses的《Dont cry》。
栗色的的头发,在风中被捋的很顺,微微倾斜的刘海稍稍挡住了些眼睛。子伊试图读懂那双眼睛。
那眼神有点空洞,像是被某种巨大的东西,吸走了所有的光芒,瞳孔的每一個密集的点都藏着淡淡的忧郁。眉宇间凝着一丝冷峻。那是双深邃,又令人心疼的眼睛。
子伊忘記了时间。呆呆的坐在那里,喝着牛奶,听他弹唱着。偶尔男生的目光会和子伊碰撞在一起,然后笑了,那笑,又漂亮又落拓。
夏子伊的心里,像飞进了一只萤火,突然有了亮光。
天越来越黑了,那个男生喝着可乐,朝夏子伊走了过来。
“谢谢你,能听我唱這麽久。”
“只是觉得,你唱的很不错。”
半夏没有回复这突如其来的赞美,而是看着眼前这个咬着牛奶吸管的夏子伊发呆。
“···额,怎么了?”
“···哦,呵,没,只是···在想,可乐和牛奶参杂在一起会是怎样的味道?”陌半夏有点不知所云的回答。
子伊有些吃惊的表情更让半夏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有多怪异,多尴尬。
“啊···这样阿,哈哈”子伊拿过半夏手中的可乐,将自己的牛奶小心翼翼的倒入可乐瓶中,然后振荡着,认真的看着白色的和黑色的液体融在一起,像个孩子般的期待着瓶子里能有什么特殊的化学反应。
最后,两个人一起挤着眉毛,喝下那颜色和味道都极其怪异的混合物。
事实证明,黑与白的混合曲风,无论在音乐上还是美术学上,都是不错的混搭,美轮美奂。
“我喜欢音乐”陌半夏低着头,垂下微斜的刘海说着“当大片大片的繁华在我面前一点一点的沦陷时,音乐,成为我最后的坚守。”
而后,在一起翻围墙回学校时才知道,原来是同一所大学,只是半夏是声乐系的,而子伊是美术系的。
大学的时光很悠闲,悠闲到你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而把所有借口都归咎于“人不轻狂枉少年”。而此后,他们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都形影不离。子伊经常带半夏去向日葵田晒太阳。子伊写生,半夏练吉他。只是从此,子伊的画,不再是只有灰白色了,他开始专心的为画上各种明媚的颜色了。而半夏也常常带子伊去看自己的表演,甚至还为他写歌。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感情正在某种介质的空气中发酵,慢慢有了微妙的变化。

[三、这一段——我该如何还它一场快乐的哀伤。]
那天,子伊下完课后去半夏的教室找他。在楼梯的拐角处,听见了2个女生的八卦谈话。
“呐,听说了吧,校花然小要在倒追陌半夏呢!”
“恩恩,哈哈,是听说了呢,而且呀,那然小要的爸爸还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呢。”
“哇,真的吗?那他们还真是公主配王子,真搭调呢。”
“恩恩,是呢,那陌半夏真的很帅呢,哎,王子的结局都会是公主呢,看来我是没戏咯”
“你丫你,还花痴呢···哈哈”
子伊的心里,突然有种怪怪的感觉,像是萤火飞出了黑暗,光亮消失了。
到了教室,看见半夏在弹吉他,旁边站着一个女生。
“嗨,子伊,快进来啊!”半夏朝子伊这边喊着,那个女生也转过了身。
“喂,半夏,这就是你常说的子伊吗?呵呵,有个这么帅的朋友,也不给我介绍丫?”
她就是然小要。
这个外表漂亮,内心却刁蛮的不可救药的公主。是个不折不扣的温室花朵。
然小要朝子伊端详了下:眉毛微微的上翘一定的弧度,柔和的双眼皮线条看起来有点性感,鼻梁尖挺,明眸皓齿,还真有点贾宝玉的神态。这张干净的脸,在这个纷乱的城市并不多见。
“子伊,这是然小要,我们系钢琴班的。”半夏介绍着。
“嗯,你好。”
“半夏经常提起你呢,呵呵,你们是很要好的哥们吧。”然小要笑着说,像是故意套近乎。
“嗯···”
“半夏,我有2张音乐会的门票,周末我们一起去看吧!”然小要转过脸去对半夏说。
“额,我答应子伊一起去写生的。”
“子伊,这个周末能不能把半夏让给我呀?”她又转过脸笑笑的看着子伊。
“恩···”看来然小要是真的很喜欢半夏阿,子伊心里想着。
然后三个人一起吃了晚饭,饭桌上,然小要对半夏的眼神和举止都证实了夏子伊的这个猜测。
直到有天下午,他们依旧挨着躺在山坡上,感受这夏日的温暖。
“半夏,你相信有‘下辈子’这种事麽?”
“···嗯 ,是相信的吧。”
然后是静谧的沉默,微微睁着眼看着空气中混合的呼吸声和风的声音,盘旋在葵花的香气中,慢慢坠落。
“半夏,下辈子,我想当一只飞鸟,你愿意陪我麽?”
“···这样阿,那我当一个稻草人好了,你累了就可以落在我的肩膀上休息了。”
“唔···”显然,被拉长的而又慵懒的语气好像表示对这个答案不是很满意。
又是一段沉默。
真正默契的人,即使没有任何语言,也依然能够读懂彼此纠结的内心。
他们就是这样,所以,在他们一起的时光里,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沉默,然后看着彼此沉默的脸,会突然像天真的孩子般,大笑起来。
子伊还是像往常那样,在沉默过后,瞥过脸来,看着半夏那张忧郁而又清澈的脸。
半夏眼角的余光也发觉了子伊在看自己,于是明媚的笑了下,转过头来看他。
尖挺的鼻梁轻轻的触碰在一起了。
好像,第一次,第一次这么近呢···
突然的不安起来,心也被彼此纤长的睫毛牵引着,频率加快的跳动起来。
在骨骼和肌肉组织紧紧包裹下的那颗心脏,似乎正裸露在空气中,心跳的声音也似乎被过往的风有意无意的放大起来···
在这所有躁动的气氛的渲染下,那么,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双唇轻轻的触碰在一起了···
那个午后,他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能这样?为什么我会这样?难道,我···”
这种无可厚非的事实,的确难以接受。
子伊在逃,半夏也在逃。
他们像两个孱弱的孩子,在逃离一场瘟疫。
一个星期的沉默。
可当彼此之间的眼神偶尔在过道里,或者走廊上触碰到得那瞬间,却又能读懂内心所有的独白,只是这种独白都不会说出来,变成对白。
夜幕降临时,将全世界都吞噬了,闭上眼睛,任凭自己被时间抛进黑暗里。
在黑暗里,传来一种不为人知的隐秘声。
“呐,是喜欢上了吧?”
“恩,看来,像是喜欢上了呢”
“呐,这是爱情吧”
·····
是自己的哪条神经在与这种隐秘声对话,始终不敢被证实触碰到的心情,还是在与这种隐秘声的对话中被赤裸裸的喊出来了。该怎么面对···
“呐,这没什么的。爱情,是可以逾越切世俗的枷锁。是最纯粹的自由。
在爱情里,可以不在乎年龄,不在乎高矮,不在乎金钱,甚至,或許,也是可以不在乎性别的“
在黑暗中挣扎,死亡,然后重生。如同一场盛大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没有光的大火,将黑暗的胆怯,燃成银白色的灰烬。
恩,决定爱了。
“恩,在一起吧。无论这份爱要的多么卑微,只要我们坚定就好。”
“恩,在一起吧。”这是同样挣扎,死亡,重生后的决定。笃定的信念。
此后,两人的命运便开始以一种氤氲的姿态,纠缠在一起了。他们更幸福了,仅仅一个微笑,都能让彼此感觉像是得到了全世界。

[四、然小要——我该如何怨你一份锥心的荒唐。]
“小要,我···爱上子伊了。对于你的感情,很抱歉。我不能接受。”
陌半夏在听完然小要练习了好久的表白后,拒绝了她的感情。
“呵,什麽?你说你···爱上了一个男生?呵,我没听错吧?”然小要感觉大脑要爆炸了,她开始无法左右自己的思想了,像是某条金属发条卡住了,整个机械停止运作。而慢慢的将这种难以置信的惊恐转化为愤怒和憎恨,发条崩断了,机械脱离操纵。
“恩,我爱他。“半夏更加坚定的说。
“哈哈···陌半夏,你给我听着,只要是我然小要得不到的东西,任何人都休想得到,听清楚了,是任何人!”一丝邪恶的黑暗的笑,掠过然小要白皙的脸,然后发狂似地跑开了。
“出事了,呐,你听说了吗,美术系的那个夏子伊被人打的半死不活的,现在在医院呢!”
当半夏在上楼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扔到吉他,立马赶到医院。
“他没有生命危险了,只是右手有多处粉碎性骨折,以后···恐怕不能活动了。根据伤势化验报告表示,那些施暴歹徒是有意针对他的右手。”医生有些遗憾的对半夏说。
半夏觉得神经一下子全部紊乱了,他没办法理清,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病床上的子伊以后不能再作画了的事实,他宁愿残了右手的人是自己,他宁愿···
突然,脑海里闪过然小要甩下的最后一句话。
“对,一定是她!”他发疯似地冲去找然小要。
“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派人做的?”他愤怒的摇着然小要瘦弱的肩膀吼着。
“呵呵,这是他应该有的惩罚,不是么?他不是很喜欢作画么?呵,那我就让他这辈子都再也握不起画笔了,哈哈···”
“然小要,你已经丧心病狂了!”半夏感觉自己像瘫痪般无力了。
“呵,是么?好戏还在后头呐”依然是那种笑,邪恶得一丝不苟。
“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收手?求你了,不要再伤害他了,不要···”他几近崩溃。
“呵,我得不到的,任何人都休想得到!要我收手?可以,很简单,我要你离开他。马上!”
“我答应你···只要你不再伤害他···”为了夏子伊,或許,这是爱他最好的方式。
他退学了。
还没来得及亲口和病床上的夏子伊告别,就要离开了。
还没来得及安慰再不能画画的子伊,就被迫的要离开了
甚至,还没来得及亲口对夏子伊说那句“我爱你”,就不得不离开了。
他只是留了张纸条:子伊,我想,我们不能在一起了,但是,那并不代表我不爱你。呵呵,子伊,我爱你。一直没有告诉你,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的爱。请记得我们下辈子的那个约定,再见。
他离开了,离开了这座有着一个名叫夏子伊的人的城市。火车缓缓的驶向未知的远方,铁轨与火车的碰撞声同汽笛声一起宣告着这场盛夏里匆忙绽放的爱情的凋亡。陌半夏慢慢的抬起了满是泪痕还未风*脸。火车正经过一片孤独的麦田,他看见,在一层一层的麦浪中,有个孤独的稻草人,肩上停着两只鸟儿,亲昵的在吴侬软语。
他埋下头,哭得竭斯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