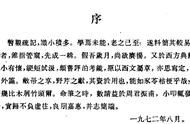中国诠释学研究40年
文 | 李清良、张洪志
提要
经过近40年的共同努力,我们对西方诠释学的引进和研究,已从最初以译介为主逐渐走向译介、研究和反思并重;对中国诠释传统的研究与清理,已从较宏观的整体研究逐渐走向以专题和个案为中心的更加深入和细致的考察;对现代中国诠释学的探索和建构,则从以海外学者为先锋逐渐转变为以我国大陆学者为主体。虽然仍有不少明显不足的方面有待克服,但通过持续努力,我们必将越来越全面而准确地了解中国、西方及其他文明的诠释传统,现代中国诠释学也必将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建立起来,并与其他文明的“诠释之道”共同为文明对话、世界和平、文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关键词
诠释学 中国诠释学 诠释之道


本文所谓“中国诠释学研究”,既包括海内外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也包括“在中国”的国外诠释学译介与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等著作的出版,诠释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并日益深入地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甚至影响到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我国虽然早在1963年第9期《哲学译丛》就刊载了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的论文《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但学者们真正注意到诠释学这门学问要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经过近40年的努力,中国诠释学研究不仅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而且成为了当代中国学术最具吸引力的研究领域之一。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专著和论文集近1000种,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逾10000篇。以下试从西方诠释学的译介研究与应用、中国诠释传统的研究与清理、现代中国诠释学的探索与建构等方面加以简要评述。
一、西方诠释学的译介、研究与应用
我国首次集中刊发西方诠释学译文始于1986年第3期《哲学译丛》,该期共翻译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尔的13篇诠释学文章。自此之后,西方诠释学成为了我国学者的重要译介对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积累,现在西方诠释学理论的主要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的重要研究著作大都有了中译本,其中尤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狄尔泰和利科尔的相关作品最为学界关注。
海德格尔是西方哲学诠释学的真正奠基者,其名著《存在与时间》标志着西方诠释学从方法论到存在论的转向,该书于1987年由陈嘉映、王庆节译成中文,由三联书店出版,汉语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18年,孙周兴、王庆节主编的煌煌巨编《海德格尔文集》30卷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集中体现了我国学者对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成果。主编者表示,这套文集还将扩展到40卷的规模。
哲学诠释学的创立者伽达默尔的著作现在也已译出十余种,如《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赞美理论》(夏镇平译)、《美的现实性》(张志扬等译)、《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张志伟译)、《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伽达默尔集》(严平编选,邓安庆等译)、《哲学生涯》(陈春文译)、《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孙善春编译)、《解释学·美学 实践哲学 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金惠敏译)、《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等。其中洪汉鼎翻译的《真理与方法》一版再版,对国内诠释学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还编译了《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主编了《解释学译丛》(商务印书馆于2009年起陆续出版)。从2017年开始,洪先生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伽达默尔著作集汉译与研究”,预计很快就会推出中文版的伽达默尔全集。
以交往理论闻名于世的哈贝马斯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到目前为止,其中文译著已达数十种,如曹卫东编译的多卷本《哈贝马斯文集》、郭官义和李黎翻译的《认识与兴趣》《理论与实践》《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尔以强调存在论诠释学和方法论诠释学相统一著称。他的著作也已译出了十余种,如《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论现象学流派》(张一兵、蒋海燕译)、《承认的过程》(汪堂家、李之喆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孔明安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恶的象征》(公车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论解释——评弗洛伊德》(汪堂家、李之喆、姚满林译)、《爱与公正》(韩梅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文融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等。
狄尔泰是首次将诠释学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家。他的著作到目前已译出了《精神科学引论》《历史中的意义》《体验与诗》《历史理性批判手稿》《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等5种,其中《精神科学引论》还有多个译本。遗憾的是,西方现代诠释学创始人施莱尔马赫的著作至今还只译出《论柏拉图对话》(黄瑞成译)、《论宗教》(邓安庆译)2种,另加国外学者的3种研究著作(国内学者的研究专著目前也有4种),他最重要的诠释学著作《诠释学与考订学》迄今为止反倒未被完全译出。
除此之外,西方宗教诠释学的不少著作,如特雷西(D.Tracy)的《诠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范浩沙(Kevin J.Vanhoozer)的《神学诠释学》(左心泰译),克莱恩等著《基督教释经学》(尹妙珍等译),戈登·菲等著《圣经导读:解经原则》(魏启源等译)等,已被陆续译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的《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自2000年开始策划以来已经出版了四百余种,其中“西方传统”系列翻译了200余种,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学者对于西方经典诠释传统的认识。
我国学者对于西方诠释学不仅有翻译,还有研究。张汝伦《当代西方释义学——意义的探究》(1986年)和殷鼎的《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1988年)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诠释学的著作。最近30年来,我国还涌现了一批长期致力于西方诠释学研究的专家,如洪汉鼎、潘德荣、何卫平、傅永军、张能为、彭启福等学者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洪汉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致力于西方诠释学的翻译和研究,著有《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真理与方法〉解读》《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实践哲学 修辞学 想象力——当代哲学诠释学研究》《诠释学与中国经典注释》等多部专著,并主编了《中国诠释学》辑刊。潘德荣翻译了帕尔默的《诠释学》,著有《诠释学导论》《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西方诠释学史》等专著,并主编《本体论诠释学》数辑,及《对话与和谐——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研究》《中西学术视野下的诠释学——纪念伽达默尔逝世十周年论文集》等论文集。何卫平译有《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导论》《伽达默尔》等著作,并有《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理解之理解的向度——哲学解释学研究》等专著。傅永军主要关注哈贝马斯的批判诠释学,著有《控制与反抗: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启蒙、批判诠释与宗教伦理》《绝对视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学:从伦理神学到道德宗教》等专著,并与洪汉鼎共同主编《中国诠释学》辑刊,还从2002年起长期组织举办中国诠释学年会,至今已召开16届。张能为著有《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等专著,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彭启福著有《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理解、解释与文化——诠释学方法论及其应用研究》,编有《理解之路——诠释学论文选粹》等。
港台学界也很早就开始了西方诠释学研究。如张旺山著有《狄尔泰》,周华山著有《“意义”——诠释学的启迪》,陈荣华著有《葛达玛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的诠释》,黄瑞祺著有《曼海姆——从意识形态论到知识社会学诠释学》,陈俊辉著有《祁克果存在诠释学》,赖贤宗著有《意境美学与诠释学》,陆敬忠著有《哲学诠释学》,柯志明著有《恶的诠释学——吕格尔论恶与人的存有》,张汉良著有《符号学与诠释学》,张鼎国著有《诠释与实践》等。
我国学者的西方诠释学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就范围而言,既有通史研究,也有个案和专题研究。如张汝伦的《当代西方释义学——意义的探究》、洪汉鼎的《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潘德荣的《西方诠释学史》就是通史研究的突出代表。就人物和流派而言,基本上涵盖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利科、赫施、哈贝马斯、阿佩尔、罗蒂、艾柯、德里达、瓦蒂莫等现代西方诠释学史上的大部分重要人物,涉及方法论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实践诠释学、批判诠释学、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乃至激进诠释学等各种理论形态。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研究,仅专著就有十余种;其次是对哈贝马斯、利科、狄尔泰、施莱尔马赫等人的研究。就问题而言,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诠释学的内部问题,涉及西方诠释学的历史流变、各个流派的整体把握、诠释学核心概念的辨析、各流派及思想家之间的分歧与相互影响等;二是诠释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与渗透,涉及文学、美学、科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律、教育、翻译等诸多领域;三是诠释学与其他思想潮流的关系,如与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相互影响,与辩证法、修辞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与自由、民主、创造等观念之间的关系,与方法论、认识论之间的关系等。
西方诠释学对当代西方各个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同样如此。目前,从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历史、法律、艺术(如音乐、美术)、教育、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建筑学、设计学、广告学、新闻传播学等理工科与应用性专业,甚至传统武术、体育等领域都有诠释学的身影,其中尤以文学、法律、教育、翻译等领域最为突出。
西方诠释学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运用西方诠释学理论分析与解释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如李建盛、刘月新等);二是运用西方诠释学理论整理中国文学诠释传统(如邓新华)和文学作品诠释史(这方面的著作不胜枚举);三是借鉴西方诠释学建构中国的文学诠释学理论(如金元浦、李咏吟、台湾周庆华等)。法律诠释学是西方诠释学的重要分支,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诠释学的探索和构建用力颇深,或从宏观层面对法律诠释学进行整体把握(如谢晖、陈金钊、疏义红、姜福东、王利明、张真理、张志铭、范进学等),或从事宪法(如徐振东、张翔等)、民法(如梁慧星、段匡、张利春等)、刑法(如徐岱、万毅等)、行政法(如王旭,李洪雷、方颉琳等)等各个分支领域的诠释学研究。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西方诠释学理论对中国法律诠释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教育过程中的“教—学”关系本质上就是解释与理解的关系,因此利用诠释学原理来研究教育学也是自然之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相关研究著作10余种,特别是哲学诠释学对中国教育诠释学的探索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金生鈜的《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就是运用哲学诠释学对教育的意义生成、受教育者的精神建构、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学校教育的课程诸问题作出解释与阐明;邓友超的《教育解释学》更是明确主张以哲学诠释学和批判诠释学为理论基础,曹明海的《语文教学解释学》亦坦承主要是以哲学解释学理论为基点。“理解即翻译”,翻译学领域的诠释学研究也是热点,各类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多得难以统计,专著亦有数种(如蔡新乐、郁东占、李静滢、裘姬新、谢云才、胡庚申、王宏印等),它们利用西方诠释学理论,或研究具体的翻译问题,或清理中国传统的译论,或构建译学诠释学。
由上可见,西方诠释学传入我国之后,对各学科领域的渗透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以理解和说明本学科内部的基本问题;二是作为基本原理建立各部门诠释学。这就为当代中国学术开拓了很多新领域,并且深化了各学科的哲学思考。然而,完全用西方诠释学理论来解释与指导,有时难免削足适履,不易准确把握中国学术的历史传统和内在精神。这就使得清理与研究中国传统的诠释学资源、建构现代中国诠释学显得十分必要。
二、中国诠释传统的宏观研究
在西方诠释学的影响与激发下,学者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诠释传统加以清理与研究。进入本世纪以来,此项研究已成为一大学术热点,涌现出很多成果,其中既有宏观的整体研究,也有具体的个案和专题研究。
最早对中国古典诠释传统加以整体研究的是海外汉学家。美国汉学家韩德森(John B. Henderson)所著《典籍、正典与注疏:儒家与西方注疏传统之比较》(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 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指出,近代以前中、印、欧及近东的知识传统大都以经典注疏形态出现,尽管所信经典内容各不相同,但在注疏假设及注疏策略上却异曲同工。比较而言,中国儒家注疏传统的特色有三:一是在经典系统的整合方面最具规模;二是保持开放状态而不断容许新经典出现;三是在20世纪前后并未充分完成“传注世界观之消失与变形”的工作。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置于世界各大注疏传统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察。韩德森后来又有《正统与异端的建构:新儒家、伊斯兰教、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模式》(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NeoConfucian, Islamic, J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等论著,继续对不同经典诠释传统进行比较研究。
美国汉学家范佐仁(Steven Van Zoren)的《诗歌与人格:传统中国经解与诠释学》(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是在其198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著虽以《诗经》诠释传统为考察中心,但实际关注的却是整个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作者认为,与西方主流的诠释学传统颇不相同的“中国诠释学”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它经历了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先秦以迄唐代的正典化和神圣化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宋代开始建立起一种以“读书法”为中心的一般诠释学,尤以朱熹为集大成者;这两个阶段虽在诠释范式上颇有不同,但中心问题都不在于“如何了解文本”,而在于“如何受到文本感化”,即都是以人而非文字意义为重心。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论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译本为《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结合中国文论传统指出,中国古代自有其“诠释学”,但与西方诠释学传统在真理观与语言观上颇不相同,这就导致“最基本的关注和公认的假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整套问题也不相同,从而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中国诠释学传统。宇文所安的这种进路,显然是在一种多元主义文化态度下,注重突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较于西方诠释学传统的独特性。
自此之后,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诠释传统的研究著作日益增多。其中如周启荣、伍安祖和韩德森合编的《想象的界限:变革中的儒家学说、文本和诠释学》(Imagining Boundaries: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 Texts and Hermeneu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及涂经诒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中国文化中的诠释学传统》(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ress, 2000)和《解释与思想变化:历史视角下的中国诠释学》(Interpre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Chinese Hermeneu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等通论性著作特别值得注意。
张隆溪的英文专著《道与逻各斯》(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于1992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冯川译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这是华人学者对中国诠释传统基本观念与精神进行总体研究的首部专著。作者认为“我们确乎可以把中国文化传统说成是一种阐释学传统”,故此书虽然“关注焦点是一种特殊的文学阐释学”,但目的是为了映衬出整个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基本特点与精神。该著反对中西文化不相兼容的偏见,试图“超越东、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差异”,围绕有关语言与解释等“共通、共有和共同”的主题,进行批判性对话与东西会通,故其“结束语”特别指出,承认并欣赏诠释的多元化正是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基本特点。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中西之间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的“道”与西方的Logos这两个根源性概念的差异着力加以辨析。
台湾大学黄俊杰的《孟学思想史论·卷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是自觉研究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首部汉语专著。该书认为,中国古代虽无西方现代意义的诠释学,但有一种古典意义的“中国诠释学”,即“中国学术史及思想史上以经典注疏为中心所形成的诠释学传统,这个传统在儒家一系表现得最为深切著明”,该书的目的即“在于分析中国学术思想史所见的孟子学解释史,并建构中国诠释学的类型学”。故此书第二章专门探讨了“中国诠释学”的三个基本方法论问题,即诠释者的历史性、问题意识的自主性、诠释的循环性等问题,最后一章又集中分析了“中国诠释学”的三种类型:一是“作为解经者心路历程的诠释学”;二是“作为政治学的诠释学”;三是“作为护教学的诠释学”,并认为“中国诠释学”的基本性质是一种“实践活动”,“实是以‘经世’为本”,因而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在此基础上,黄俊杰又于2000年开始,建议从比较思想史的立场,研究整个东亚近世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发展及其特质,以迈向儒家经典诠释学的建构,从而为“东亚诠释学”的建立奠定实证研究的基础。为此,他联合李明辉、杨儒宾、陈昭瑛、郑吉雄、蔡振丰等台湾学者,共同研究“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等课题,并通过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等平台,与国内外同仁进行广泛交流,同时将相关研究成果纳入《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约200种),其中《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通论篇》(黄俊杰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儒学篇》(李明辉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三):文学与道家经典篇》(杨儒宾编)等书,虽然只是论文集,但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国古代诠释传统的研究。黄俊杰本人也相继推出《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等中英文专著多部。通过这些努力和成绩,黄俊杰成为中国诠释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所在的台湾大学也成为该领域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北京大学汤一介从1998年起连续发表《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5篇倡导性文章,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从此以后,我国大陆学者也纷纷加入中国古典诠释传统研究的行列,并且日益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
李清良的《中国阐释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是大陆学者最早通论中国古典诠释传统的专著。该书除导论外,共分“语境论”“时论”“理解根据论”“理解过程论”“阐释论”等5篇凡15章,着重清理中国古代诠释传统中最基本的观念与思想,并试图初步勾勒出中国古典诠释学理论的基本轮廓。该书《导言》明确认为,“任何独立自足的文化系统都必须面对理解与阐释的问题,都必须思考何以能够理解以及如何去理解与阐释的问题,因而都有其阐释学理论”,因此“并不是只有西方文化中才有阐释学理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同样各有其独特的理解观念与阐释方式,各有其独立自足的阐释学理论”。作者从经史子集发掘出许多材料,颇能表明中国古代确有其独立自足且不同于西方的诠释理论与传统。此后,李清良又出版专著《熊十力陈寅恪钱钟书阐释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提出研究中国诠释传统固然包括多个层面,但主要应当落在诠释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诠释思想上,并且应当把研究视野由古代扩展到近现代。故此书虽是对于三位现代学者的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但其旨趣则是试图考察中国诠释传统在现代文史哲三大学科领域的延续与变化,试图由此表明,我国现代学者已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有过不同程度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取得了不少卓越成就。
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的发生与发展历程、典范体式、解释方法、基本特点等方面作了系统考察。周光庆认为“中国古典解释学”以中华文化经典为基本解释对象,以认识圣人之道为基本解释目的,以修己治人为实际解释归宿,以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为主要解释方法,其缺点在于没有明显的独立学科形态,注重解释方法的革新创造,却缺少本体论的理论基础,也很少论及解释者与文本的互动和对话。基于这样的观察,他将其称为“古典解释学”,以与“哲学解释学”或现代解释学相区分。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对中国古代诠释方法有较系统和细致的分析,并对中国诠释传统的发生发展历程和基本的诠释体例作了初步考察。
周裕锴的《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认为,中国古代自有一套阐释学思路和理论,并且“由于中国和西方的阐释学是在不同的存在方式的基础上对不同的言说文本的理解,因此在同一普遍的理论原则之后,存在着一种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的深刻差异”。该书除“前言”外共分7章,通过收集分析散见于各种典籍中有关理解与解释的论述,演绎出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学派诸如经学、玄学、佛学、禅学、理学、诗学中所蕴藏着的丰富的诠释学理论内涵,试图“由此揭示出中国古代阐释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异于西方阐释学的独特价值”。作者认为,就整体特色而言,中国古代阐释学可以称为“互文性阐释学”;根据阐释对象的不同又可细分为“诗歌阐释学”“经学阐释学”“佛教阐释学”等;根据阐释观念的不同则可细分为“意图论阐释学”与“多元论阐释学”、“尚意阐释学”与“尚味阐释学”、“清代阐释学”与“宋学阐释学”等类型。此书尽量从经、史、子、集各种典籍中搜罗片玉遗珠,尤其对有关文学诠释传统的各种资料的搜集贡献颇多,因此对一些重要概念与问题的辨析往往能见人之所未见;此外,此书对于中国佛教诠释传统也予以较多关注与梳理,同时又注重将抽象的诠释观念与具体的注释形式和编纂方式加以综合考察。
景海峰的专著《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也以不少篇幅论及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其中除介绍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汤一介四位学者建构中国诠释学的不同探索之外,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主张:一是通过考释“诠释”“解释”“阐释”等词的源流,主张将hermeneutics译为“诠释学”;二是认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多半只能划归到‘前诠释学’的形态当中”,因此对于西方“当代诠释学”主要是借鉴和吸收的问题,并且应当从方法论与本体论两个方面努力;三是认为我国儒学史作为一部经典诠释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先秦到六朝是“以经为本”的时代,从中唐到两宋是“以传记为中心”的时代,元明清则是“经典系统被彻底地经院化和严重格式化”而后逐渐“走向多元”并终于“全面崩溃”的时代;四是认为建构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并不是也不能“重回训诂学的怀抱”。该书出版之后,景海峰教授又陆续推出了一些相关论文和著作,继续借鉴西方诠释学相关理论研究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观念,同时又对这一传统的现代流变及其研究现状予以考察。总的来说,景海峰主要是从中国哲学发展角度关注并参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研究。
刘笑敢的《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也是颇富创见的专著。该著最主要的观点有四:(1)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传统有密切关系,自魏晋以来大多数重要的哲学家都是以完整的经典注释或诠释方式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2)以经典注释和诠释方式建构哲学体系,必然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定向,一是历史的、文本的定向,一是现实的、自我表达的定向,由前一种定向将走向思想体系的“拟构”,由后一种定向则将走向思想体系的“创构”;(3)古人对于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未必自觉,但在今天则应该有方法论和学术目标的自觉意识,从而应对不同的定向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4)西方诠释学理论尤其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中国哲学诠释传统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推动力,但也应该看到其局限,当根据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的突破。
张茂泽主编的《中国诠释思想史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是近年涌现的又一重要成果。该著虽然只是“个案或片段地讨论中国古代诠释思想史”,但有三个突出特色:一是将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诠释、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法律诠释纳入了中国诠释思想史的考察范围;二是认为中国现代学人如冯友兰、金岳霖等人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古代诠释方法在近代学习西学后得以丰富和发展的集中表现和主要标志”;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将诠释思想与诠释活动、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考察。
三、中国诠释传统的专题与个案研究
随着上述通论性著作的问世,这个新的论域迅速成为汉语学界的关注焦点,有关中国诠释传统的各种专题和个案研究成果不断推出。总体而言,从对象来看,对中国经学儒学的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最多;从时段来看,对先秦两汉和两宋明清的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最多。
相较中国文化的其他思想流派,学者们对中国经学和儒家的经典诠释传统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如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4卷6大册(前两卷出版于2003年,2010年出齐全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是这个方面较早推出的重要成果。该书“绪论二”指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是以不断地对原典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开展的。儒学经典与诠释的关系,反映为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对儒学经典的诠释,亦即是对中国历史传统的诠释”;二是中国经学在“各时代的经典诠释与其时代思潮感应互动而呈现出神学化、玄学化、理学化、朴学化、西学化的时代特征”;三是先后呈现出一些基本的“诠释学导向”,如“知人论世,以意以志”“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实事求是,六经皆史”“返本开新,托古改制”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该书对中国经学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经典诠释进行了讨论。又如蔡方鹿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除从整体上梳理中国经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外,还特别对宋明理学家的经典诠释思想、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异同,尤其是朱熹的经典诠释思想加以深入清理与阐发。再如台湾学者赖贤宗的《儒家诠释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和大陆青年学者康宇的《儒家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与《儒家诠释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著作,分别梳理了儒家诠释传统的发展历史、基本思想以及基本方法等内容。
从断代角度加以研究的,则有刘耘华的《诠释学与先秦儒家意义之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以“诠释立场”“意义”“意义生成方式”等概念为纲,系统梳理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诠释思想。陈昭瑛的《儒家美学与经典诠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对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郭店楚简》及朱熹、徐复观的经典诠释思想作了深入探讨。臧要科的《三玄与诠释——诠释学视域下的魏晋玄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对魏晋玄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认为从何晏王弼与阮籍嵇康到裴頠郭象,经典诠释思想在方法和内容上呈现为一个清晰的逻辑演进过程。姜海军的《宋代经学诠释与思想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则专门研究了宋代经学诠释范式的基本特征、丰富内涵、传承演进、典型个案、广泛影响等。崔发展的《乾嘉汉学的解释学模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对乾嘉汉学的核心观念“实事求是”作为考证的方法论、认识“实事”与“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何以可能”的存在论等作了系统阐发。
更多的研究是以个别经典的诠释史为中心展开。比如《易》学方面:郑吉雄的《易图象与易诠释学》、林义正的《〈周易〉〈春秋〉的诠释原理与应用》、林忠军的《易学源流与现代阐释》、杨效雷的《中国古代〈周易〉诠释史纲要》与《诠释学视野下的易学》等。《尚书》学方面:张兵的《〈洪范〉诠释研究》、史应勇的《〈尚书〉郑王比义发微》、钱宗武的《〈尚书〉诠释研究》等。《诗经》学方面:尤家仲的《〈诗经〉的解释学研究》、史应勇的《〈毛诗〉郑王比义发微》、郭持华的《经典与阐释——从“诗”到“诗经”的解释学考察》、邹其昌的《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郝永的《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等。《礼》学方面:薛永武的《中国文论经典流变:〈礼记·乐记〉接受史研究》、吕友仁的《〈礼记〉研究四题》、乔秀岩的《义疏学衰亡史论》、华喆的《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等。《春秋》学方面:刘国民的《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陈明恩的《诠释与建构——董仲舒春秋学的形成与开展》、平飞的《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等。
《四书》学诠释传统研究是另一个学术热点。除前述黄俊杰的《孟学思想史论》《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及所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等著作之外,还有朱汉民、肖永明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唐明贵的《论语学史》和《宋代〈论语〉诠释研究》、杜敏的《赵岐、朱熹〈孟子〉注释的传意研究》、周元侠的《朱熹的〈论语集注〉研究——兼论〈论语集注〉的解释学意义》、柳宏的《清代〈论语〉诠释史论》、高青莲的《解释的转向与儒学重建——颜李学派对四书的解读》等专著。
有关的个案研究专著就更多。如李凯的《孟子诠释思想研究》、刘国民的《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陈明恩的《诠释与建构——董仲舒春秋学的形成与开展》等。在这方面,海外汉学家贡献了不少著作,如美国汉学家桂思卓(Sarah A.Queen)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朱腾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G. Wagner)的《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他们的研究思路较为开阔,颇能给我们以启发。如桂思卓指出,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不仅在汉代政治法律的实践中产生了实际影响,并为儒家士大夫对现实政治展开褒贬提供了经典依据,还使得儒家经典上升为像西方宗教典籍那样具有宗教性的“圣典”(Canon),成为了君主与臣民共同信奉的精神源泉。又如瓦格纳的上述著作,不仅简要梳理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还特别注重揭示诠释策略、隐含读者、对立文本、链体风格、注释技艺及其与语言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内在联系。艾尔曼的上述著作则通过考察今、古文二派的争论,探讨经典诠释为正统政治观点提供根据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个案方面,尤以研究朱熹诠释思想的专著最多。如林维杰的《朱熹与经典诠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分别从意义论、方法论与工夫论等角度深入解析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曹海东的《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及《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论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运用范畴分析方法,从经典文本论、经典解释目标论、经典解释方法论、经典解释效果论、经典解释弊病论等方面的范畴体系重构了朱熹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尉利工的《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兴起背景、根据、路径、原则和方法等进行了研究。邹其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对朱熹《诗经》学的诠释原则、创作旨趣、品赏方式、审美品格做了系统分析。郝永的《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认为朱熹的“诗经学”是关于《诗》三百篇的解释学,是扬弃旧学而回归《诗》三百的诗歌本体后的理学解释学。周元侠的《朱熹的〈论语集注〉研究——兼论〈论语集注〉的解释学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认为《论语集注》是朱熹吸取传统注经模式、广泛采纳传统注硫以及宋代义理解说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佛、道经典诠释传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佛学方面的专著如林镇国的《空性与现代性:从京都学派、新儒家到多音的佛教诠释学》、赖贤宗的《佛教诠释学》、杨维中的《经典诠释与中国佛学》、陈坚的《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高新民与沈学君的《理解与解脱——智者的佛教解释学与人生解脱论》、程恭让的《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等。道家方面除杨儒宾主编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三)文学与道家经典篇》论文集外,还有赖贤宗的《道家诠释学》及前文已提到的臧要科的《三玄与诠释:诠释学视域下的魏晋玄学研究》、夏可君的《庖丁解牛——庄子的无用解释学》等。
对中国文学诠释传统的研究成果不少,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有所涉及。其中有不少是着重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之特点的。如李有光的博士论文《论“诗无达诂”》(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及多篇论文认为,与中国经学解释学“祈向元意”相反,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取向是多元论,而代表这种取向之原则、主线、标志和纲领的话语就是“诗无达诂”。冯淑静的《〈文选〉诠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从《文选》诠释体系、诠释体式、文献诠释、文学诠释等方面对历代《文选》诠释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刘洪波的《阐释学视野下的〈楚辞补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对洪兴祖《楚辞补注》的诠释动因、诠释体式、思想视域进行了研究。何明星的《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展现了钱钟书的名著《管锥编》的独特诠释方法、价值及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继承、发展和贡献。张晚林的《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以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心性论”为主线,以徐复观的艺术诠释观念及实践为研究对象,力图构建“徐复观的艺术诠释体系”,并解析其精蕴与价值。何明星、张晚林的上述著作和李清良的《熊十力陈寅恪钱钟书阐释思想研究》、刘毅青的《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也是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现代诠释思想的专著。
除专著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各类期刊与学位论文。举凡历史上较重要的经典诠释著作和作者大多已成为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逐渐全面和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中西诠释传统在基本观念、具体方法、诠释体例等方面的差异。这就为探索现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四、现代“中国诠释学”的探索与建构
中国学者清理与研究中国诠释传统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借鉴和吸收西方诠释学,对中国诠释传统加以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以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国诠释学。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叶维廉、成中英就已分别提出“创造的诠释学”“中国传释学”“本体诠释学”等构想。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旨在吸纳西方诠释学的精华,建立中国本位的诠释学方法论原则。他认为,以儒道佛三家为主的中国哲学思想史乃是一部“创造的诠释学”史,今天应站在“中西互为体用”的立场,将文本意义的诠释分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等五个层次。叶维廉认为,应该借鉴西方“诠释学”建立“传释学”,因为所谓“诠释”往往只从读者角度出发了解一篇作品,而“传释学”所要探讨的是作者传意与读者释意之间互为表里又互为歧异、既分且合的整体活动。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则试图贯通中西两大哲学传统,主张诠释与本、体三位一体,“本”指根源性的动态力量,“体”指由此种根源生发出来以后形成的整体存在,对本体的把握和理解即是“诠释”,自本体而来的理解首先形成本体论,对这种本体论的反思与理解又导致更好的理解,而更好的理解又促成新的本体论,如此自本体的理解与对本体的理解相互贯通。三位学者的上述构想,都基于他们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相关理解和研究,初步体现了建构“中国诠释学”的意图,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影响。
大陆学者金克木也早在1983年介绍西方诠释学时认为应该有“中国诠释学”研究。他说,既然我国有丰富的经典注疏传统,“为什么不可以有中国的、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符号学和诠释学研究呢?我看我们不是不具备突破西方人出不来的循环圈子的可能”。不过他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所以其建议也没有什么影响。对国内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是上文提到的汤一介自1998年以来连续发表的数篇提倡“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论文。他认为,创建“中国解释学”,应当建立在对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与西方解释学都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只有“对中国的经典历史作一系统的梳理,写出若干部有学术价值的《中国经典解释史》,来揭示不同时期对经典注释的发展历史,总结出若干中国经典解释的理论与方法”,“然后才有可能创建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现代中国解释学’”。为此,他梳理出中国经典注释中三种最为典型的解释模式,即以《左传》为代表的“历史事件的解释”,以《系辞》为代表的“整体性的哲学解释”,以韩非《喻老》《解老》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后来又指出,《墨经》的《经》与《经说》并列的模式对于后世有关字义或辞义的的解释也有很大影响。汤一介的这些论文,不仅为开展中国诠释传统的研究提供了范例,也为大陆学者创建现代中国诠释学的探索拉开了序幕并奠定了基调。
有些学者反对建构“中国诠释学”,或是认为诠释学不存在中西之分,或是认为现代诠释学本来只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产物,中国学者没有必要邯郸学步。但大多数学者并不如此认为。本世纪以来,对于如何建构现代中国诠释学,学者们不断提出各种不同的构想。比如张立文主张建构“和合诠释学”,林安梧试图构建“中国人文诠释学”,杨乃乔则主张在中西比较基础上建构“经学诠释学”。洪汉鼎、景海峰、陈少明等学者则对如何建立中国“经典诠释学”提出了建议。此外,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主张。比如俞吾金提出了“实践诠释学”的主张,认为实践活动是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历史性是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本特征,意识形态批判是正确地进人诠释学循环的道路,试图由此解构语言独立王国并引入新的诠释方法(还原法与考古法)。张一兵也提出“思想构境论”,认为读者不可能复原原初文本的语境,离开原作者所呈现的当下文本语境,恰恰是文本研究者自己建立的,是由“我”建构的模拟性的理论思想之境,因此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相应地,文本解读进程可以细化为“符号文本层解释——互动性的意义场的理解——生产性的思想构境”等三个不同阶段。这些构想,在我国学界都曾引起讨论,有赞成者,也有质疑者。以下主要介绍近年来讨论得较多的几种看法。
如前所述,黄俊杰很早就提出了建构“中国诠释学”的主张,近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东亚诠释学”的构想。他的这一主张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以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作为建构“中国诠释学”的主要基础,二是希望把“中国诠释学”扩展为“东亚诠释学”,三是注重对儒家经典实际诠释的总结、归纳与反思。所以,对于他来说,“中国诠释学”和“东亚诠释学”的主要内涵都是“儒家经典诠释学”。他认为,这种诠释学的基本性质是以“认知活动”为手段,以“实践活动”为目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实践诠释学”(praxis hermeneutics)。黄俊杰最近著文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并指出,东亚儒者总是在与“诠释的权威”相印证的“秩序”中以及普遍命题与地域特性的互动中,进行创造性诠释,完成经典意义的再创新。
潘德荣的“经典诠释学”和“德行诠释学”是近年颇有创见的一种构想。他认为,当代西方诠释学的重心从“经典”转向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导致当代诠释学视野中只有“文本”而无“经典”。但“经典”乃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与“价值世界”,“经典”文本的一般化意味着价值取向的失落,导致现代西方诠释学疏于对诠释之价值取向的深入思考。而中国自孔子以来就确立了以“立德”为宗旨的经典诠释传统,这正可以克服西方诠释学的价值短板。因此,他主张 “中国诠释学”应当是以“立德”为宗旨的“经典诠释学”。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这种“经典诠释学”实际上是“以‘实践智慧’为基础、以‘德行’为核心、以人文教化为目的”的“德行诠释学”(Die TugendHermeneutik),它是“继方法论与本体论诠释学之后的新型诠释学”,“不仅意味着孔子所奠定的中国古老的传统诠释理念在当今时代仍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同时这也是我们对世界的诠释学研究作出的应有贡献”。很显然,潘德荣的这种构想,是力求在全球视野和现代学术框架中对中西诠释传统加以反思与整合,并试图在更高层面上将现代中国诠释学“铸造为一个具有更为广泛适用性的理论形态”。
张江近年提出的“中国阐释学”构想,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他认为,当代西方诠释学理论具有“强制阐释”的特点,即理解者在阐释文本时背离文本话语,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具有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基本特征。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他提出“本体阐释”的主张,即以原始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从文本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拒绝前置立场和结论,一切判断和结论生成于阐释之后。但旨在还原作者意图的“本体阐释”如何可能?张江认为,阐释是一种出于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需要的公共行为,理解的主体、被理解的对象,以及阐释者的存在,构成一个相互融合的多方共同体,这意味着作者只能以“公共理性”传达其意图,理解者也只能以公共理性理解作者意图,这决定了有效阐释必然是具有理性、澄明性、公度性、建构性、超越性、反思性等特征的“公共阐释”,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还原作者意图的可能性。
李清良近年也发表多篇论文,极力主张现代中国诠释学即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他指出,根据我国学术传统,对于各种基本的生存活动不断进行反思、探索以建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各种分殊之道,始终是一项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化任务;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一项生存活动,诠释活动同样需要建立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反思与规范的“诠释之道”。“诠释之道”包括既互相区别又相互统一的多个层面,既有作为形上之思的存在论一层,又有落实此道的规则与方法论一层,同时还有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诠释智慧一层;将这三个层面贯通统一之后,诠释理论便不是无关实践的纯理论,诠释智慧也不是无法操作的空智慧,诠释方法更不是横通一切的死方法。任何独立自足的文明体系都有自成一体的 “诠释之道”,因而并不存在唯一普遍的“诠释之道”,不同文明的“诠释之道”有着不尽相同的问题意识、理论立场和价值追求,虽可以也应当相互对话和学习,互资启发与借鉴,但无法相互取消和替代。各大文明虽有其传统的“诠释之道”,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都必须适时通变,建立现代“诠释之道”。从西方现代诠释学的一枝独秀到各大文明现代“诠释之道”的百花齐放,正是“后西方”时代的主要趋势。由于中华文明长期以来以儒家传统为主流,其现代“诠释之道”的主要发展方向也将是基于但不限于儒家传统的“仁道诠释学”,以一套具有现代意识和形态的仁学观念,对诠释活动的性质、地位、工夫、方法、目的与关怀等从根本上加以全面系统的反思、解释和规定。
以上这些构想的学术背景与具体思路虽然各不相同,但大多具有会通中西的包容性和非常明显的“中国性”,这既源于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开放性传统,也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诠释学研究逐渐走上了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道路。
五、结语:反思与展望
以上相当简略甚至是挂一漏万的梳理表明,经过四十年来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在对西方诠释学的引进和研究方面,已从最初以译介为主逐渐走向译介、研究和反思并重;在中国诠释传统的研究与清理方面,已从较宏观的整体研究逐渐发展为以专题和个案为中心的更加深入和细致的考察;在现代中国诠释学的探索和建构方面,则从以海外学者为先锋逐渐发展为以我国大陆学者为主体。总之,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诠释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形成了一支相当庞大的研究队伍。中国诠释学研究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不断拓展、持续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当然,也有一些明显不足的方面有待我们克服。比如,在西方诠释学的译介和研究方面,目前虽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离全面而准确地译介和研究西方诠释传统仍有很大差距,同时也缺乏足够反思,不少学者仍以当代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唯一真理或最高水平。又如在中国诠释传统的清理和研究方面,对于道家道教诠释传统、佛教诠释传统、史学诠释传统、文学诠释传统、法律诠释传统、教育学诠释传统、政治学诠释传统以及整个中国诠释传统中的众多个案和专题还研究得很不够,至于对中国诠释传统在近现代的转变、创新和发展,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更少,在译介和研究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成果方面,我们更是刚刚起步。再如在现代中国诠释学的探索和建构方面,目前虽已提出了不少构想,但离成熟的理论形态还有较长的距离。但我们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逐渐得到解决。因为现在我们不仅有专门的学会组织——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诠释学专业委员会,也有专门的学会刊物《中国诠释学》,更有将近十个诠释学研究中心和一支来自不同学科的庞大研究队伍。可以预料,我们将会越来越全面准确地了解西方和其他文明的诠释传统、中国的经学儒学诠释传统以及其他各家各派各学科的诠释传统,包括近现代中国学者经过不懈努力和探索而初具规模的现代诠释传统。我们所期待的“现代中国诠释学”也终将建立起来,它很可能会有多种形态同时并存(像传统中国儒释道并存一样),但必会以“和而不同”的方式一道构成现代中华文明的“诠释之道”,解释、反思和规范现代中国人的诠释活动,并与其他文明的“诠释之道”不断进行对话交流和互资互鉴,共同为文明对话、世界和平、文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作者简介
李清良(1970—),男,湖南新宁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中西经典诠释传统。
张洪志(1987—),男,湖南新化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中西经典诠释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