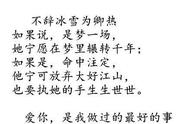赫塔·米勒

◎裴雪如
写作,永远与两个因素息息相关(同时也被其所制约),其一是风格,其一是历史。赫塔·米勒通过写作所勾连的,一端是清澈的诗意光晕,一端是浑浊的历史沉沙,两者被奇异地融合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眩晕同时又令人着迷沉醉的文学书写奇迹。
在20世纪的俄国文学界,以什克罗夫斯基为首的形式主义理论家们提出了奇异化的概念。在《散文理论》中,什克罗夫斯基阐释道:“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文学语言,是日常语言的变形、扭曲与重新组合。赫塔·米勒的小说可视为奇异化理论的具象折射,在小说的宇宙中,叙事的进程不再按照常规的线性方式延伸,变成了混乱交缠的线团;历史的背景被隐入语言的烟雾缭绕之中,读者只能在支离破碎之中朦胧地寻觅现实的虚影。她的小说有点像塞巴尔德的某些作品,同样关乎历史最隐秘的创伤,同样以诗的语言与小说这一文类结合,同样以迂回而暧昧并带着象征性的方式勾勒故事的线条。
相较于赫塔·米勒最负盛名的迷宫般的罗马尼亚三部曲,《呼吸秋千》显得如此明晰。在后记中,赫塔·米勒明确了小说的历史背景与书写原因。1944年,苏联军队深入罗马尼亚境内,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内斯库被捕并被处死,罗马尼亚从德国的帮凶变为苏联的盟友。一年后,苏联向软弱无力的罗马尼亚政府强制索要其境内的17至45岁的德国人为苏联的战后重建卖身出力——他们被流放的地方,史称“劳改营”。
《呼吸秋千》作为一本虚构小说,其建筑结构模仿的是一个以书写纳粹集中营而闻名的作家普里莫·莱维的非虚构作品如《元素周期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每一小节由一个小标题所统御,内容则是关于从标题展开的描绘与反思。迥异之处在于,首先,普里莫·莱维的作品显而易见是非虚构的,《呼吸秋千》虽然建立于真实历史的地基,但终究是虚构的小说文本。其次,集中营题材因其灾异的惨绝人寰的独特性与令人惊骇的恐怖性在全世界得到了无数关注与探讨;而劳改营,因为它让人想起了罗马尼亚法西斯的历史,成为了每个人绝口不提的禁忌——这个话题和身在劳改营的男男女女们一样在历史长河中流离失所。赫塔·米勒的母亲及村里的人都曾经是劳改营的一员,但“只有在家里,或是和自己也有过流放经历的很熟的人之间,才会谈起在劳改营的岁月。即使谈起来,也只是暗示而已”。直至朋友奥斯卡·帕斯提奥向她回忆当年的细节,赫塔·米勒才萌生了创作的念头。更为重要的是,普里莫·莱维更倾向一种平实的娓娓道来,赫塔·米勒则通过文字孕育出了一种同样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截然不同的风格印记。
赫塔·米勒的比喻,似乎总是能涌入最不可思议的联想领域,同时又亲密地贴合着劳改营生活本身。“树下是白雪覆盖的屋顶,像空中搭建的工棚里被压弯的床铺。”“有些植物只靠明矾生长,开的紫花就像凝固的血,结的果子像上了褐色油漆,宛如荒原草丛中干了的土狗血。”
此类型的比喻也同样出现于《心兽》之中。一方面,这凸显了小说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主观视角,劳改营的烙印如影随形,如疫症般感染侵蚀着四面八方的世界,让叙述者,同时也让读者如附骨之蛆般无法摆脱。另一方面,从客观效果来说,比喻又显得别具匠心不落窠臼,绽放出了奇异化的辉耀,自然而然同时又闪烁着惊奇。小说所采用的另一种比喻是紧缩的省略喻词的复合构词法隐喻。这是一种特别的现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技巧类型。小说的名字《呼吸秋千》本就是一个复合词,同样类似的还有“饥饿天使”“面包法庭”“腹泻炉渣”——这些复合词发挥着深远的意涵。同样的,这种复合词的构成也源自于劳改营的生活——它们的反复出现使其化为一种标志、一套理论,一个外界不理解但在劳改营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
饥饿,是《呼吸秋千》中一个沉重的主题。饥饿这一词汇在小说中被高频率地重复使用,如同小说的脉搏般不停地跳动。小说的叙述者雷奥帕德·奥伯克将其称之为慢性饥饿病:“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原有的饥饿之中。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跃入旧的、永恒的、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在劳改营中,饥饿是头等大事,人被饥饿所攥紧、束缚、驯服,小说中饥饿被化成“饥饿天使”。饥饿天使对于人拥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力,人只是为了服侍它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饥饿天使就是劳动营本身。赫塔·米勒通过语句持续不断地唤醒着饥饿天使的两大特点:无所不在、独裁控制。
《呼吸秋千》中还有一种以食物为喻体的比喻类型,“每节车厢都装着核桃、榛子、玉米粒、豌豆粒大小的煤块”“管道上结着冰柱,像玻璃做的白萝卜”。这种比喻除了让读者领略文学化的笔触,更是通过这种主观视角令我们感知到饥饿业已深入骨髓。同样,在小说的句法中,不再是人感受到饥饿,而是饥饿统治着人,人常常处于被动的位置,不再充当为主语。“最后一束日光将果实悬垂于我们面前”,在这里赫塔·米勒所暗示的,并非是人看见了果实,而是物(日光)使人看到了果实。句子常常以“主动转换”的形式出现,物——就如小说所言“饥饿就是一个物”——总是处于主导地位。人甚至和他的关节、肢体、身躯分离。人,总是麻木不仁的,而代表着人类性格的形容词却被安置在了物品和抽象概念上。
饥饿天使衍生出了另一个崭新的词汇——面包法庭。法庭是秩序律法的象征,而在劳改营,能充饥解饿的面包就是它的法典。小说有一节描述了面包法庭是如何粗暴野蛮地对“犯罪者”执法。阿尔伯特·吉翁忍饥挨饿地省下了五块面包,却被卡尔利·哈尔门偷窃。没有审问、没有辩解、没有任何语言的交流,阿尔伯特·吉翁直接挥舞拳头诉诸暴力。而这一举动大大激发了其他人的嗜血野性和冲动,一群人疯狂地对卡尔利·哈尔门进行围殴,人变为原始的野兽(讽刺的是,这其中有一个人的职业正是律师)。往后的日子,这件事绝口不提一切一如往常。赫塔·米勒这样阐述了面包法庭的逻辑法则:“面包法庭不审判,只施罚……面包面前人人平等,面包的公正没有前奏和终曲,只有此刻。要么完全透明,要么完全隐秘。无论怎么说,为了捍卫面包的公平性而施行暴力,和吃饱喝足的人使用暴力,根本不是一回事。面包法庭不认通常的道德。”
《呼吸秋千》也充斥着一些格言式的语句。每一次格言的效果都等同于一场微型但有力的爆破。罗兰·巴特认为格言的本质是对照。“跟世界不再有任何关系,应该说,这世界不再和我们有任何关系。”赫塔·米勒借此抵达了一种残酷的真实性:劳改营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本末倒置的世界,一个相对于外面的世界颠倒过来的世界。精神需求必然被摒弃,人沦落为肉体的奴隶,用尽全力只为了能在劳改营舒服一点、温饱一点。即便如此,对于他们,暗无天日的日子是看不到尽头的,他们是活着的僵尸。
集中营更加可怖,但毕竟,集中营与战争紧密相关;而劳改营,完完全全发生在和平时期,外面歌舞升平,里面奴役压迫。赫塔·米勒不断提及和平一词,物是却人非,他们离开与后来回到的世界一直鲜花锦簇,而他们可以被取代,就像雷奥帕德·奥伯克被那个素未谋面的新生弟弟取代一样。这些人被永远地戕害,同时也被永远地遗忘。
卡夫卡曾经以这样一句话激起了现代主义的浪花:“希望是存在的,但与我无关。”而对于赫塔·米勒想要书写与怀缅的人来说,和平是存在的,但与他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