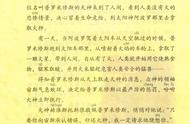“现实”和“现实性”在德文中都是Wirklichkeit,在英文中都是reality,在中文里也没有明显的分别。这是因为,在各个自然语言中,“现实”与“真实”、“事实”被当作同义词,“现实性”被当作对“现实”的抽象强调。其实,性质是事物存在的确定状态,不确定的存在状态不是事物的性质。确定性作为一种性质,是事物在某个时期处于确定的状态,却被我们当作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性质,是事物在某个时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而是我们对其不确定状态的确认。因此,“现实性”是指事物的确定的存在状态,“现实”则是指事物的不确定的存在状态,“现实的”是事物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的存在状态,“现实性的”是事物在某个时期不会发生变化的存在状态。换言之,“现实”是正在进行中的事件,“事实”是已经结束了的事件,因此,可以说“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不可说“现实是不可改变的”。
黑格尔试图区分“现实”与“现实性”,保留了自然语言中“现实”与“事实”的同义词关系,却把“现实性”说成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从而把“现实性”披上了“必然性”的外衣,所谓“合理的必然是现实的”、“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有现实的美名”。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是指作为感性直观对象的“现实”,这是以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修正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如是观之,不能感性直观的“理论的现实”便如同“圆的正方形”,是一个逻辑悖谬。
旧哲学只有“观念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分别,还没有产生“理论的现实”与“客观的现实”的分别。作为旧哲学中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有一句传世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意思是说,现实的东西必定合乎某种必然性(如规律),合乎某种必然性(如规律)的东西必定会成为现实。在这句名言里,黑格尔用一个“理”字把“理论的现实”与“客观的现实”混同了(这种混同最早出现在老子那里),即两个现实遵循同一个“理”,从而存在着共同的规律,这种混沌不分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尚未在德国出现的现实状况在德国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宋明理学也是这种前资本主义的反映),从康德到黑格尔都还没有意识到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是不同的两种规律。黑格尔的哲学化的宗教信念是,“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只要把握了两个世界所共有的“理”,就可以实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旧哲学困囿于主客观二元论的观念划分,尽管在两个世界(观念的世界与物理的世界)的关系上,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也仍然无力推出两个现实(理论的现实与客观的现实)的划分,更是无法对何以会有“理论的现实”做出恰当的解释。我们现在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两个现实的分别以及“理论的现实”的成因做出人本主义立场的解释。
把一些信息或知识加以编号,或者把它们一五一十地堆集排放,对于记取它们几乎是无济于事的(例如全班同学的学号无助于终生记忆各个同学),只有把它们用事件或故事的方式编织起来,才会对于记取它们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π值的记忆,用汉语谐音的方式把这个没有任何规律性的数值编织成一个故事,山巅一寺一壶酒,尔乐苦煞吾,乐尔乐苦煞吾,……。只要有了一定的中国文化积累的人,对这个故事看过一遍,就会终身不忘。这是因为,大脑神经元的活动机理是,记忆不是像刻字那样刻在单个神经元上的,而是由一组不确定个数(少则几十多则上万)的神经元组成一个联接模式(可以类比为电子回路)来存储(记忆)和激活(提取)的。把一组信息以某种意义关联起来,有助于大脑记忆和使用这些信息,即使赋予的意义并不是这些信息本身所固有或可能具有的。所谓“意义”,就是与人的活动有关,由人的行为形成的事件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说,人脑不是数字处理器,而是事件编织器。
所谓“理论的现实”是说,每个人看到的东西未必意识到,意识到的东西未必认识到,认识到的东西未必构成一个有着因果关联的体系。这是因为,人的思维不是“透镜”,而是“滤镜”,客观现实中有哪些东西,它们是怎样的,并不是像镜子反映一般进入人的思维活动中,而是取决于人是怎样与客观现实发生关系的,这种关系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客观之物。也就是说,人不仅是自为存在的主体,更是建构人与外界关系的主体。只有当认识到的东西作为认识的内容由因果性关联起来并且系统化为一个体系,人脑才能有效率的存储、理解和运用它们。
由于人自身的资源(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只有把认识到的东西以因果关联方式组合成一个系统,才能把握住越来越多的认识内容。所以,有没有因果关系意识,因果关联的水平和程度如何,决定了个人的认知活动的范围、容量和深度。同样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有没有因果关系意识和能力,出现了个人之间在信息获取、处理及利用上的效率差异。又由于因果关联方式不是唯一的,因而同一个客观现实会有不同的“理论的现实”,同一些认识内容也会有系统化的个人差异。再者,每个人的头脑里都会有许多个观念,但是并非每个人头脑里的观念都系统化为一个体系,因而每个人头脑里都有“观念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头脑里都有“理论的现实”。
“理论的现实”并非一定就比“客观的现实”更好,而是自身资源有限的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人定胜天”的“定”不是“必定”,而是“安定、安排”,是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生命物是负熵体,只有化无序为有序、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才能得以生存,人类的理性能力是生物本能的升华。对信息和知识做出人为安置,用因果关系把它们关联起来并且形成一个系统,才能有效率地利用它们,才能接纳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因此,“理论的现实”未必比“客观的现实”更好,却必须比“客观的现实”更适于人自身的活动要求。
“理论的现实”比“客观的现实”更重要,并不意味着先有前者而后有后者,更不意味着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映、后者是前者的投影。反映说与投影说的对立,在旧哲学上表现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冲突。反映说存在的问题是,把“理论的现实”仅仅看作是“客观的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理解为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投影说存在的问题是,以为只要把理论直接运用于现实就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而不必对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随时做出协调处置。米塞斯把经济学原理贴上“先验的”标签,既会导致反映说,也会导致投影说,从而造成观念混乱。恰当的观念是,“理论的现实”不是对“客观的现实”的反映和再现,而是对后者的去蔽和塑造。“理论的现实”与“客观的现实”之间不是谁符合谁从而谁服从谁的问题,而是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以更有效率地行动、以满足行动的目的需要。也就是说,“客观的现实”不存在目的性,只有“理论的现实”才具有目的性,即“理论的现实”是为了满足人自身能力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说“理论的现实”本身存在着独立于人的目的性,更不是说“理论的现实”以符合“客观的现实”为目的。
两个现实的区别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物质资源的稀缺性与人自身资源(时间和精力)的稀缺性是不同的。人类为了有效率地运用自身资源而形成的经济规律,不同于自然物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然规律,甚至独立于人与物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规律。例如,各种飞行器的飞行规律不是经济规律,却要由经济规律来决定它们之间的优胜劣汰,例如飞机淘汰了飞艇(可以详见张维迎的有关文章)。在表象直观上,私有财产是经济规律得以形成的基础,两个现实的区分才能显明,经济规律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人对自身有限资源的有效运用,财产私有仅仅是激发个人有效运用自身资源的方式之一。
概念是思维的工具,要想解决理论问题,就必须有适当的概念工具,并且恰当地使用这种工具以建立起工具与问题之间的关联方式。概念工具的改进同样会带来新的理论问题,例如,“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改进,由此产生的理论问题是经济范畴的排序问题,连带产生的问题便是这个排序的起点是生产资料、分工合作还是企业家判断。因为,分工合作是企业家判断所需的环境条件,而不是企业家判断所必须遵循的客观原理,就是说,不会因为存在着分工合作,就自动地产生企业家判断。实际上,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往往表现为对既有的分工合作格局的破坏,从而表现为对分工合作原理的违背,甚至不把分工合作当作自己必须遵从的原理。
原因由一组条件组成,发展的结果决定了发展的原因是怎样的。就人类历史而言,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会对初始条件做出改变,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原因,并且对其之前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原因及要素做出新的排序,以至于先前时代被当作必要前提的东西,在当下阶段成为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例如,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确立之初,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分工合作当作经济学理论的起点,并且把分工合作归因为人的“本能”,由此排列各个经济范畴的次序,而在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以“企业家判断”作为经济学理论起点,从而重新排列经济范畴的次序,即:企业家判断→生产要素组合→企业行为边界→价格/市场形成→分工格局→产生财富。由此,经济学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的现实”,处于经济范畴序列起点位置的要素不再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