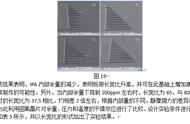文/巴金
窗外露台上正摊开一片阳光,我抬起头还可以看见屋瓦上的一段蔚蓝天。好些日子没有见到这样晴朗的天气了。早晨我站在露台上昂头接受最初的阳光,我觉得我的身子一下子就变得十分轻快似的。我想起了那个意大利朋友的故事。
路易居·发布里在几年前病逝的时候,不过四十几岁。他是意大利的亡命者,也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不能和解的敌人。他想到他没有看见自由的意大利,在那样轻的年纪,就永闭了眼睛。1927年春天在那个多雨的巴黎城里,某一个早上阳光照进了他的房间,他特别高兴地指着阳光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可喜的事。我了解他的心情,他是南欧的人,是从阳光常照的意大利来的。见到在巴黎的春天里少见的日光,他又想起故乡的蓝天了。他为着自由舍弃了蓝天;他为着自由贡献了一生的精力。可是自由和蓝天两样,他都没有能够再见。
我也像发布里那样的热爱阳光。但有时我也酷爱阴雨。
十几年来,不打伞在雨下走路,这样的事在我不知有过多少次。就是在1927年,当发布里抱怨巴黎缺少阳光的时候,我还时常冒着微雨,在黄昏、在夜晚走到国葬院前面卢梭的像脚下,向那个被称为“18世纪世界的良心”的巨人吐露一个年轻异邦人的痛苦的胸怀。
我有一个应当说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的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了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为了浇熄这心火,我常常光着头走入雨湿的街道,让冰凉的雨洗我的烧脸。
水滴从头发间沿着我的脸颊流下来,雨点弄污了我的眼镜片。我的衣服渐渐地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模糊的雨景,模糊……白茫茫的一片……我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来走去。转弯时我也不注意我走进了什么街。我的脑子在想别的事情。我的脚认识路。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马路,我不留心街上的人和物,但是我没有被车撞伤,也不曾跌倒在地上。我脸上眼睛看不见现实世界的时候,我的脚上却睁开了一双更亮的眼睛。我常常走了一个钟点,又走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我回到家里,样子很狼狈。可是心里却爽快多了。仿佛心上积满的尘垢都给一阵大雨洗干净了似的。
我知道俄国人有过“借酒淹愁”的习惯。我们的前辈也常说“借酒浇愁”。如今我却在“借雨洗愁”了。
我爱雨不是没有原因的。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ihxdsb,*33864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