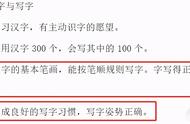作者~蔡沙弟

当年的我,棒小伙儿!米饭能干四、五碗,馒头一顿八、九个。干上铁匠也不惧,红炉跟前寻快活!
武汉市乃至湖北省,抢枪乱军那会儿到底因为子弹乱飞,手榴弹四下轰鸣死了多少人,没有见人统计过。反正那会儿报纸上也好,造反派的各种小报也好,总是见到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并且越来越好。"
那时候总觉着死点儿人没事,关键得看形势好不好?形势好了,死点儿人也不算什么。
有了枪支弹药后人就牛逼哄哄了。特别是武重厂武重技校的小年轻们。刘太平被干掉后,技校基本上也就成了"钢派"的一统天下。年轻人好大喜功,受到"天下造反派是一家"这句口号的鼓舞,将几辆"嗄斯六九"苏制吉普车外部都銲上钢板,四下里开出射击孔,整成一副装甲车的模样。他们也要向外输出革命。听说保定的造反派受到了打压,马上就荷枪实弹,开上"装甲吉普"就上保定去"支左"了。
如今回想一下,当时全国各地武斗如火如荼,真正是乱成一锅粥了。尽管如此,当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不管天下有多乱,反正是:"乱了敌人,锻练了群众"。有这句话兜底,多乱也不怕!
朱鸿霞这段日子是几乎没回厂里打过铁了。他这时在干吗?后来他受到审判时,对湖北省内的武斗承揽了很大的责任,应该还是不冤枉的。
中央文革终于发现,"抢枪乱军"发展下去形势将不可收拾。全国武斗升级不说,连解放军当时也有被打死的情况。于是在当年的七月,连发两个公告,简称""七.三"、"七.二四"公告。措词严厉,要求全国各地各派停止武斗,并将所抢枪支弹药立即交出。
但此时有枪在手的各地造派已有几分尾大不掉了。"有枪就是草头王"。老子怕谁?!
当时武重厂的情况就是如此。几乎是无人理睬这措词严厉的两份公告。
我是个复员军人。虽然我在部队服役的时间不算长,但我对短暂的军队生活的一点一滴莫不记忆犹新。我的父母都曾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我爱我服役过的军队!而且我在部队时也曾经历过"抢枪"事件,并非常痛恨。出于这种种原因,我在"七.三公告"发布后的第二天,我就将剩下的三枚手榴弹从床底下取出,用我的黄挎包装上,带去厂里,交到了军代表的手上。军代表眼睛睁得大大地,用略带点儿惊讶的神色瞪着我。记得好象我是武重厂里第一个响应公告,交出枪支弹药的人。当天中午我去厂前食堂打饭时,看见了军代表贴在厂子大门口,用红纸写就的表扬信,我的名字赫然其上。你别说,就在我其后,武重厂也真的出现了一股上交枪支弹药的小高潮。不久"七.二四"布告也随即而至,口气就严厉许多了。军代表也在厂里开了几场大会,划出了交出枪支弹药的最后期限。"逾期不交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一看来真的了,厂子里的造反派才陆续交出了抢来的武器。也是至此时,武汉市才没有了子弹不时划破夜空的喧闹。
那时节,全国发生了一件很热闹的大事。*在北京一次接见外宾时,外宾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送给*几枚热带水果~芒果。主席没吃。而是将芒果转送给了全国的工人阶级。
说句真话,我那时在人世间也混了将近二十年了,自以为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但芒果这种水果,当时别说见过吃过,连听也没听说过。
芒果有一枚*送给了武汉的工人阶级~这是多么大的面子多么珍贵的礼物呀!芒果是用飞机空运来武汉的。朱鸿霞代表武汉的工人阶级,在飞机场豋上舷梯,双手捧过了这枚珍贵的芒果。然后乘坐大卡车~卡车用绸缎围裹,四周彩旗环绕,朱鸿霞站在卡车车厢的前面,手捧一个大盘子,盘子正中置放着那枚珍贵的热带水果,然后卡车车队环绕武汉三镇巡游。让三镇人民都能一睹这枚领袖送来的热带水果的风彩。顺带着也能看看这个取个女人名字的"钢工总“一号头头。
时隔不久,朱鸿霞就又回车间来打铁了。在我们那间小破屋里,"天天读“的仪式搞完后,我一边往脚上套着翻毛大皮鞋,一边就问上他了: "老朱,芒果什么味儿呀?"
他翻我一眼,说"那是*送给全国工人阶级的礼物,你小子就知道吃!"
"废话。"我说,"*不是送给我们吃的?未必是拿来做样子的?"
在我们生产小组,就只有我经常与朱鸿霞调侃几句。我才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儿呢?
他沒有理我,转身告诉陈班长,武汉气候太热了,芒果从外国带来中国,又带来武汉,已经开始流水了,烂了,不能吃了。后来请化工厂用塑料做了枚仿真芒果。他在车上捧着的那枚就是仿真塑料做的。
我有点不依不饶,说道:"流点水怕什么?水果水果,流水烂一点,照样能吃。是不是你们几个接的人分着吃了?" 朱鸿霞白了我一眼。
陈班长笑着打圆场,说我:"你这个小子就是只知道吃。*给的,能随便吃嘛?"
其他人也纷纷与我开玩笑。后来听说,那烂芒果确实扔了。东北人说话,白瞎了。
虽然大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一幕我记得如此之清晰,恍如昨日。现而今芒果已不算什么稀罕物了,想吃了超市里四季都有。但我总是一吃芒果,就想起了当年…。我这人别看平日里大大咧咧,其实心里也蛮小资的。
这以后,朱鸿霞在我们生产小组打铁就又成常态了。
尽管朱鸿霞是全省钢派一号头头,但接触中,我心中对他好像并不十分反感。他也知道我是个走资派子女,他对我也没有什么歧视态度。彼此心照不宣。他是与陈班长同时期的老锻工,也是我的师傅。我们之间的关係总之还过得去。干起活来,他掌钳操作时,我也是认认真真地给他打下手。
那时我非常喜爱练中国式摔绞。因为我上中学时练过,有基础。武汉重型厂摔跤运动当时比较盛行。因为厂子里的很多老工人都是从东北、山东、天津一带过来的,那边的人爱摔跤,自然就渐渐形成一种氛围。厂大门口马路对面是武重厂的俱乐部,俱乐部后面就是武重足球场。足球场边上有一块草地就是厂子里工人们下班后摔跤、练跤的地方。武重技校也有很多年轻学生经常在此摔绞。那个被打死的刘太平就是在这儿练跤的常客。我有段时间也经常来这里看他们练跤。但人不熟,我不愿惹事,就只是站在一边看他们练,没下场交过手。但估计他们不是我的个儿。
我在一吨锤当上锻工后,尽管干活儿挺累,但那时人年轻,好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光打铁还不足以让我长块儿,我就想自己做一些健身练肌肉的器械。我们一吨锤的苏师傅特能理解我,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锻打了一副扛铃,重九十公斤。还打了一对哑铃,单重二十公斤。做出来的器具有模有样,一点儿不亚于商店买回的。杠铃放在车间,有点儿空闲时间我就在车间外面空地上挺举、抓举的练练。哑铃我拿回了家里,天天早上举举。我的力量自打当上锻工后增加的很快。当时的锻件虽然都是蒸汽锤锻打出来的,但仍时常有些边边角角不符合图纸要求,差上个一星半点儿。这时就要靠我们锻工们手挥二十四磅大锤,"叮叮当当"将那缺的尺寸找补回来了。这活儿特累人,别人都躲着,我却特乐意干。"嘿哟!嘿哟!"一口气地抡他个几十百把下,汗水滴在红铁上"滋滋"作响,觉着很解压过瘾。锻工当了一两年后,那胳膊粗壮地象小树桩似的。比如掰手腕,刚进厂时我掰不过苏师傅,一、两年后,我轻易就掰过他了。在武重厂,也有外车间人专门找我来掰腕子的,但从无对手。
那会儿车间一周要搞两次"政治学习"。天气好时大家就坐在车间外面的樟树下读读"人民日报",或学习一下*的"最新最高指示"。工人们学习,哪儿坐得住?学一会儿无聊了,就搞点儿花样。大家伙儿就怂恿我和三吨锤的陈师傅摔跤。陈师傅四十多岁,正值壮年,多年铁匠,身高体壮。文革前没事也爱去足球场摔跤。我生性好斗,别人一怂恿,我就来了劲,先就站了起来,走到场子中央,这下子陈师傅就忍不得了,也站起来走到中央,俩人在场子上躬起身子面对面转圈。都穿着打铁的粗帆布工作服。这工作服结实,与专业的跤衣也不差。我瞅住个机会揪住他的肩膀头儿,抓紧带住他,佯装往左用力,一下身子钻进去,横腿扭胯,连绊带摔,陈师傅一下从我背上一个骨碌摔倒在尘埃。我连忙跑上前将陈师傅从地上扶起来,给他拍着身上的灰。陈师傅有几分惊讶地看着我,半晌问我,你是不是练过?我说,在北京上中学时,练过摔跤。这结果,围坐的工人师傅们谁也没料到。从此我在车间一战成名。 和我同时分到锻造车间的还有几个八二0一城防部队的,平日里也好在车间外的空地上打打擒敌拳,练练捕俘操。我约了他们好几回,摔摔跤,练一练。但他们都不应战。
朱鸿霞是有点儿武术功底的。他的父亲在武重厂宿舍区带小孩练武功,那是我亲眼见过的。朱鸿霞也有武功基础。后来他回车间来打铁了,肯定是有人对他说过,小蔡这小子有点儿功夫。他没有和我切磋过。但估计他那么一个白胖子,纵然小时他父亲教过他一些功夫,日久不练,也剩不下什么了。但他经常在我面前要显摆一下。早上我们都换好了工作服,走向锤台时,他经常当着我的面,紧走几步,突然腾空跃起,"啪啪"手击脚面来上两个飞脚。我知道他这是在向我示意:别看我胖,我也是个练家子!从这些小事看来,他的好胜心也是挺强的。
我们锻造车间自己有个洗澡堂。那时武重厂只有几个工作强度超大,工作环境肮脏的车间自己有洗澡堂,如翻砂车间、锻造车间等。我们每天下班时,必须要先洗个澡。我们每月每人发一块大肥皂,专门洗澡用的。不然浑身是灰尘、油泥、机油渣、铁屑等,怎么出门见人?
澡堂就在车间门囗右手边。里外两间小屋,外面一间是更衣室,墙上钉着一排挂衣钩,下面是一块约有三米长的木板,给我们当凳子换衣服。
我们一般是在下班前打完最后一炉铁后,在锤台旁的换衣处就脱得只剩一条小裤衩了。然后光着大膀子穿着自制的木拖板,毛巾往肩上一搭,手中握住肥皂~就是极普通的那种洗衣服的粗糙肥皂。天热时就从容地"呱哒呱哒"地慢慢从车间中间的那条"官道"上向澡堂走去。大约有个五十米左右距离。冬天严寒,朔风从车间刮过,打着唿哨,我们就缩脖聳肩, 一溜小跑,"呱哒板"响成一片。朱鸿霞有时跑在我的前面,白白胖胖,身上肥肉一颤一颤的,煞是有趣。在澡堂子里,一片热气蒸腾,十余个莲蓬头,哗哗地热水一倾如注。锻工们有老有少,全赤条条地痛痛快快地冲着澡。你别说,出了一天的大力气,这下班前的这一通热水浴,委实解乏。脑袋上抹上一层肥皂泡沫,闭上双眼,任热水从头顶淋下,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滋润地张开了,人都不由地咀里哼起了小调。锻工们都爱在澡堂子里开玩笑,趁人这会儿脸上有肥皂,就飞快地跑过去,照屁股上打一巴掌,然后再快速溜回自己的莲蓬头下佯装洗澡。等挨了一巴掌的人冲洗掉头上脸上的肥皂,睁开眼睛时,满澡堂子里雾气蒸腾,真一时分辨不出是谁打的?这种玩笑几乎天天洗澡时都有发生,都是一个车间的兄弟,一般也就是开开玩笑,也没有谁计较过。有次我洗澡时,趁朱鸿霞正在冲着头,我照他的肥屁股上就猛搧了一巴掌。大约是将当时父母亲挨斗与这位一号头头联系了起来,这一巴掌有点儿重,有点儿"冒高"。打完后我立马跑回我的莲蓬头下佯装冲澡。朱鸿霞大声叫着,匆匆冲掉脸上的肥皂,睁开眼,一下就认定是我打的这一巴掌,嗷嗷叫着就冲到我面前要打我。口里大声喊着:"开玩笑怎么能用这么大力气!太不象话了!"陈班长等几个人连忙上前将我们挡住分开,朱鸿霞指着白屁股上的那清晰的五指掌印,大声忿忿地说道:"你们看看,哪有开玩笑用这么大力气的?!"
我也自知理亏,挠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是下手重了点儿。要不,朱师傅你也还我一巴掌吧!"我边说边转过身子将屁股对着他。
众人都笑着在一旁打圆场,朱鸿霞这才渐渐气消了。
第二天早上上班"早请示"时间,我又再次向他道了歉。他也原谅了我。说:"你小子开玩笑没轻没重,早晚要出事的。"我连连点头称是。原先我对他总是称做"老朱"。我一个复员军人二级工,他三级工,我称呼他"老朱"也无可厚非。可自从这次"洗澡门"事件后,我总有点对他心生愧疚,称呼也就改为"朱师傅"了。盘点一下,我还是划不来呀!
我是一九七三年初离开武重厂的。后来我当了钳工,又去读了三年"工农兵"大学,还去公安局搞了两年"反扒"。我在社会这所大学里混了个"溜够"。终于在七九年文革结束,被砸烂的"公检法"恢复重建"时调进了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我一直以为,以我的成长经历与人生阅历,以我已形成的人生观,我要是不干"公检法",那真就是太埋沒了。
我原以为我与朱鸿霞的人生邂逅,在我不再踏进武重厂的大门那天起,也就此打住了。
人的一生啊!要结识多少人啊?!
人海茫茫,人与人有过交集已属不易!多少年后竟然不经意间又会相逢,岂非天意?!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文g中在"砸烂公检法"的大潮中被取缔了。一九七八年久违的"公检法"又被"恢复重建"。我一生自打小时看过《三俠五义》后,就在心中立起了一个"包公情结",要铲除恶霸豪梁,替天下百姓申张正义!进了检察院,当时确实是遂了我的心願。
那时的检察机关,还属于劫后重生的草创时期。没有具体的办公地址。在武昌首义路省委第二招待所借了几间房子做为办公地点。
一年后,"两案"专案组也搬进了这家招待所。所谓"两案",是指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专案。其实真正的两案成员全在北京。湖北省的两案抓的人基本都是文革中的本省的造反派头头,朱鸿霞首当其冲。他是省内最大造反组织"钢工总"的一号头头,人人皆知,抓他也算不上冤枉。
我那时中午在招待所食堂吃完中饭后,一般都是找人下象棋度过中午的休息时间。"两案专案组"有个姓刘的伙计也酷爱下棋。他是从下面区里公安分局抽上来搞"两案"的。我们俩下过几次棋后,关系就成熟人了。他是分局的,我是省里的,他对我也很是客气。从他咀里我得知他正好是朱鸿霞专案组的。这可真是巧巧的姆妈生巧巧,巧到一路去了。我将我与朱鸿霞当年的邂逅经历讲给他听,他连连称奇,陪着我发了一顿感慨。大约半年左右时间后,我们接到通知,说下周要在汉口武汉剧院开"两案"人员的公审公判大会。省市公检法的人员都要去参加。
我找到老刘,告诉他开会前我想与朱鸿霞见上一面,没别的意思,就是当年同事一场,他这马上要去劳改了,见上一面而已。
这要求不高也不过份。老刘叫我届时到了武汉剧院可以先去找他。
当时我们检察机关尚没有自己的工作制服,穿的都与公安一样,一身蓝,加帽徽领章。

当年的我,老成许多,结婚了,有孩子了。在长城上目视远方,将我的未来搜索。
那是一个上午,我们乘坐大交通车来到了武汉剧院。一下车我就先去找到了老刘,他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门口,外面有武警战士站岗。我推门进去,朱鸿霞面朝门戴着手铐坐在一张板凳上。见我和老刘进来,他漠然地看了我们一眼,根本没认出我来。我走到他面前,轻轻推了他一下。 我说:"怎么?朱师傅,不认得我了?" 他抬头看着我,眼晴越睁越大。 "你、你是小蔡?!"他非常之惊讶。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当年在澡堂子里打了他屁股一巴掌的人,如今竟一身警服地出现在他面前。 我说是的。我是蔡沙弟。我跟他说我现在在公检法工作。老熟人了,来看看他。进去好好改造,没准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
因为时间很紧,而且那种环境说点儿什么都不大合适,就纯属见上一面。我感觉着我与他还是有缘份的。不然世界那么大,我遇见过那么多人,怎么就和他兜兜转转经历了那么不平凡的一段日子后又能再见面呢?!
人生啊!有个新词叫"活久见"。就是说你活得时间足够长了,你就总会见多一些大千世界里面的形形色色。
朋友们,这段"活久见"我就写完了。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