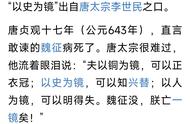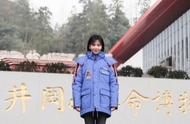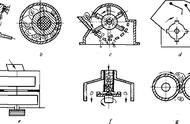唐晓敏
中国史学的发达。黑格尔: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岳麓书社,2010.
中国文化中,史学之所以特别发达,主要原因是政治的需要。即中国古代政治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利于政治。《战国策•赵策一》:“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改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成语,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以作后来的借鉴。
古代的帝王“以史为镜”,以历史为借鉴。汉承秦制,汉朝建立后,刘邦基本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史官制度也不例外。为了从秦亡中吸取经验,防止汉朝重蹈覆辙,刘邦要求陆贾全面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通古今变化的要求,并且沿用了秦朝设置的专门史官太史令,其负责天官的事务,并同时开展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于著述。总的来说,西汉的太史令主要负责的是天文星历和历史记录,最有名的太史令即是司马迁,他写下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的《史记》。与刘邦相似,李世民在掌握政权后也极为重视对隋亡经验的总结,十分注重修史,他在位期间,不仅完成了对《隋书》的编撰,还完成了对《晋书》等前朝历史的编撰。此外,李世民还专门在禁中成立了史国馆,由宰相来专门监理修史。同时,唐初还专门设置了起居郎,后来又在中书省专门设置了起居舍人,主要负责来记录皇帝的起居言行。随着史官制度在唐代的进一步分科和史官职责的进一步明确,史官制度至此也日趋规范化和系统化,得以真正确立。
李世民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资治通鉴》就是“帝王的镜子”。同时,儒家信徒也以历史来约束皇权。“二十四史”中,有八部修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梁书》和《陈书》是姚思廉在其父姚察《梁史》、《陈史》草稿的基础,扩充内容而成。《北齐书》是李百药在其父李德林所撰《齐书》的基础上撰成。《周书》为令狐德棻编撰。《隋书》的总监是魏征,同修的有房玄龄、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贞观名臣。《晋书》的主修者是令狐氏,房玄龄为监修。《南史》、《北史》为李延寿撰写。
历史是士人的修养,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中国传统教育特别重视历史教育。与古人接触,是培养人格的重要方法。所谓“尚友古人”。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是面向古人开放的。《史记》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韩愈《出门》:“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中国史书类型多样。有传记体的史书,正史的《二十四史》都是传记体。纪传体是将人物事迹与时间结合而成的文学有机体, 用来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一部《二十四史》就有3219 卷,450多万字。
清赵翼论之云:“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两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史记》之后,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成为我国正史的规范, 这不能不归功于《史记》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日本学者斋腾正说:“读一部《史记》, 如接当时人, 亲睹其事, 亲闻其语, 使人乍喜乍愕, 乍惧乍泣, 不能自止。”这就是《史记》人物的感染力。
编年体的史书,最早是《春秋》。《春秋》的记事极为简略,每记一事只用寥寥数语。如“隐公元年”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种文字大概是写给当时的鲁国国君和执政大臣们看的,因为这些事他们都是亲身经历,所以只要记下时间和事件梗概即可,类似于备忘录的性质。然而,后世之人读了这些文字就会感到茫然。为了更好地明白文字背后的具体故事,就必须借助“传”。“传”就是解释“经”的文字。《左传》一*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十二代国君、254年间的历史,比《春秋》多出13年。此书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从而详细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的历史面貌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描绘出一幅春秋时代的历史画卷。它还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史实,而且还征引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在体制上最大的特点是史事分年记叙,散见各处。
如同《春秋》记事一样,“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一人一事往往散见于各处。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活动,横贯襄、昭二君44 年之间。这种体制造成了人或事件的简单、片面、支离破碎,很不利于把人物作为中心进行描写。
古代的史学著作,还有一种体裁叫“有纪事本末体“,其特点是,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它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新体裁,从而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这种体例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朝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通鉴纪事本末》将《资治通鉴》所叙述的一千三百余年间史事,总括为239篇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史事,每一件史事又由若干细节构成,其中包括众多的人物、情节和场面。这些人物、情节和场面在纪传体史书中存在于所涉诸多人物的传记之中,在编年体史书中则散入事件发生的不同年月之下,往往前后相隔数语乃至数卷。经过袁枢“区别其事而贯通之”,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年份记载和不同纪传之中的人物、情节和场面,受到“因事命篇”的规范而汇聚起来,它们就像一块块“拼图”,共同构成了一件件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由此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以为后世所鉴。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时,给予纪事本末体极高的评价,认为它秉承《尚书》之遗风。章氏对纪事本末体的撰述特点作了如下概括: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 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纪事本末体是古代主要史体之一, 和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为古代三大史体。清代乾隆时所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纪事本末类正式著录22 种, 存目4 种。本世纪三十年代所编《续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著录106 种之多。这是我国古代史籍中的一个庞大的家族, 和编年、纪传二体一样, 完全可以组成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事本末体通史系列。
政书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史学著作。特点是广泛收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材料,分门别类系统地加以组织,并详述各种制度的沿革等。政书一般分两大类,一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式政书,名称中一般有“通”字,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一为记述某一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式政书,称为会典、会要,如《唐会要》、《元典章》等。
中国史书,还有一大类,这就是“野史”。“野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古人所说的“正史”,首先指的是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也包括自古以来凡“史臣撰录”之书。而“野史”,指的是非官修的史书。“凡不是官修的史籍, 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 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 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野史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也极大地活泼了中国古代史书的编撰形式。与西方的历史著作相比,中国的史书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古代的史书重点是写人。对此,钱穆讲:“历史是文化积累最具体的事实。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西方人看法便与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人为副,倒过来了。因此,西方历史多是纪事本末体,中国虽有此体,但非主要。中国史以列传为主。”蒙文通也说:“中国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即是重人,正史被称为纪传体,学史则有学案体,在人物基础上重建‘学脉渊源’和时代风尚正体现可这一特点。”中国历史著作大多富有文学色彩。《左传》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刘知几说:“左氏之书, 叙事之最。”(《史通• 模拟》)刘熙载也说:“左氏叙事, 纷者整之, 孤者辅之, 板者活之, 直者婉之, 枯者腴之, 剪裁运化之方, 斯为大备。”(《艺概》)
《资治通鉴》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有一些叙述看似平常,但实际上有很高的文学性。如第一百二十六卷:“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馀,春燕归,巢于林木。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国人皆尤之。” “春燕归,巢于林木”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却很震撼。这是因为,燕子筑巢用的是土,土做的巢不能碰到水,所以得建在屋檐下,不能建在树上。这年的春天,燕子不得不筑巢于树上,说明这个地区已经没有完好的房子了。
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并不严格是记实的。其中往往有合理虚构的成分。“晋国鉏麑行刺赵盾而自*前的一段独白,楚国偶读太子商臣和老师密谋弑父,是谁听到的?陈胜把‘大楚兴,陈胜王’的帛书偷偷塞进鱼腹,张良为刘邦失言而悄悄踢脚,又是谁看见的?诸如此类,不可胜举。问题只能这样回答,就是历史记载周公搀和了想象和虚构。钱钟书先生说过:‘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不可尽同而可相同。”(《管锥篇》)秦汉史籍中那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描写,应当都是根据简单的原始书面史料或传闻,再经过史家运用合理的逻辑想象而后形之于笔端的产品。想象和虚构是文学的专利,就这样,《左传》、《史记》才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钱鍾书先生盛赞《左传》述事记言(尤其是记言)之妙,他认为:“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17〕钱先生首先正确指出:“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曰:‘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盖非记言,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钱先生虽觉得那些“生无傍证、死无对证”的独白或对话是“想当然”,有明显疑点,但依然肯定这种做法。
中国古代的史书,对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古典的文言小说里,明显地存在一个“史”的传统。《汉书 艺文志》里提到的“小说”,指的是闾里乡村的“丛残小语”,到了魏晋南北朝,“小说”一词则大多意味着野史杂记一类著作。和现代概念或者接近的小说创作,在唐朝以前都被作为历史看待。现代的文学史家承认的小说雏形或者已经是小说样式的作品,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经》、《西京杂记》、《搜神记》等等,在《汉书 艺文志》和《隋书 经籍志》里都列进史部。不论内容如何怪异荒诞,作者自己却以为写的是历史,至多不过是另外一个世界中的历史。……唐代文人写传奇小说,明明已经是纯粹的文学创作,但总是要在适当的地方交代所写的古寺发生在某朝某年甚至某月某日。唐代小说创作即受史传的影响,唐人多以“传”、“记”、“志” “录”来称自己的小说或小说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