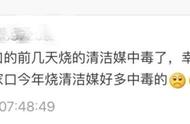作者:陈忠
那年头,家里如果有蜂窝煤炉子,做饭取暖是很方便的。一般家庭,都是烧煤球,或煤末子做的煤饼子。家里有老人还好,如果父母都上班,孩子又上学,炉子就很难封住,搞不好,晚上就要用火头重新点,晚饭往往吃到八九点钟。
一入冬,家家就开始买蜂窝煤,而且,一买就是一冬的。那时,我们这一片的居民,买蜂窝煤要到正觉寺街东头(大约是现在泉城广场科技文化中心南侧)路北的一个国营煤炭店去买。
一天晚上,天空飘着雪,父亲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里的蜂窝煤怕是不够烧的。下雪天,买煤的人少,你半夜起来去排队去吧,早上我接你去。母亲说:外面下着雪哪,把大小子冻着咋办?父亲说:哪这么娇贵啊,穿厚一点就行了。好在那天半夜,南屋的平哥也去排队,有个做伴的。我穿得严严实实的,围上母亲的毛线围脖,和平哥拿着杌扎子步行去了煤炭店。
上半夜,排队的人多,一热闹,也没觉得多么冷,到了后半夜,冻得我直流鼻涕,不得不停地在雪地上跺脚,稍停下一会儿,双脚就会冻得麻木生疼。好不容易等到天亮,父亲拉着从邻居家借的板车来了。父亲将平哥家里捎的饭递给他,然后,给了我两根油条、一个热烧饼和一瓷缸子豆浆。他见我冻得直哆嗦,看了看一大溜排队的人,说,吃完你回家吧,到中午再过来帮我拉车吧。
排队买蜂窝煤,不是为了节省几角钱的运送费,而是,过年前煤炭店送蜂窝煤的师傅不够用的。
那时候,家里有人或有关系在煤炭店工作,是很牛叉的。一是不用起早贪黑去排队,二是给自家送的蜂窝煤是晾晒*,因为刚砸出来的很湿,不好搬运,也不好点火,而且,还容易产生煤气。
我们院里有个姓刘的,是个喜欢吹牛叉的人,外号叫“能不够”,世上没他办不了的事情,越是难办的,他越是能办得到。

杨鹁 绘
一天,晚饭后,“能不够”门口堆满了半吨煤末子和粘土,院子里的人都纳闷:他这是想干什么?开煤店吗?
是夏天,院子里的人都在大门口纳凉。就见“能不够”从自家屋里扯出一根电线,挂在自家门前的小树上。拧上一个一百多度的的电灯泡,然后,个子很矮、很精瘦的他,扒光了上衣,指挥着他媳妇到街西口的自来水站,提回来好几桶水,他吭哧吭哧地将煤末子和粘土拌匀了,抓起了一把,捏了捏,感觉能攥成团了,才歇了下来。他端起大瓷缸子,一口气喝下了大半凉开水。
东屋的齐大爷就问他:刘科长,大热的天,你怎么干起这个来了?
“能不够”媳妇就嘟囔道:他显能的呗……
歇了一会儿,“能不够”就从自家屋里拎出一个长一米左右的手提铁架子,是人工的砸蜂窝煤机器。他指挥着媳妇将拌匀的煤末子往蜂窝煤模子里填满,然后,他吃力地将模子提起来,狠狠地往地上一墩,随即,右脚踩住模子上的盖子,再一用力,一个湿漉漉的蜂窝煤就从模子里挤出来了。
砸蜂窝是个力气活,我在同学家干过,砸上二三十个,就会腰酸腿痛,尤其是手腕子疼得好几天过不来那个劲儿。
那晚上,我很早就被父亲赶到床上睡觉去了,因为,第二天要早起,到北园的藕池捞鱼虫子去。中午要赶回来,给父亲养得一缸金鱼喂食。
至于“能不够”那晚上砸了多少蜂窝,干到几点,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没过三天,有人找他门上来了。
来人肥头大耳,一看就是个小领导。来人当着我们全院人的面,质问“能不够”:你买的蜂窝煤怎么不一般大呢?你从哪煤店买的?我们找他啦啦去,哪能这样干活的,也忒力巴头咧。
“能不够”被搞得很尴尬。他一个劲地陪着笑脸,将那位小领导劝进了自家屋里,并且,关上了门。
后来才知,来人是他单位的老科长,因为听“能不够”说煤店里有很铁的哥们,就信以为真地给了他钱和煤票,没想到,拉回家里的蜂窝煤大小不均匀不说,而且,还不好烧。
据说,老科长始终不知道那半吨蜂窝煤,是“能不够”两口子忙活了一整夜才砸出来的。
那几天,看着“能不够”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就觉得他太能砸了,半吨煤末子啊,也真不容易。

作者介绍:陈忠,男,1960年出生于济南。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市作协主席团成员、副秘书长、济南市徐志摩研究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