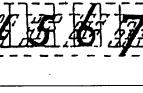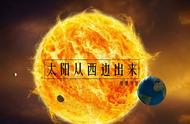今天,三明日报校园版刊登了一位原三明师范学校校友张宗铝的追忆文章,再现了他和同学在学校的一段岁月,勾起许多师范人的美好回忆。


(资料图,来自三明学院校园网)
记录民办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经历——虎头山下的书声
那时候我们被称为“老民办”,那时候我们被逼去读书,那时候我们在虎头山下的狮子坑度过了两年的快乐时光……
“老民办”的求学

原三明师范学校八四级(5)班共有52名同学,除了两名委培的小学妹,其余都是乡村的民办教师,也就是高中毕业后进行短期培训直接上岗的在编的由人民公社发给工资的教师。我们在家乡已经教了七八年,有的甚至教了十几年,于是被叫作“老民办”。
1984年,听说是民办教师考师范学校的最后一年,大家都拼了命去读书,于是这一年也是民办教师考师范学校竞争最激烈的一年,但是我们都考上了,我们来到了位于三明市梅列区虎头山下狮子坑的三明师范学校。
也许你会认为,考上师范学校一定很高兴,因为可以脱胎换骨了。但是我们高兴的起来吗?我们都是多年教龄的“老民办”。我们原本在乡村,有的教小学,有的教初中,学生都比我们早进入师范学校,自己却刚刚踏入师范学校的大门。下课的时候,迎面走来你的学生,笑容可掬地问一声“老师好”,那时的感觉真是不好意思啊!
更让我们觉得不能来读书的原因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班只有几个同学还没有结婚,大多数的同学都有一个或两个孩子,有的同学有三个孩子。我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去学校第十天才生下来的,有个女同学*六个月还要堕胎去读书。理由很简单,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全家人的幸福,我们不得不去读书!
但我们不得不去读书,因为不读书,就要迎接没完没了的考试,比如教材教法、暑期培训等等。我在乡村当了七年的“老民办”,每年暑假都要参加学习与考试。心想,与其年年考试,还不如辛苦一年,考上三明师范学校!于是,考一次就上了。
“老民办”的老师

虎头山下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在众多的老师中,有的是“文革”期间大学教授下放的,有的是中学一线教师抽调上来的,有的是本科院校刚毕业的,有的是大专留校的。就拿我们的班主任王钦焕老师来说,他原先是将乐县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师,因为教学成绩好,被调到三明师范学校来,所以他的教学经验特别丰富。
王钦焕老师年近花甲,走起路来气喘吁吁的。他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是板书非常好,每一个字都非常端正。直到在他垂暮之年我去看望他的时候,字依然写得很端正。他跟我说:“当老师的,字就应该要写好。”
班主任上课一流是公认的,条理非常清楚,重点非常突出。他教的是《语文基础知识》,简称“语基”。虽然书中的知识是枯燥无味的,但他讲得风趣幽默,全班没有一个打瞌睡的,经常笑声连连。他给我们讲的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啰嗦诗》:“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子规啼。”这就是冯梦龙的《宿山房即事》,作者有意重叠同义词,造成一种很有诗味的意境。2016年5月,班主任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第二位老教师是张鹏,他教历史。张老师上课从来不带课本,因为一本100多页几十年不变的《历史》课本,他已经教了几十年,每一个典故在哪一页哪一行他一清二楚。他说:“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他的《资本论》就是给资本主义一巴掌一巴掌地盖过去。”所以我们牢牢地记住了马克思的出生时间是1818年。因为历史课不好上,容易枯燥无味,他采取了激励的办法,那就是回答正确记个“ ”。他的“记个‘ ’”说得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记住了历史课老师“记个‘ ’”,也记住了从来不带课本的非常响亮的名字——张鹏。
第三位老教师是胡树人,他教音乐。胡老师个子不高,头发卷曲,声音特别洪亮,咬字非常准。“1234567——唱得整个人都颤抖起来,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在三明影剧院的演唱,我们都去听了,第一次听到他在舞台上的演唱,我们觉得特别震撼。他的歌声用“绕梁三日”“三月不知肉味”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张清水老师个小,长得清瘦。从他的名字中我们似乎读懂了老师的清贫,读懂了当老师就应该像他那样。他的《几何》课上得比谁都好,他从不带圆规、三角板。“画出来的圆形‘比圆规还圆’”,这就是我们对他的评价。他口齿清楚,语速不快,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听得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小学数学教学》的老师是任君秀。自从她来教我们,我们才知道这世上还有姓任(读音rén)的,但我们许多同学都把它读成了任务的任(读音rèn)。她来上课从来不带笑容,一脸严肃的表情告诉同学们她的课堂上不可以讲话,不可以开小差,更不能睡觉,但她的严肃终究被她自己逗笑了。那是她想提问男生,她叫了曾庆辉,站起来的却是一位女生。接着她想提问一位女生,就叫了我张宗铝。也许是她看到“铝”与“钗”字形比较接近,“钗”是古代女子常用的名字,所以就把我当作了女生,弄得一节课两次哄堂大笑,她也跟着笑。从此,她来上课就再也没有忘记带笑容。她的课非常好,好到极致。
还有,代数老师刘建民,政治老师林樱珠和张梅英,语文老师魏仪,心理学老师宋宙红,体育老师朱天民,美术老师沈庆标等等,都是我们的好老师。
“老民办”的学习

(资料图,来自网络)
前不久,有朋友跟我说,他以前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去三明师范学校混两年回来的,哪里会教书?我跟他说,我也是去三明师范学校混两年回来的,我就教得很好。他说,你是例外。
去三明师范学校读书是我们不得已的选择。去之前大多数人都是想混两年,能拿到文凭就行。到了学校以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那时候,老师都很优秀,我们没有理由不读书。比如,王钦焕老师的课谁会不想听,谁会考不好?比如,张清水老师的课,谁会听不懂?谁会考不好?比如,任君秀老师的课,谁敢在课堂上讲话?谁会考不好?
那时候,我们都是“为人师表”过来的。自己管学生还不是很严,现在反被老师管得特别严。自己要求学生早读课要大声读书,我们的早读课也要大声读书。当时有一句非常形象的话“我们用书声唤醒沉睡的山谷。”“老民办”突然回到了学生时代,也许感到不适应,但日子久了,也就自然了。比如,重新学习我们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汉语拼音,重新学写毛笔字。那感觉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
三明师范学校的考试挺严的,谁也不敢去偷看,谁也不想去偷看。就拿我来说,我的同桌何树明代数就很好,而我代数就一窍不通,我们两个人的语数偏科正好相反。考试时,我们谁也不偷看谁,所以我考代数经常不及格,他考语文也非常艰难。
虽然是“老民办”,但因为1984年考试竞争特别激烈,整体素质也不会很差。1983年以前,名额没有分配到各县,全市民办教师考师范的200个名额中,尤溪县就考上了60名左右。而1984年按县分配名额,100个名额中尤溪县就只有14名,生源比例大大地低于往年。在这14个“老民办”中,有的是“文革”后期尤溪一中的毕业生,有的在高中阶段成绩就不错,因为家庭的劳累,他们错过了考试的机会。
除了文化课的紧张学习,我们还认真学风琴、学美术、学书法等。午饭后,同学们都去午睡了,我总是一个人在教室里写毛笔字。晚自习下课,同学们回宿舍了,我还在教室里练字。虽然写字进步不是很快,但我的基础也挺好。
后来,三明师范学校兼并到位于荆东的三明学院,不再有中等师范学校,但我们还是眷恋虎头山下狮子坑的生活,因为三明师范学校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资料图,来自网络)
那段岁月的生活点滴
在三明期间,我们遇上了全市环城跑。我们都是从乡下来的,虽然艰苦,但都没有跑过这么远的路。每次环城跑,都是三明师范学校的学生夺得第一名。我们抱着坚持就是胜利的理念,十几公里一口气跑下来。虽然没有获得什么名次,但我们为能跑完全程而感到高兴。
当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集体舞,集体舞就是我们在三明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才有的。学校允许我们跳集体舞,但跳一两次就没有消息了,大概是大家没有兴趣的原因吧!
看电影是我们难得的文化消费。周末的晚上,我们三五成群地去看电影,但很少男女一起去。那时候,学校禁止学生谈恋爱,发现就开除。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谁也不想去闯这个雷区。那时候,电影都是战争片。要是能看上爱情片,回来就津津乐道,几天没有休止。
在我们还没有出门之前,根本就没有看见过公园。到了三明,我们的第一愿望是去看看麒麟山公园。麒麟山公园就在学校的边上,在公园可以看到学校的全貌。其实,麒麟山是一座很平常的山。明月夜,短松冈,有很多人去散步,此外就没有什么特色。与众不同的就是山上有动物园,还有索道。索道要收费,我们只能走路上去。在三明师范学校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去麒麟山的次数很少。
学校的后门是虎头山,上面住着部队。全班组织一起上去,但我因事没有去成。听同学说爬山非常累,女同学上去勉强能行,下来就麻烦了,有的还要人背。
学校没有澡堂,再冷的天气都得洗冷水。女生还好,会去学校食堂锅炉边提热水。男生到宿舍的卫生间,开打水龙头就冲。数九隆冬也不例外,但大家都没有感冒什么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跑到山下的澡堂去洗澡,这是我们最奢侈的消费,但也只去一两次而已,因为我们没有钱,哪怕每次一两毛。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喝酒,男生总是避免不了喝酒的。那时候,满园春是三明最热闹的地方。满园春的小巷很长,一共有七八家的小炒店,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餐馆。那时最好喝的白酒是54℃的小角楼,一瓶两三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会喝上半瓶。喝着,喝着,不知不觉醉了,到了周一上午还没有清醒过来,但醉酒的事很少。
(尤溪职业中专学校 张宗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