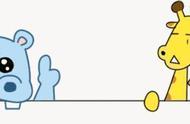回到县上的半天,我好像一直在吃饭,姨姨一直在做饭。虽然姨姨的手艺,在家里是被笑话的对象,但我偏爱的就是这一口饭。那天下午,真的就像黑撒乐队唱的「美美的喋,你就美美的喋……」
到了晚上近8点时分,吃过了最后一顿,我斜躺在沙发上,饭饱而愉悦,看姨姨边收拾打扫,边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这时浑身有一种松弛的疼痛感,极强烈但内心奇怪的觉得挺好,像是特别清晰的提醒我:真的回来了。

猛的,伴着锣声,外面就喝了起来。
「有人喝秦腔啊?」我问了姨姨一声,忙站起来走到窗子前,向外面望去。
「近一向没有,估计今儿人都想耍了」姨姨随口答了句。
「那我下去看看」。

天刚麻麻黑,人们正吃过了晚饭,就在小区大门口左边的街铺前面,围成一圈儿了。老人们多带着一个交叉撑板凳,有人早已坐稳当,张望着正在唱戏的人,有人背着手提着,边漫步边听边寻着坐的地儿,年纪轻一些的,则多数抱胸而站。
唱戏人在中间,两边是伴奏乐者。我混在听戏的人群中,装做个熟人看着周围的一切,见过的却都变得像是没有见过。
「乐器这么全,有的都不认识」我有点问旁边人的意思,又避免尴尬显得是自言自语。司鼓、牙子、勾锣、小锣、梆子、扬琴、铙钹、二胡、板胡、还有一个像是月琴和电子琴,一帮子人这么一坐,基本自乐班全套,立马就能耍将起来。

正在唱的是一个大叔,不对,应该是正在喝(hè)的,或者正在耍的。唱这个字,过于端正甚至有一些萎靡,并不适合秦腔。
秦腔是野的,是能撕裂西北风的呼喊,是钩沉黄土中传奇的赞颂,是身处山尖沟壑面朝黄土背朝天后,立起身来的一嗓子叫天响。那怕是女人声,你也一定会发现,细腻中一样有跟天斗的烈。
此刻,天无斜阳,路有车鸣,一个人,朝天,喝着一板秦腔。在伴奏的推、拉、敲、打,按、弹、抖、捏之下,快、慢、厉、沉的搅动的空中虎虎生气,怎不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