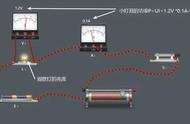“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的《赠花卿》被后人评为意在言外,明赞人所奏之乐美妙,暗讽人违背了乐制,僭越了礼数,用了宫里才能用的曲子。诗有美刺之分,杜甫外美内刺,融二为一,含蓄蕴藉。奈何岁月流逝,祖宗乐制早已不施,历代皇宫尽管热闹已极,礼数尽皆销形遁迹,难怪此诗“刺”渐消而“美”愈彰,“天上”“人间”剥落了寓意,只剩了本义。单就本义而言,我以为只属天上的曲子定是有的,即是“天籁”;只属人间的乐声也是有的,比如《二泉映月》。
旧坟衰草拜娘亲,长跪顾伶仃。二弦枉作鸳鸯侣,却吟得、别怨离情。低首月光孤影,举头泣血双睛。 石街竹杖踏歌行,泉水伴琴音。此身总在伤悲处,问幽暗、何处光明。此曲人间方有,九天只可倾听。
这是我拜谒了惠山东麓的阿炳墓后所填的一阕《风入松》。阿炳的墓原在西郊璨山,后遭损毁,有人收拾遗骨,迁葬于此,墓碑有翼墙三面环绕,呈音乐台形。阿炳生平颠沛,死后再多一次流离,谅也无妨;新坟设计堂正,想是比原来的更佳,却也无他。生前的黑暗也好,身后的光明也罢,拉琴的花子也好,音乐的大师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曲子。
据说阿炳擅器很多,能曲更多,冲淡和扬厉,欣悦和感伤,手弹指挥皆能胜场,譬如琵琶曲《龙船》节奏轻快喜庆,二胡曲《听松》旋律豪放劲挺。但当《二泉映月》响起,这些曲子,不,所有曲子,无不被它的悲伤融化殆尽,而它的悲伤却连一滴都不会被稀释。
我之所以认定此曲只属人间,理由是天上之曲是不会悲伤的。因为悲伤人间独有,九天无奈,只有倾听。阿炳四岁丧母,只能在衰草遍地的旧坟前拜见娘亲,八岁随父当了雷尊殿的小道士,上私塾,习吹奏,二十多岁时交友不慎,嗜鸦片,眠花柳,终致身染恶疾,双目失明,只能走街串巷,卖艺谋生。由于阿炳身份卑贱,文字无传,对他的叙述大多来自街谈巷议,有不同甚至矛盾的说法,但对他身世的悲伤,是没有异议的。仅此一点,便证明苦难为诗人,悲伤成绝响的道理。
对此曲的来历,有不同甚至矛盾的说法。有人说是高人传授的古谱,也有人说是妓院云雨的淫调,前者略近乎神,后者较近于人。我以为旷代杰作与盖世英雄一样,不要追问出处,若一定要寻根究底,则更应留意阿炳到底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去腌臜而纯净的。
对阿炳的品行,有不同甚至矛盾的说法。有人说他位卑心高,外俗内雅,用此曲诉说了自己的一生凄惨,也倾吐了百姓的万世疾苦。也有人说他青年堕落,中年猥琐,目盲后视钱如命,可怜又可气。前者略近乎神,后者较近于人。我以为人的内心与外行未必如一,不可捉摸,更难确定。艺术更是充满了偶然性,大致与天赋、修习的关系较近,与道德、品行的关系较远,就像《二泉映月》的曲名与意涵,有很大的差别。
此曲原本无题。据说阿炳在街角门边、楼头巷尾演奏时,初因信步而行、信手而拉,姑称“自来腔”或“随心曲”。后因常在惠山卖艺,信手以惠山名胜天下第二泉,改名为“惠山二泉”。至于“二泉映月”,是阿炳为慕名而来的专家录音时确认的,当时距他去世,只剩半年。
对此曲的名称,有不同甚至矛盾的说法。有人说定名贴切,二胡的旋律如流水、似月光,展示出惠山之景和清雅之境。也有人说此名幽美疏朗,此曲悲戚伤感,名实难副。前者略近乎神,后者较近于人。贺绿汀说得好,“二泉映月”这个风雅的词儿,与曲子是有矛盾的,与其说阿炳抒写了泉月的风景,还不如说是深刻地抒发了自己的痛苦。
在中国人的乐器里,二胡最长于抒发痛苦。爱乃人生极乐,我从未听过用二胡拉两情相悦的,二弦看似同行,实为永隔,平添一把别泪。阿炳很可能没得到多少亲情,更可能没有得到什么爱情。他虽有两个老伴,但他的曲子里全没有这个消息。
人都是从哭着开始,又多是被哭着结束的,有人引申为痛苦是人生的主旋律,《二泉映月》自是尽情抒发痛苦的悲曲。不过哭并非全然出于痛苦,譬如婴儿,还有始终如婴儿般的艺术家。艺术若只是纯然地抒发痛苦,绝不会成为艺术杰作。与杜诗异曲同工的是,《二泉映月》悲在曲前,呈现的是悲伤之后的安静,世俗之后的文雅,于是出现了无望之后的有待,随心之后的规整——据说阿炳临终前,还在为此曲润饰音律、调整节奏,使之完美。可见阿炳尽管痛苦,但绝不是一个悲伤到绝望的人。如果像九天那样倾听,人们可以发现曲中深藏在暗哑中的光明,潜行于迂回中的通透,不但不会令人沉沉堕下,反而生出一种相反的张力慢慢升起,犹如污水在蒸腾中滤尽了灰尘、变为白云,又如清光在雾霾中经过了考验、终见澄明。
这是阿炳在曲子中告诉人们的一种方法,这是人类在痛苦中拯救自己的一种方法。
对阿炳的去世,也有不同甚至矛盾的说法。有人说他贫困交加,不得治疗而病死,有人说他毒瘾发作,无法排遣而自尽。前者很有可能,后者也有可能。我只想问,这与艺术有何关联,与人类的命运有何关联?自古而今,病死的穷苦人还少吗,自行了断的艺术家还少吗?
关心肉身究竟是如何死去的,这还有多大的意义?(胡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