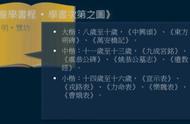男孩穿好衣服,下楼前读了欧拉夫的两首诗。
楼梯上迎接他的是詹斯的鼾声。这位邮差一直都睡在楼下的客房,他在村里待的时日不长,从不会超过两天,只够让马休息。不过如果有暴风雪,如果恶劣天气带着古老的恶意从海底升腾而起,他会停留得更久。男孩下楼后,咖啡的香气和鼾声混在了一起。早餐正等着他:面包配粥。科尔本嚼着面包,上面抹了厚厚的肉酱。你来救我脱离科尔本的无尽欢乐吧。海尔加说。男孩觉得非常自在,所以笑了起来,没有受到船长那阴沉表情的困扰。詹斯怎能在自己的鼾声中睡得着?他说。睡觉的一些人有福了。海尔加边说边听着煮咖啡的声音。之前的咖啡是专门给科尔本煮的,他早晨没喝咖啡时那般暴躁,大多数活着的人,甚至生活本身,在他面前都会退缩。
咖啡煮好了。
啊,这黑色饮料的芳香!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此清楚?自从我们喝上咖啡以来,有很久了,很多年了,那味道和愉悦仍挥之不去。我们躯体的最后一部分很久以前就已被吞噬,肉身腐烂离骨,你如果把我们从土里挖出来,只会发现嘲笑你的白色骨头。尽管如此,肉体之乐仍然紧随我们,我们无法摆脱它们,一如无法摆脱超越死亡的记忆。死亡,你的力量何在?
厨房里温暖舒适。科尔本闻着空气中的味道,一双大手捧着空杯子。你还要咖啡吗?海尔加问。老人点点头。你说了这一天的第一句话吗?我错过了吗?男孩问。但是科尔本没回答他。词语的成本很高,耗去了很多早晨的第一件事。海尔加说完打了个呵欠。他们夜里睡晚了,除了科尔本,他再熬不了夜,筋疲力尽,没用了。睡前他们坐在咖啡馆里,詹斯在盖尔普特的要求下,给他们讲了各地更多的新闻,直到喝酒耗尽了他的精力。坐在桌旁时,男孩才注意到船长脸颊上的划痕,很深的两道,不过在黑皮肤上不太显眼。他向海尔加投去探询的目光,食指从脸颊上滑过去,想让她注意科尔本脸上的伤。她耸了耸肩,显然什么都不知道。今晚有会吗?科尔本问。他指的是工匠协会的聚会,每月在咖啡馆举行一次。这是他早上的第一句话,普通得叫人难以置信,寻常的词语,却好像他设法让它们充满了敌意。是的,八点钟。海尔加回答。她坐在桌子末端,喝着那让血脉温暖、让她心情更好的咖啡。她叹了口气。如果有天堂,那里一定生长着咖啡豆。用不用我在划痕上涂点药膏,可能会感染的?海尔加说。你是怎么弄的啊?男孩没等科尔本答复就问道。他太年轻了,不懂策略。科尔本哼了一声,颤抖着站起来,像头脾气暴躁的公羊一样走出厨房,同时四下挥动手杖,敲向墙壁,有两次重重地砸到詹斯的房间旁边。詹斯惊醒了,鼾声骤然停止,头疼得钻心。他们听着科尔本上楼梯,拿手杖猛敲猛打,或许是希望叫醒盖尔普特。该死,他有时真有意思。男孩说。是的,但你不该那样问他,那些痕迹肯定不会来自什么好事。他们听到楼上传来门的巨响,科尔本到了他的领地,猛然关门,好让他们在楼下的厨房里都能听到。他现在谁都无法容忍,除了自己。男孩对着面前的粥喃喃自语。你确定他能容忍自己吗?海尔加轻声说。她抬起头,仿佛要让视线穿透科尔本的房间,穿透地板和墙壁。
老船长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摸着他的手杖,好像那是条忠诚的狗。他的房间和男孩的一样大,床旁有一个沉重的书柜,大约四百本书,一些很厚重,很多是丹麦语的,都来自科尔本还能看见、眼睛还有目标的时候。现在他躺在床上,眼睛没用了,可以被丢进大海,可以躺在海底,一片黑暗之处。船长叹息着。有时,如果你感觉糟透了,说说话是有好处的。咖啡煮好,只有他们两人时,海尔加说,我有善于倾听的耳朵。但科尔本只是嘟囔着他自己都难以了解的东西。许多人在生活让他们最痛苦时选择沉默,因为词语往往只是没有生命的石头或是撕得破烂的衣衫。它们也可以是杂草、有害的疾病传播媒介、腐烂的木头,上面连只蚂蚁都没有,更不用说人的生命了。然而,在一切似乎都背叛了我们的时候,词语是我们手边实际拥有的少数事物之一,记住这一点;此外还有没人理解的那一点——最不重要的、最不可能的词语,可以完全出人意料地承...
科尔本的眼睛闭上了,缓慢而确定。他睡着了。睡眠是仁慈的,也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