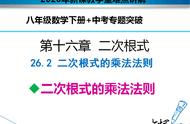文/ 石若萧
近日上映的《007:无暇赴死》是第六代007主演丹尼尔·克雷格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电影中,007昂首挺胸迎接了导弹的炮火。这既代表着戏内角色生命的终结,也昭示着戏外007这一IP即将要迎来新的变化。
丹尼尔·克雷格的离开没能激起太多讨论。观众们早在去年确定黑人女性接班007时就已经把该吵的架吵完了,如今只不过是坦然接受事实而已。从市场角度出发,影片在全球的表现都称不上多好。在国内,其上映前三天单日票房均未过亿,票务平台总预测票房不到5亿;而在海外,据IMDb统计,该片首周末进账5523万美元,不仅不及业内预期,在丹尼尔·克雷格系列中也只是倒数第二的水平。

《007:无暇赴死》
从1962年第一部007上映,这一IP迄今已经存续了将近60年。60年时间不算短,国际关系、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社会文化思潮都经历了好几个轮回。而在不断变化的浪涛中,007这艘小船依然在艰难地把握航向,以免自己漂向未知的地方。
乱七八糟的剧情
剧情方面其实没有太多好聊的地方。几十年来,007系列的叙事模式都是大同小异:主角或碰到阴谋,或被人暗算,接到上级指令或求助后开始上路,途中与各式各样的邦女郎纠缠一番,然后有惊无险地战胜反派,最终错失或抱得美人归。
几十年前这么操作,逻辑上是成立的。因为彼时还处于冷战时期,全球大小冲突不断,提供了绝好的社会背景,即使反派并非某个具体的国家,但不用挑明观众也能理解其指代的意涵——以第一部《007:诺博士》为例,反派设定是中德混血,信仰混合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俨然是美国两个最大恐惧对象的拟人化身。

《007之诺博士》
后来的系列反派也大差不差,大毒枭、能源危机、核技术走私、有意挑拨两个核武大国开战的疯子……总之每一部都能叩击到观众内心的某个恐惧点上。
但随着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电影逐渐脱离了原著加持,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也变得和平稳定。007想要继续下去,就不得不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反派是哪里来的?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分别是什么?
“9·11事件”发生后,“恐怖分子”就成了个万能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来自中东穷国的恐怖分子们毕竟没那么神通广大,制造区域性混乱可以,太高精尖的事做不来,于是主创们只好把这个概念又给变了变。
以系列片中的著名反派组织“幽灵党”为例,根据网络定义,其共有21位核心骨干,成员包括盖世太保、克格勃间谍、秘密警察、意大利黑手党、特工等……目标是致力于从世界霸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中牟取暴利,往往采用反情报、洗脑、谋*、用大规模*伤性武器敲诈勒索等手段。但是,幽灵党也会采用渗透的方式进而逐渐主导全球,因而和全球很多恐怖组织(如量子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高官有合作。
简而言之,就是以“恐怖分子”的粗糙概念为外壳,再拿一大堆历史中臭名昭著的形象填充之,完了再设计出一堆耸人听闻的动机来。但仅仅这样显然还是不够,因为世界毕竟还是没那么混乱,观众潜意识中不接受。
于是近年来的几部作品,都在反派的动机中混进了不少私仇成分,好让剧情显得更加可信。《大破天幕*机》中的哈维尔·巴登饰演的席尔瓦是M16的弃子,决心对体制进行报复;《幽灵党》中的布洛菲尔德和邦德是兄弟关系;《无暇赴死》中的萨芬则和邦德带点儿情敌关系……但这些心理疾病式的理由却反而使得人物观感更为混乱。

《007:大破天幕*机》
反派立不住,也影响到了007本人的塑造上——他的信仰究竟是什么?为何而战?众所周知,邦德没有个性,没有爱好,没有家人和朋友,没有过去和未来,这种为了国家利益甘愿摈弃一切个人追求的性格人设,在冷战时期还可以用“意识形态战士”来说通,但如今又是靠什么来支撑起邦德孤狼一般的状态和气质呢?
说来说去,怎么也说不通。于是近几年的影片又混合进了不少严肃探讨,比如从心理学角度发掘邦德的隐秘内心,拷问大英帝国前途何在等。但编剧作出的所有这一切努力,观感上俨然是一个学生在一道不会做的数学题下面堆砌大片公式,却依然掩盖不了“这题我不会”的事实。
《攻壳机动队》导演押井守曾针对系列第23部影片《007:大破天幕*机》写过一篇颇为尖刻的评论:剧情可说是乱七八糟。之所以这种糟糕透顶的剧本能够拍成电影,是因为观众对007这系列作品已经有基础认知。如果没有任何基础就这样搞,只会被当成白痴。
纠结中改变着
电影的核心在于故事,当故事本身弱得不能再弱,就只能把别的次要因素尽可能做得漂亮些了。
比如说,风景、豪车、科技,当然还有肌肉和美女。用第五代007主演皮尔斯·布鲁斯南自己的话来总结,系列片吸引人的点无非就是“美艳的邦德女郎,是新奇的道具,是性,是英雄、浪漫和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