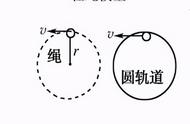出土于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墓的“文帝行玺”金印。/图虫创意
回过头来,马伯庸也把这种沉浸体验回馈在了作品中,从方言、衣食住行、社会习俗等方面呈现地域特色,无论是《食南之徒》中的岭南风味,还是《两京十五日》中的大运河沿岸风情,抑或《长安十二时辰》对于唐长安城里坊制度的刻画,背后都离不开作家对于各地风土人情的洞察。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我不是去写这一段才专门去走访,正好相反,是每到一个地方之后一定要把当地的东西研究透了,那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后,它会突然成为写作的灵感。”
长久以来,马伯庸出远门时都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到一处就在手机地图中查看附近的地名,然后探究它为什么叫这个地名、命名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契机。
六年前,马伯庸在广州路过一条叫作“寺贝通津”的狭长街道,他被这个奇特的地名所吸引,了解一番后才发现——津当然是码头,但这个寺还不是传统的寺庙,而是一个教堂,教堂背后有条小路通往珠江码头,所以叫寺贝通津。

寺贝通津路边上的教堂。/林泽君 摄
这个有故事的地名,目前还没找到机会写进书里,但马伯庸认为,这种好奇与追寻本身,就构成了人们对于城市的感情。
粗糙的澎湃,胜过严谨的平淡
同样不带有目的性的兴趣,还有读书。
马伯庸的阅读方式像打猎,他不爱被网络大数据“猜你喜欢”,更偏好去传统书店“捡漏”一些冷门好书。
他最近喜欢上看桂阳铁矿的档案合集,透过一份份档案看到整个湖南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金属冶炼发展史对于当地官制、军队建设甚至文化审美的影响,这种以小见大的角度尤其让马伯庸着迷,而这正是他口中“随机的乐趣”的意义所在——未来也许会用到,但是不以写书为目的去查这些资料。
这种无心插柳的积累也迎来了厚积薄发。写《长安的荔枝》时,由于对唐代历史地理、衣食住行乃至官制方面的知识储备已经非常纯熟,马伯庸唯一需要花时间检索的是荔枝本身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特性,写作也难得地进入心流状态,“灵感喷薄的速度比打字还要快”,前后总共用了11天就写完了这本7万字的小说。

马伯庸近年来最酣畅淋漓的一次写作,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另一部一气呵成的连载是《太白金星有点烦》,这本以太白金星李长庚为主角展开的“神仙工作流水账”,创作于新书《大医》交稿后。完成严肃恢弘的长篇后再写一部轻松愉快的短篇,是马伯庸独特的调节心情和创作节奏的方式,类似运动后的拉伸。
前后一个多月,马伯庸洋洋洒洒写了10万字,疲惫一扫而空。完结后,他本想精修一下连载时略显粗糙的文本,又因为担心失去原本的风味而作罢。
作品出版、再版时,马伯庸也会对其进行修订,但往往只局限于错字、语病或者历史考据上的讹误,那些文学性的表达他尽量不去改动,“我一直认为这种粗糙的澎湃要好过严谨的平淡。当你把一本书写得四平八稳,没有任何破绽的时候,文字本身承载的情绪可能就消失掉了,所以我有时候宁可让它糙一点。”
马伯庸很珍视创作时激情澎湃的感觉,他的作品多为兴起而写,有些没能兴尽而终,就成了一个个“坑”。成名多年,江湖上还一直流传着他“陨石遁”的传说,加上至今仍在被全网催更的《扶苏奔鲁》,有不少读者开始为连载中的《食南之徒》捏一把汗。

他曾透露,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其实不是《风起陇西》,而是围绕南朝宋的一位将领创作的故事,但只写了开头就没再继续了。/《风起陇西》
但马伯庸表示这次自己一定会完结,“我的写作主要由兴趣驱动,之前会有很多坑放在那没有填,但现在我至少会保有一个职业作家的操守,最近开的作品肯定会把它写完的。”
写作的本质,是找朋友
很难说清楚马伯庸算哪里人,这个80后作家生于内蒙古赤峰,长在广西桂林,在上海和新西兰都读过书,成为全职作家之前,还在北京一家知名外企工作了长达十年。
2015年6月底,马伯庸发文宣布辞职,文中写道“我已经三十五岁了,也想尝试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不过,他至今依旧保持着朝九晚五的上班节奏,早上7点多送孩子上学后在工作室开始工作,下午5点后回家,他的上下班界限明显,晚上再有灵感也不碰电脑,在家尽量只读书、玩游戏、陪孩子。
全职写作近八年,许多读者见证了马伯庸在互联网上声量的提高。这期间,他写出了《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等备受好评的长篇,多部作品已完成或即将进行影视化改编,有人戏称内娱正在迎来“马伯庸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