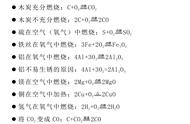引言:上世纪50年代,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仅凭《洛丽塔》一书,便奠定了其在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从小说《洛丽塔》出版至今,对于书中的内容,各路的批评声就从来不断,有人认为书中的故事有违人伦,违反了传统道德,一些文学评论家和出版社甚至因为《洛丽塔》中的一些情色描写,就直接把这本书划为了色情小说。
但尽管批评声种种,那些批评家们依然没有阻挡住《洛丽塔》的出版与发行,而且随之而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与那些传统的出版机构和老派文学评论家不同的是,大量的读者不仅没有针对《洛丽塔》中的情节与内容对纳博科夫咄咄相逼,反而对小说中的主人公(亨伯特),产生了恻隐之心。

亨伯特的饰演者杰瑞米·艾恩斯
那些批评家们口中十恶不赦的变态、恶魔、恋童癖,却被很多读者施以万般同情,这无不是一种有趣的现象,而这种评论方向两极分化的情况,也不由得想让人探究这背后的原因。下文笔者将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小说《洛丽塔》中的主人公亨伯特,之所以能博得读者同情的几点原因。
一、《洛丽塔》的叙事手法小说《洛丽塔》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这种视角更加适合情感的表达和抒发,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亨伯特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来回忆过去的。在书中,他采用的是“经验自我”的视角,以他今天的感觉来写过去,回忆的内容按过去的时间顺序来进行叙述。也就是说,即使是回忆,也仅仅是在写过去的事件,并没有连同过去的情感一起进行叙述。
回忆过去的事件,叙述现在的感受,这正是纳博科夫在小说《洛丽塔》中最具特点的叙事手法。因为如果按过去的真切感受来写,可能会有很多晦暗的地方,尤其是以亨伯特现在的罪犯身份来说。所以站在亨伯特的角度上来说,这种叙事手法实际上是他对客观往事进行修改的一种手段,他可以抹除掉那些不光彩的事件细节,甚至可以对往事进行美化,以便博得陪审团成员们的同情。

故事之外,单从小说的文学技巧上来说,纳博科夫的这种叙事手法无疑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悲情、执拗,又充满浪漫诗人气质的小说人物(亨伯特)。而且纳傅科夫成功地保持了微妙的叙事平衡,在这种反反复复地回忆过去,并用今天的情感去表达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令读者感到突兀的地方。
第一人称视角给了读者很强的代入感和沉浸感,而小说中亨伯特的口吻有时则更会像是你的一位老朋友,当读者的这种情感定位后,便很难再那么刻意地去思考和审视亨伯特客观层面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代表对于罪恶的崇尚,我们要知道,亨伯特的心理和处境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一种隐喻和象征。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情感方面都有很强的张力,其所讲述的故事也都带有一种浓郁的悲伤色彩,但两者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在对往事的叙述中,《情人》有很多对于曾经时候的心境描写,而《洛丽塔》则不然,它更像是亨伯特此时此刻对于过去的种种臆想。我们甚至可以把亨伯特的这些感受理解为,深陷情感漩涡而无法自拔的一种表现,一切看似悲伤,却又那么的咎由自取。

如很多人对加缪《局外人》的评价一样,小说《洛丽塔》中的故事也饱受道德争议,但实际上,《洛丽塔》的侧重点根本就不在于道德或是情色。确切点说,纳博科夫用精湛的文笔,成功地将整部小说塑造成了一部审美价值极高的作品。同时,纳博科夫也将洛丽塔诗化,将亨伯特此前的悲痛经历诗化,书中的各种场景如童话故事一般,读者又何来憎恨?
纳博科夫对于故事的诗化,是使得亨伯特能够博得人们同情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诗化自然也是靠纳博科夫登峰造极的文笔来实现的。如小说《洛丽塔》的开头: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小说的开篇就如此惊艳,给人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在惊艳之后,当我们看完整部小说再来细细品味这句话时,又会有无限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