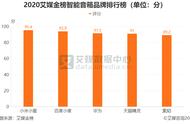佛教于汉朝传入中国,魏晋之后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信奉佛教的朝代国祚都很短暂,北魏、南梁直接因奉佛而乱亡。隋朝之时,因独狐皇后笃信佛教,百官尽皆影从。当皇后驾崩之时,著作郎王劭趁机献媚,对隋文帝说皇后是妙善菩萨的化身,她的驾崩时间正合符验,并非真死,文帝闻之大喜——谁知,隋朝最终也没有逃过短命的宿运。
到了唐朝初年,佛教依然盛行。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奏唐高祖,请求废除佛法,从而掀开了一场佛教论战。

唐高祖有意整治佛教
唐朝初年的一场佛教大论战傅奕通晓历数,曾预言过隋朝汉王杨谅的败亡;他精通天文,注解过《老子》,所以隋朝灭亡之后,被唐高祖任命为太史令。在请求革除佛教的奏疏中,傅奕将佛教称为“邪法”,斥佛经为“妖书”。认为佛法远在西域,与中国言语不通,所以那些不忠不孝之人就借助“汉译胡书”的做法宣传歪理学说;他们削发去须,假借出家来逃避赡养父母的责任;又假装云游修行,以此来逃避国家的征税与徭役。更可恨的是,佛教徒妖言惑众,设地狱轮回来恐吓愚民,动辄诅咒无神论者下地狱。最终使得人们皆“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藐视世俗法律,不服官府管教,造业作孽,被逮捕入狱了,还在牢笼中礼拜佛祖、口诵佛经,行为犹如禽兽,却在内心中自许清高,难以教化。更为严重的是,佛教徒“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对国政产生巨大的危害,所以唐朝应当重视佛教泛滥的问题。
接着,傅奕继续论述佛教对国运的危害,他说:“降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直到东汉初年,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导致佛法东侵,玷污中土风俗。西晋时,官府尚且严令华夏之人剃发易服,然而随着五胡入侵,佛教得以大行其道,后果是“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因此傅奕断言:“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
最后,傅奕请求扫清佞佛的社会风气,勒令僧尼还俗,这样可以使“四海免蚕食之缺,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对于这篇奏疏公布后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傅奕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像北齐仇子他那样因批判佛教而被朝廷*害,他也无怨无悔。
于是,唐高祖将奏疏付于百官讨论,结果只有张道源拥护傅奕的观点,群臣尽皆反对。中书令萧瑀恐吓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他并不打算在理论上驳倒傅奕,而是想利用权力来消灭异见者的肉身。于是傅奕也以牙还牙,说萧瑀信奉无君无父的浮屠之道,是“以匹夫而抗天子”,更该处斩。萧瑀无言以对,只得低头合掌诅咒对方,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尽管百官反对,但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唐高祖仍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在京城只留下三所寺庙、两所道观,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

唐太宗继位之后,对傅奕批判佛教的观点很感兴趣,曾问他:“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傅奕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认为在佛教盛行的西域,国家皆混乱羸弱,可见这种宗教对国政多有损害。唐太宗听后,颇以为然。但傅奕想要革除佛教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在临终之前对子女们说:“老、庄玄之一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可见傅奕是站在老庄周孔的立场来排斥佛教的,他所信奉的老庄也并非道教,而是古代的道家,因为他本人“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
谁知,在傅奕死后,老庄周孔之道并未在唐朝复兴,道教与佛教反而更加昌盛。武则天佞佛,唐玄宗好道,唐肃宗、唐代宗和唐德宗皆以山人李泌为师友。中唐以后,国家愈衰微,佛老愈盛行。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随着淮西藩镇被平定,大唐帝国出现了中兴的迹象。然而此时的宪宗日益沉迷于神仙方术,下令天下郡县寻访方士,谄媚之徒应声而起。宗正卿李道古向朝廷举荐了山人柳沁,宪宗命其在兴唐观烧炼不死药;接着,功德使也争相邀宠,上奏说:“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宪宗闻讯,立即下令中使率领僧众去迎候佛骨。
当时的官员皆唯唯诺诺,不敢出一言劝阻,眼看国家又将走向上弯路,此时的韩愈心事重重,正酝酿着一篇惊世之作。

韩愈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韩愈与傅奕所生活的时代大不相同:唐朝初年,虽然百官都是佛教徒,但皇帝并不沉迷于佛教——唐高祖与唐太宗都优先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不惜打击佛教。与之不同,唐宪宗沉迷于神仙方术,又是一名佛教徒,在这种情况下上表批判佛教,不仅会遭受百官的攻击,而且还得不到皇帝的袒护,甚至有*头的危险。然而,韩愈依然还是写出了惊世骇俗的《谏迎佛骨表》。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韩愈开宗明义,直取要害,大胆地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此法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从夷狄之国传进来的。在佛法未东传之前,中国的君主们都很长寿,百姓也安享太平。由此可知,尊奉佛法并不是求得君王长寿、天下太平的条件,所以是否要尊奉佛法,这是值得讨论的。
接着,韩愈又对比佛法传入以后的历史,发现自从中土皇帝信奉佛教之后,皆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梁武帝三度出家,废弃礼法,不食荤肉,以此来乞求佛祖保佑。结果他却遭遇侯景之乱,不得善终。于是,韩愈断言“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所以佛法是不值得尊奉的。
之后,韩愈追溯历史,说当年唐高祖神圣英武,能够力排众议,支持傅奕非佛的主张;只因群臣识见不远,百般阻挠,才使佛教继续肆虐于东土。宪宗继位之初,为了平定藩镇,也曾下令不准度人为僧尼、道士,禁止增设寺观,以此来补充劳动力。谁知藩镇刚刚平定,皇上又重开倒车,令人大失所望——陛下即使不能行高祖之志,也不应让佛教“恣之转令盛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上才刚刚下令群臣去凤翔迎接佛骨,陛下虽然没有昏聩到信佛的地方,但这种做法会鼓励百姓尊奉佛法,“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在朝廷的引导下,佛教又将盛行起来,恐怕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
最后,韩愈发表了近乎无神的议论,他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假如佛祖还活着,他也听不懂东土之人的祷告,何况是一具枯骨呢?来自天竺的佛祖“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跟我们东土之人不同俗,我们不需学他,也不用他来学我们,只要彼此尊重即可。他如果前来拜访,朝廷不过是赐给他一点礼物,命人将他礼送出境而已,如今何须陛下屈尊去迎接一具“枯朽之骨”?韩愈甚至说:“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且说:“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韩愈在写《谏迎佛骨表》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耻于“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谄媚政治风气,故而在文中多有激愤之辞,这令唐宪宗读后非常不舒服。第二天,皇帝便将《谏迎佛骨表》出示于众,表示要对韩愈加以极法。裴度等人急忙劝解说韩愈在文中谩骂的对象是佛法,而非皇上,他说的话虽然不好听,但也是为了皇上和社稷着想,罪不至死。宪宗则说就算韩愈批评我“奉佛太过”,我也能容忍他,但他却在文中说尊奉佛教的国家大多混乱,国君皆寿命不长,这种狂悖之辞已经涉嫌诅咒唐朝和皇帝本人了,实在罪无可赦。
与傅奕的处境相反,这次虽然皇帝没有站在反佛者一边,但“国戚诸贵”却都为韩愈求情,认为死刑太重了,最后宪宗才将韩愈贬到生存环境恶劣的潮州去当刺史,欲令其自死。
不料次年,唐宪宗就因误食丹药,暴躁易怒,隐于深宫,不与群臣相见,最终被宦官弑*了。

傅奕与韩愈的论点都基于孔子的“夷狄华夏”之论,想要捍卫华夏文明的纯粹性,给佛教贴上“夷狄”的标签,以便划清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界限。这说明,在六朝与隋唐之时,中国人尚未能够调和政教之间的矛盾,还不懂得如何利用宗教来服务于政治。
中国的政治家们对宗教干政的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始终站在世俗的一面来排斥宗教,避免神权凌驾于皇权的现象出现。宋文帝、魏太武帝、周武帝乃至唐高祖都意识到了宗教对政治、经济的消极作用,通过“限佛”、“灭佛”的做法来遏制神权的扩张,避免中国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傅奕与韩愈对宗教的批判属于政治层面,他们并未从理论上驳倒佛教,而是通过历史和政治来说明佛教的出世倾向与政治的世俗倾向不能相容,这是大部分信奉佛教的国家都没有好下场的原因。到了晚唐之时,随着佛教日益内在化、心性化,对政治的干扰才逐渐减弱。而到了宋朝,中国的思想家们才真正在理论层面对佛教进行辩驳,并将其部分思想吸收到宋明理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