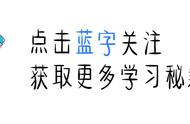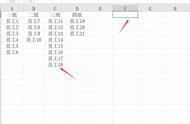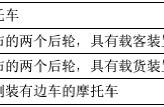文|许志杰
吃水饺,这是一件很隆重的事。
大人各司其职,放下吃饭的桌子,围坐在一起,和面、调馅、擀皮。
在欢声笑语中,一家人期待的饺子包好了,良辰吉时一到就可以添水烧火下饺子了。
山东人的餐桌上不能没有大蒜,吃饺子更是无蒜不欢。
大人包饺子,剥蒜就是小孩子的活。

小时候我干得不少。
平时不到饭点基本不在家待着,满街地疯癫,在听见母亲喊着名字叫吃饭时才回来。
家里包水饺就不敢出去了,一直在家候着,生怕晚了饭点误了吃饺子。
其实我挺烦剥蒜,尤其到了冬天大蒜皮干透之后,与蒜瓣紧贴在一起,一点一丝往下抠,指甲下的嫩肉被辣得钻心疼。
熟能生巧,后来知道剥蒜前用水泡一下或者用蒜槌子将蒜瓣敲破,剥蒜这活也就易如反掌了。
我们家喜欢蒜泥加醋,因为醋的酸和蒜的辣,无论跟何种菜品做的饺子馅都不犯冲,保持各自的原汁原味。
热气腾腾的饺子,蘸着辣味十足的蒜泥,加上一颗吃饺子激动的心,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
这是只有山东人吃饺子才有的样子。

可能很多人对于大蒜并无清晰的概念。
首先,大蒜并非“古已有之”,它的原产地在古西域甚至更往西一带,也有可能最早是从南美洲传入中亚,此后步步东进。
最早进入华夏地界,传说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慢慢由西往东生长开来。
一本《东观汉记》的书中记有:“李恂,为兖州刺史,所种小麦、胡蒜,悉付从事,无所留。”
过去人们称西域一带的人为胡人,他们带来的物种也就姓“胡”了,如胡萝卜、胡椒,不一而足。
就此断定,大蒜进入山东当在后汉时期。
这位李刺史曾在张掖、武威做太守,把胡蒜带到齐鲁大地茁壮成长,养育了一方山东大汉,可谓功劳卓著。
是不是中原以左山东人最早吃大蒜不可测知,至少山东人保留了两千年喜食大蒜的饮食习性,而且成为中国种植大蒜的主产区。
其次,大蒜是北方越冬农作物生长时间最长之一种,几乎与冬小麦共时。
惊蛰节气不久,我到菜市场见着新鲜大蒜。
听有人问这是咱当地的吗?
商贩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是的。
这样的回答并非诈言,在蔬菜实现大棚种植之后,季节被搅乱,时令跟着感觉走,不要说惊蛰吃鲜蒜,即使冬至食用新鲜大蒜亦非妄言。
但是,大蒜是有自己一条清晰的来路与成长历程的。

秋冬之交为大蒜下种的最佳季节,把留好的种蒜小心翼翼分成单瓣,根系朝下,掐好前后左右间距,在耕耘平整、干湿恰当的地上,将其轻轻摁到土里。
这颗下地的蒜瓣就是来年大蒜之父,肥美的土地就是大蒜之母。
待到大蒜冒芽并缓慢长高,浇上头遍水,冬雪来临之前在蒜地盖上一层御寒的庄稼秸秆,像高粱、玉米、小麦的秸秆都行,之后再漫灌一遍水,就可安全过冬了。
这层庄稼秆如同现在的塑料薄膜大棚,起到保暖、保湿、促长的作用。
翌年开春,万物复苏,大蒜新芽萌动,此时把覆盖的庄稼秸秆清除出地,给即将拔高生长的蒜苗,亮出宽敞通风的利好空间。
浇水,施肥,精心护理,两个多月后的春夏交际,蒜薹脱颖而出。
这是大蒜赠予人们的第一口美味,也是对精心呵护大蒜一个冬天安然无恙的主人的真挚谢礼。
在我老家采收蒜薹叫做“蒂”蒜薹,应是“拔”的意思。
是不是这个“蒂”拿不准,音是这样发的,有“瓜熟蒂落”之意。
“蒂”过蒜薹,就是大蒜最后个把月的快速生长期,日期夜盼,种蒜人等待着丰收的喜悦。

大蒜浑身是宝,成长中的每个时期皆可入食。
青春年少时的蒜苗,蘸着黄豆大酱或用大饼卷着吃,一股的青春气息。
五花猪肉爆炒蒜苗,也是一盘佳肴,伴之米饭,狼吞虎咽。
中年盛期的蒜薹吃法更多,洗净了生吃,稍带一点辣头,清脆爽口。
次之是用开水一焯,加盐以及轻点豆花酱油和米醋,拌过一刻钟入味即食,还可以存放三两天,味鲜不打折。
当然做法最多的还是炒蒜薹之类,肉炒、鸡蛋炒,各种小海鲜炒,五花八门,样样好吃。
记忆深处,鸡蛋熬蒜薹是我一直追寻着的味道。
那是麦收的季节,天干燥热,烈日炎炎之下的劳作,争分夺秒,抢收抢种,不敢丝毫懈怠,中午饭常是各家做好了送到田间地头。
正是蒜薹上好时,新鲜的鸡蛋、嫩翠的蒜薹,铁锅一熬,美味到无与伦比。
接着收麦,一点不累。
这是每年到季必做几次的一道美味。
春末夏初鲜蒜上市,“一口鲜”将大蒜的正常生长期“咬”断了,为经济效益算计,也属聪明一招。
我爱这口,尽管最初鲜蒜的价格一度达到极值,却丰富了大蒜的花样年华,拉长了鲜蒜食用周期。
与鲜蒜对味的是小米面窝头,香气鲜美,每饭必吃。
肥而不腻的熟猪头肉与大蒜同样很投脾气,隔三岔五解解馋。

蒜生四季,历经秋冬春夏,摄取四季之精华,涵养天地之气神,具备人体康健必需的营养成分,尤以消毒抗菌壮骨为最。
根据地域气候不同,大蒜的收获季从西往东延伸,大概与小麦收割的时间差不离。
有地方是收了小麦再收大蒜,有的则反之。
我老家昌潍一带就是先收小麦再“拔蒜”,从而留下麦收季节吃鸡蛋熬蒜苔的幸福回忆。
趁大蒜刚出土,腌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各家口味不一,腌蒜所用材料不尽相同,有的盐配醋、酱油,有的是配糖,吃涮羊肉火锅的糖蒜即是。
山东人喜食大蒜,受益于大蒜。
走遍天下,只有山东人的饭桌上摆着大蒜。
小孩闹肚子,吃几颗烧熟的蒜瓣,保准管用。
无论身在何地,只要听到“服务员,有大蒜瓣吗”,那必定是山东人在呼唤。
看过一篇文章,说山东人和上海人一样爱吃海边的毛蚶,山东人叫毛嘎啦(蛤蜊)。
上海却有一年突然因食毛蚶而爆发甲肝,查明原因,山东人不生食毛嘎啦,即便吃也是就着大蒜下咽。
前些年出国必带两样,一是五香花生米,再是大蒜头。
无论饭食合不合口味,有这两样在,走遍天下都是家的味道。
随着时代之变大蒜吃法翻新,迎合现代理念的黑蒜、大蒜营养素,甚至有了无味的大蒜。
和善的山东人不会拒绝。
但我说,任凭翻天覆地,山东人大口吃蒜的习惯不会改变。
大蒜那股特有的味道,就是山东人特有的气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