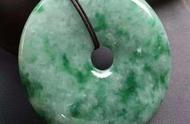昨天早晨我锻炼回来路过体育场门前,看见一个摊贩站在一辆小皮卡车前吆喝卖甜柿子,只见皮卡车厢内装满了黄中带红的柿子,柿子呈四角形,有成人掌心大小。我知道妻子爱吃这种甜柿子,就问摊贩多少钱一斤?摊贩说:“三块钱一斤。”我当时要去单位上班,不方便携带,就没买。今天早晨我又路过体育场,这个摊贩仍旧在卖柿子,我上前买了四斤。在闲谈中我知道摊贩是咸阳人,他们那里柿子树很多,大多数都是以前的老品种柿子,采摘后要么自然放软,要么用温水温几天,才能吃,否则吃起来涩口。这些直接能吃的甜柿子都是改良后的品种,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被农民大量种植,它的优点是直接采摘下来就能吃,缺点是硬柿子,牙口不好的老人、儿童不能吃。我猜测这些柿子应该是咸阳山区种植的,摊贩笑着肯定了。我们首次接触甜柿子是去年中秋节在四姑家,她的一名朋友种植甜柿子送给她们一些。我临走时她给我们装了一点,我们一直将柿子带回洛川,我和儿子不喜食柿子,因此柿子多半被妻子吃了。


对于柿子,我并不陌生,小时候我们村的耕地多位于丘陵地带,田间地头都栽种着柿子树,柿子树生长得慢,有些粗大的树都是我们老爷、爷爷辈栽种的,因此对这些树的树龄连父亲也说不清。并且柿子品种很多:有成熟后晶莹剔透的火晶柿子,有成熟后没有一点涩味的蛇留黄柿子,还有结得密密实实、枣子大小的皱柿,在泉水旁还有邻村的一片柿子树,这里土壤湿润,柿子结得个头大,有四角柿、蒸馍柿,只是这两种柿子有点缺点,就是里面有核,多得有三四个,我们在成熟时一般不吃这种柿子。我们小学离泉水不远,我们上学时不带水瓶,渴了的时候就到泉边舀水喝,舀水的工具就是柿子叶,有些馋嘴的同学,还把枣子大小青涩的柿子摘回家,泡在清水中,几天就能吃;每当柿子成熟时节母亲总是挑拣柿子最稠密的一个小枝折下来,挂在房间的芦苇顶棚上,让其自然成熟。过一段时间,各种品种的柿子成熟变软、变红,十分诱人,成为我们当时免费的水果。晚上摘几个柿子,在热水中温一下,剥掉外皮,咬一口甜津津的汁液溢满口中,非常美味。当然这些柿子也是我们招待客人的佳品,父亲的朋友尝过后赞不绝口;秋天下一场雨后,在阳光的照射下,柿子自然变软的更快了,只有软柿子才能吃,这时田野中大大小小的柿子树也成了我们农村孩子的乐园,周日一伙孩子在野外撒欢:摘柿子、烧红薯、烤玉米......记得有一次我和堂哥摘了一些软柿子到孟塬火车站卖,还买了几块钱。还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独自摘了一篮子柿子,吃力地挎着准备到车站卖,在穿越火车道时被一名火车司机拦住。他问我愿不愿意拿这篮柿子换一篮煤(麦)。由于司机是外地人,将煤发音成麦,我当即就点头同意了。当他从篮中取完柿子准备给我装煤时,我才知道搞错了。但从小大人就教育我们要守信用,再加上我这个人脸皮薄,我就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当我将一篮子沉重的煤挎到四五里之外的家中时,细嫩的双臂已经磨得通红,并且有点肿;我们村口有一个小沟,沟中种满柿子树,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这些柿子树也分到每家每户。当时采取抓的办法分柿子树,父亲抓得阄,为我们家抓到三棵小柿子树,当然每年摘得柿子就不多。



我们将成熟的柿子进行挑拣,摔坏的、破损的用来酿醋;好得用刀子去掉表皮,晒在席上,晒干了装入一个坛子中,等到下霜后,表面就是一层雪白,也就做成了柿饼。现在富平柿饼非常有名,尽管价格昂贵,但已成为馈赠亲友的佳品。一年春节亲戚带来一盒富平柿饼,我尝了一个,发现它尽管绵软,但似乎是在柿子还没成熟的季节就采摘了,因此没有我们以前成熟柿子做成的柿饼筋道、口感好,特别是这种柿饼不耐放,只要暴露在空气中过段时间就坏了,不像我们家中的柿饼放一两年也没事;当然还要挑拣一些没有疤痕的柿子,小心摆放在稻草席上,上面也盖上厚稻草。冬天夜晚想吃时,可以捡几个软柿子用水温或用炉子烤着吃。我们当地还有一种普遍的吃法,做成柿子饼:挑拣软柿子,剥掉皮,将柿子浆放入盆中,放入少许玉米面(小麦粉烙下的饼子不软)搅拌均匀,用手捏成手掌厚的饼子放入锅中烙,烙成的柿子饼软甜可口,老幼皆宜,也是我们招待客人的一道美食;城市人更精明,他们用不多的柿子浆,搅些白糖、面粉,做成拳头大的饼子放在油锅中炸,进行现炸现卖,一元钱只能买五个小饼子,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西安上学时亲眼见到的,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也不到两元钱。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中二三十年都过去了,随着田地分到各家各户手中,柿子每年的收购价格不高,加上村民嫌地头的柿子树影响耕作和庄稼采光,就乱砍乱伐柿子树,现在我们村的柿子树几乎绝迹,连沟中的柿树也由于修建高速公路,邻村大量卖土方,已经将沟一边挖成平地,也伤了不少柿子树。二舅的村中靠近秦岭,还有不少柿子树,但由于经济价值不高,柿子成熟了也无人采摘,任其落下腐烂,让人感到可惜。现在孩子的娱乐方式多样,早已不下沟玩耍,想吃柿子可以到水果店购买,因此下沟的小路已被荒草淹没,柿子成熟时节也就是村中几名六七十岁的老人摘一点。每当想到这里,我都不由得感叹时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