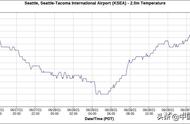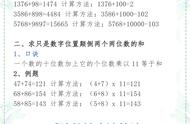民国时期北京哈德门外街景。
国都通常是对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称呼,也是政治文化中心所在。溢美的表达为首善之区。历史上的习惯称呼是都城、国都。1927年4月 18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中国历史悠久,留下西安、洛阳、北京等多个王朝的故都,国民政府便将南京称为首善之都。这样,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就有了“首都”的称呼。
首都选址问题,民国时期有过1912年、1927—1928年、1935年、1941—1943年、1946—1947年五次争论。在新发现的中央设计局专家秘密论证的密档中,北京、南京、西安、武汉四个备选建都城市清晰浮现,建都选址内幕揭开。
孙中山主张:南京
辛亥革命之后,“建都议起,南北殊言”。针对孙中山等主张建都金陵(南京)的主张,章太炎在1912年初致信南京参议会,列述金陵建都的五害。他明确主张建都北京,若迁都金陵,广大的北方失去了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和统治力,政府“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是一害。文化的影响力不及,“是将北民化为蒙古”,是二害。若袁氏被迫南迁,日俄会乘机侵及东北,中原失重,国体将土崩瓦解,是三害。政府南来,蒙古诸王相拥戴,使南北分裂,是四害。若政府和使馆南迁,耗资极大,民穷财尽,是五害。因此,章太炎提出,“谋国是者,当规度利病,顾瞻全势,慎以言之,而不可以意气争也”。更不能“忘国家久安之计,而循朋友利禄之情”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38-439页)。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迁都南京后,蒙古分裂、日军侵占东北等问题,都被章太炎说中了。
毕业于南京高师的商务印书馆地理教科书编辑张其昀,1927年5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中国国都之问题》,为学术界第一次给南京建都所作的论证。他认为北京官吏腐败,积重难返,人文与物力都不及南京,加上风沙肆虐的环境,和缺乏海道的不利因素,不宜为首都。南京高山、深水、平原并有,有国际交通的便利,人文优势巨大,最适宜建都。1928年,张其昀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随后20年间,他撰文十篇,坚持为南京建都鼓吹。
1928年间所发生的建都问题论争,起因于1928年6月吴稚晖在上海市党部第七次“总理纪念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披露了国民党南北军事集团之间关于在南京、北京建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他说在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主力与以冯玉祥为首的东征主力在徐州会师时,冯玉祥首先向蒋介石、吴稚晖等人提出了国民政府应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意见。
由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在南京定都,到了1928年6月全国统一之时,南北军事集团在建都选址问题上展开了争执。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军事集团的势力和利益在江浙,此时又依靠江浙财阀的经济支持。所以这时候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站出来讲话:“南京建为首都是总理理想的主张,总理还要将遗体葬在南京。……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而北方舆论界在阎锡山、冯玉祥等军事集团的支持下,则有坚持建都北京的主张。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白眉初(月恒)教授,在1928年7月《国闻周报》刊出《国都问题》。他以史为鉴,提出建都北京国运长久,建都南京国运短暂的历史问题。于是,在1928年7—8月间,双方以《大公报》系的《国闻周报》为阵地,开始了建都问题的争论。
白眉初的《国都问题》分四部分:历史之观察、地势之评判、外侮之应付、现状之宏隘。他首先列举出中国五个古都的建都时间:长安887年、洛阳822年、北京857年、南京443年、开封163年,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南京十代国都,其特点所在,非偏安,即年促。”其中吴53年、东晋103年、宋60年、齐23年、梁53年、陈31年、杨吴16年、南唐39年、明太祖和惠帝两朝53年后迁都、太平天国12年。具体说来:“平均之,每代不过四十五年。”“除朱明以外,皆为偏安,而无一能成统一之局者。”
白眉初倾向于北京建都。他说:“今世强国之都城,皆萃于北纬四十度南北。”这八大都城所占纬度如下:华盛顿北纬38度32分、伦敦北纬51度25分、柏林北纬52度34分、巴黎北纬48度53分、罗马北纬41度55分、莫斯科北纬55度50分、东京北纬35度46分、北京北纬40度。白眉初强调:“一种气候之下,其民族之体力精神,随之变异。”北京居于国疆之上游,“表雄视八方之气概”。他说:“今环拥北京之民族,西则秦陇,南则燕赵,东北则满蒙,东南则徐淮。此等民族,受气候之影响,而北京据乎其中,诚具雄武之气象也。”南京,“就其附近狭小之形势言之也。苟合大江南北百里内外观之,则一平原四战之区耳。非若北京之有大长城,大山脉,大沙漠。重重叠叠,千里环抱之雄图也”。
白眉初指出南京物产丰富,人民生计容易,行则乘舟而体质柔弱,不能与燕赵徐淮之尚武民族比较。在这种文化地理环境下,“南京十代建都,多偏安而年促者,一因北方地势占胜,民族强健,或被迫而南迁,或欲北伐而不得势。此其所以偏安也。二因恃长江以为天险,不修政治,甚且化于文弱,溺于荒淫,而不克自拔,而北方来侵,遂以亡国。前者为受地势之害,后者为食文弱之赐”。最后,白眉初强调:“假令总理生至今日,亦当幡然改计,以建都北京为宜也。”
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叶景莘支持白眉初的观点,他说:“近来建都南京的主张似乎并不是从地理天时上立论,而多是从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说话。”他对吴稚晖讲话中所谓北京的建筑是封建式的,不适合现代的要求提出质疑。他最后的结论是:“就全国的形势与国家的大计说,首都应在北京,固无疑义;即就国民政府说,亦未尝不可建都于北京。”
白眉初所说历史上南京十代国都“非偏安,即年促”的结论,大大地刺痛了国民党政府。这等于是在为一个政权敲警钟或丧钟,听起来很不吉利。随之而来的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官方言论,是具有权力话语霸权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打压。著名报人龚德柏的文章《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不讲学理,多谈政治需要,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一剑封喉,不容讨论。龚德柏说:“白君对于近代国都之议毫无了解。故以十八世纪以前之国都论,而欲适用于现代,根本上已属错误。”强调:“盖南京建都已系既定之局势,决不为书生一两篇文字所左右也。”他针对白眉初所说的“列强之侵略”和“使馆保卫界之纠葛”一事,诋毁白眉初,说白的两段言论“与日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辙”,“若为中国人(观此白君为中国人否尚属疑问)而竟能发此丧心病狂之怪论,不能不使吾人疑为外人作说客,为帝国主义者当走狗”。龚德柏最后的结论更是武断,他说“白君大著,曲学推崇北京,不惜牺牲一切”,是“荒谬绝论之议论”,“图欺世人”,“贻误国家”。
由于这种代表政府权力的话语的出现,学者不再作“国都问题”的学术谈论,南京也就自然成了国民政府的首都。

胡焕庸《战后我国国都问题》。
贺昌群主张:北京
1941年下半年,钱穆在致张其昀的信中谈到,他自己虽久抱国都必须迁北方的私见,但不敢轻易发议,特请教张其昀,孙中山是否主张首都必须设在南京?
张其昀认为建都南京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古时南京建都,内以长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今日之南京,以舟山群岛为第一道防线,杭州湾为第二道防线。古时防御之目标,为南下之铁骑,今之目标则为东来之战舰”。张其昀在这里是讨好最高当局,为他们制造了一种虚幻的假象。
秦一统中国后,自汉朝始,中国的外患,一直来自北方。到了明代,才开始有来自海上的东南之患,如倭寇*扰东南和荷兰人入侵台湾。自鸦片入侵而引发的战争始,东南海上门户洞开。从军事上看,如果没有强大的海上自卫能力,首都不宜设在东南沿海。
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贺昌群的《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第42期,1947年2月1日),针对张其昀的观点,提出建都要以中华民国的利益为重,不要把孙中山遗愿、中山陵与建都的关系并为一谈。孙中山的建都南京计划,如果条件不够,任何人也不能以此为借口,造成一条金科玉律的宪法。中国没有海军,也就无海防实力和国防保障。中国的国防第一线至今仍是在大陆。日军很快侵占南京的事实说明,海防及军事的无力,也就无法保障首都的安全并发挥政治、经济作用。建都长安的朝代是西北塞外民族强盛的时代。在北平建都,从地理上说,是依靠河北的重要地理位置,与东北、山东半岛、渤海湾、北方边事、大西北等多有关联。同时,中国历史上是北强南弱,战争是北方征服南方,文化是南方征服北方。坐守北平可顾及东北、西北。而没有强大海防即无防御的南京,设为首都只能是暂时的需要。贺昌群一针见血地挑明:“帝国主义在长江及沿海口岸的势力,是以兵舰为后盾的经济侵略,中国的国家财政不能不与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相勾结,所以政府迁都南京,无宁说全因国家财政的关系,绝不能以国防为理由。”
事实上,南京有一种历史的宿命,即短命之首都。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言,孙中山在这里不足两月即让位给袁世凯,大总统没有了,首都完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因日寇要屠城,弃首都跑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三年多,蒋介石还戴上行宪总统的帽子,很快又被赶到台湾。
钱穆主张:西安
钱穆研究秦汉史,也是秦汉文化精神的推崇者。他主张战后新首都建在西北长安,并以北平为陪都。在《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第17期,1942年12月1日)一文中,钱穆明确提出:长安北平一线,略相对黄河平原之地带,即代表前期中国汉唐精神的地带,应使长安为新中国首都。“全国青年受国家政治教育宗教哲学各部门精神方面的训练培养者,以集中此地带为相宜。壮阔的地形,严肃的天象,深沉古老的历史文化之真迹,全在此地带上。这一地带表示着中国民族之坚毅强韧笃厚伟大。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宗教师、大军人,全应在此地带受洗礼。自此以北,益高益冷益旷益大的边疆区,应成为新中国之兵库。万里长城即其最好的象征。新中国人应在此带建设活的万里长城。”
钱穆反对首都偏建在东南江海丘陵小局面之下。说偏建在东南会使中国文化,特别是现代中国的中央地带和亚洲大陆冲荡斗争的大局面闭幕。东南江海丘陵小局面之下的人物,无驾驭大局的能力,也无力回旋北方的大势。
贺昌群主要的考虑是防御侵略,即国防。钱穆具有强烈的儒学复兴理想,他把首都看成是“播撒精神种籽的一块良田”。张其昀因有政治教条和对现政权的依附,主要的考虑在于行政的方便。
胡焕庸主张:武汉
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在1941-1943年间,从实际可操作层面,为战后首都选址、还都或迁都时间步骤等,进行了具体秘密设计。一份1943年6、7月的《中央设计局拟定战后复员计划纲要》机密档案显示,有来自学界、政界、军方的多份意见和总结报告,并用统一的纸张书写后呈报。其中气象学专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关于战后国都及陪都问题之意见》一文,列举出北平、南京、西安、武汉四地选址优劣,指明以天时言,北平最为相宜;以国防地理论,则西安应为首选;以人口物产立论,则南京、武汉有胜于北平与西安。从历史与现实国际大环境看,主张战后首都必须以北平为首都,重庆、西安为陪都。竺可桢的意见基本上是发挥了以往章太炎、白眉初、叶景莘、贺昌群的观点,做出以北平为首都的结论。
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委员丁锦的《建都地点之商榷及实施之步骤》,主张战后首都设在西安,并列举出建都地点所必备之八项条件,他同时也提出了分批北迁,三批完成的具体步骤。
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6月,在《地理学报》二卷二期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提出了“瑷珲—腾冲”这一大致为倾斜45度的直线——线东南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自古以农耕为经济生活方式;线西北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战时他参与中央设计局拟定战后复员计划纲要工作,在《战后我国国都问题》的意见书中,他明确主张首都设在武汉,理由是武汉为地域、交通、人文与财富中心;同时增设陪都三个,即兰州定为西京,沈阳定为东京,广州定为南京。
包凯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讯发布组少将组长兼中央设计局委员,在《提请另建新都议》一文中,他主张建新都武汉。
相对于以往二十多年关于在哪里建都的讨论,中央设计局的这个复员计划纲要更为具体,武汉是过去北京、南京、西安三个选项之外,新出现的城市。
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国际公法专家黄正铭在《建都刍议》的意见书中,以国防、交通、粮食、人口、气候、民俗六大条件为选址标准,主张以北平为首都。同时提出,先在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一年,然后再行奠都北平。
法学家钱乃信在提交的《主张战后仍以南京为首都意见》中,以务实的理由称,南京已经具备为首都的有利条件,在南京之外新建首都,国力所不许;抗战以来规复南京之冀念,意见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抗战胜利,正应回都南京,以维持利用此种力量。
中央设计局委员、“战后复员计划纲要”中“首都”设置项目召集者许孝炎在此项目的总结报告中,将南京、北京、武汉、西安四个备选方案加以总结说明,肯定它们各自所拥有的优势,也提醒西安、南京、北京历史上作为首都的得失,特别是现实政治地位,呈报给最高当局。他认同胡焕庸的主张:武汉。
结果,是钱乃信的意见务实,政治正确,且符合国民党人一贯坚守“总理遗愿”的教条,还都、奠都南京成为事实。
“非偏安,即年促”的王朝悲剧命运再次应验。1949年,历史大转折时,主张定都南京的吴稚晖、张其昀、龚德柏、钱乃信、黄正铭(主张先还都南京),主张定都西安的钱穆,主张定都武汉的许孝炎都随南京国民政府溃败,离开了大陆;共和国新政府1949年9月下旬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北京建都,奠定建国基业。主张定都北京的叶景莘、贺昌群、竺可桢到新政府首都北京就职。
只顾眼前政治正确的做法,往往是悲剧宿命的症结所在,这也是历史的通鉴!
沈卫威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