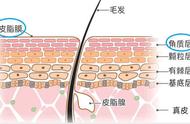岁月把我推向了中年。三十多年过去了,巧克力、奶油蛋糕抹不去童年玉米爆米花、糖稀的记忆,它们在流逝的岁月里发酵,里面藏着我儿时生活中的企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没有多少零食可以选择,幼年时的腊月,爆米花、糖稀无疑成为我不可缺少的美味零食。回忆曾经的爆米花蘸糖稀情结,一种幸福萦绕心头。

爆米花
糖稀亦称“饴糖”,为浅黄色黏稠透明液体,味道甜柔爽口,广泛用于糖果。绕糖稀很好玩,用两根小棍把糖稀稍稍拉长,一手抬高把长长的糖稀搭到另一根小棍上,再赶快绕下来,把随时有可能流下去的再绕在这根小棍上,就这样重复着,边绕边吃。一根根细丝如同金线那样光亮纤细,刚才还拉得长长的,没等放入嘴里,丝线便不情愿地断了,赶紧再拉,拉好了伸出舌尖迅速舔入口中。啊,真甜!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浸满了甜丝丝的糖稀。
记得进入腊月,吹糖人的特别多,多半都挑一个担子,一头是加热用的炉具,另一头是糖料和工具。一般都是自己属什么就要求吹制什么,制作时火候的控制是关键,过热则太稀易变形,冷了又会太硬无法塑形。吹糖人使用的工具很简单,多是勺和铲。糖人有人物、动物等各种造型。每次他们来村里都会围上很多人,尤其是孩子们。只卖糖稀的推劳动车,车上有一个罐罐,那里面就是最诱惑人的糖稀。可以用钱买还可以易货贸易,家里的旧衣服、帽子等旧东西统统可以换取糖稀。

儿时记忆
腊月里一听到小巷里“砰”地一声,我的魂儿便给勾了去,肯定是爆爆米花的大伯来了。赶紧回家让母亲盛上一碗玉米粒或是一茶杯大米,再加上一大把粉条,我便疯了一样地冲出家门去小巷里排队。爆爆米花的人都是些年龄大的大伯、爷爷,记忆的深处他们都穿着一件很厚的大衣。他们的肩上往往都是一条扁担,挑着一个细铁丝围成的近乎圆锥形的网,一个椭圆状密封的黑锅,一台铁皮制成的低矮小炉子和四方形风箱。只见爆爆米花的大爷烧上炭火,然后掀开厚重的爆炉盖子,把生玉米或大米倒进爆炉,把炉盖拧紧,一手拉动风箱,一手不紧不慢、有节奏地摇动着摇手,一圈圈转动锅子。一声声爆响令我心情怦动,我紧捂耳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斜着身子瞥着大爷用脚使劲儿地踩爆米锅,“砰”地一声,满锅的爆米花如天女散花,一下子都钻进了长长的网兜。爆米花的香气扑鼻而来,我真想一下子钻到网兜里吃个够。人很多,我从日暮时分排到满天星斗,满心的欢喜,这算是我们家改善生活的小食品。那瞬间变得臃肿的粉条更是我的最爱,拿起一根放在嘴里,酥酥的、脆脆的。

崩爆米花
要是赶上过年,爆米花和糖稀都有,爆米花蘸糖稀那种爽甜胜过当今的奶油。微不足道的糖稀如今很难看到、买到了,绕糖稀成了我美好童年的回忆,永远沉淀在心底。而今的奶油爆米花,总是勾不起我的食欲,相反使我更加怀念儿时的爆米花,怀念腊月乡村那种热闹的爆爆米花场景和纯朴的乡情,那记忆中旋转的爆米花锅,还有那苍老的爆米花大爷。那炉炭火温暖了寒冬,温暖了乡村,温暖了儿时的记忆。( 宫文平 自石家庄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