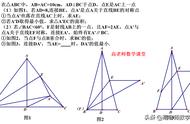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文|李斐然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标记外)
我就揍他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侠客,这句话差一点就成真了。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从小逃学,打过老师,打过恶霸,打过警察,上课熟读《江湖奇侠传》。12岁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湘西汉子黄永玉,这辈子要当侠客,浪迹天涯。
然而,人生在想当侠客那天下午拐了弯。妈妈突然宣布,家里孩子太多,他得离开这个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这是一个母亲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家族败落,父母失业,跟随父亲离家,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来投奔叔叔,中学打架退了学,他和家人失去联系,开始流浪。
现在的他是一个画家、作家、诗人、雕塑家、偶尔的菜谱创作者和长期的拳击爱好者。他平生最讨厌的一个词叫做「历史必然性」,被他称为「屁咧的历史必然性」。最好的证据就是他自己,以下两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历都属于黄永玉:
黄永玉,湖南凤凰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院院士,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三次获得意大利政府官方授勋,其中包括最高等级的大十字骑士勋章。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春潮》《阿诗玛》、水墨画作品《墨荷》《天问》、*纪念堂巨幅壁画《祖国大地》,还有很多无从归类的作品,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设计、电影《苦恋》的人物原型。
黄永玉,湘西流浪汉,爱好打架、逃学、偷吃爸爸做的鹌鹑脑壳,初中留级5次,因打人退学,烧过瓷器,做过棺材,在小学、中学、大学当过老师,抗战期间在战地服务团画过海报,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打猎、做烟斗,60多岁在动物园门口制服了三个抢劫的小伙子。80岁时说自己还是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比打官司解决问题好」。
出生于1924年的黄永玉是另一部中国百年史,教科书里不写的那种。他是中国最擅长打架的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最高学历小学毕业的教授,中文公开作品中出现「他妈的」「混蛋」「杂种」「小兔崽子」词频最高的艺术家。他说自己没有学历,所以不相信书本上的历史分期,他只认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新时代,一个是旧时代。让人平安快乐的日子叫做新时代,让人挨饿害怕的时候叫做旧时代,「毋论唐汉,毋论纪年」。
黄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国道理,相信因果,重视情义,讲究礼尚往来、知恩图报,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任何后天学的理念、主义都没有大于这种质朴的人生法则。他这辈子只在吃牛肉的时候喊过万岁,见最高领袖说的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待朋友赤诚,见长辈谦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学问的,搭救落难的,只有一种人他不来往,「害我是不行的」,这是闯江湖的底线问题,「我就揍他」。
再有两个月,黄永玉就要99岁了,该有老人模样了,可他没有。他的画室门口挂了一个拳击沙袋,写作的桌上依次摆着一支钢笔,一叠草稿纸,还有一把匕首。他每天早起画画,中午写作,下午见朋友,晚饭后窝进沙发里,抱着一只小猫,看电视上的拳击比赛。

《人物》在过去一年采访了这位老人,记录了一个人即将到来的99岁。这一年的最大感受是,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大于时代,大于命运,大于痛苦,大到足以让他扭转结局,把悲剧写成喜剧,把苦变成笑话。黄永玉做梦遇到鬼,从来都是他追着鬼跑,吓得鬼到处躲。他的梦想是有一天把鬼捉住,挠他痒痒,看看鬼会不会笑。这样的黄永玉没有同类,他是一个会画画的齐天大圣,一个偶尔参加组织生活的孙悟空。
认识之初,黄永玉给了我一张他自己印的名片。他听人说名片是身份的象征,头衔越大权力越大,他不服气。他的名片上没有电话,没有单位,没有官职,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
黄永玉
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
(港、澳、台 暂不通用)
其实他本可以有很多真的头衔,但他愿意出名,乐意挣钱,唯独不想当领导。他不会喝酒,讨厌开会,痛恨人打牌和麻将,开大会上台发言,他把「四个现代化」讲成了「三个现代化」。退休之后,晚辈想给他申请一项国家级荣誉身份,他当场回绝,并狠狠训了他。有人想给他搞一个「黄永玉画派」,他把人从国外千里迢迢叫回来,骂他没出息,「狼才需要结党」,而黄永玉认为自己是狮子,狮子干自己的事,一个人也能称王。
和这样的黄永玉聊天是一场绝对自由的愉快旅行。我们听不同版本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打赌一场拳击比赛里谁会赢,听着Beatles讨论《世说新语》,研究蜘蛛的活法。那段时间他在准备一幅新画,一只小小的黑蜘蛛捕住了一只折翼的蝴蝶,画名《价值的判断》。黄永玉动笔前除了要准备颜料和画纸,还要解答问题:蜘蛛那么小,却可以吃掉蝴蝶、捕住麻雀,战胜远大于自己的对手,它到底是怎么赢的?
画家的答案是时间,「蜘蛛不是靠进攻战胜对手的,打是打不过的,它有耐心,等。造一张密密的网,等待猎物落网,用网束缚它,用毒针刺它,等对手耗尽力气了再去降服。」这个结论让我们都笑了:原来蜘蛛还懂《孙子兵法》呢,知道强敌是不可战胜的,胜的唯一方法是躲起来活着,等敌人自行灭亡。
有时候,我们也讨论恐惧。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是苦会再来。他让我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是,历史不会重现,因为改变往往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发生;第二句是,一切都会过去,「你要记住,任何苦都会灭亡,只是这件事有个时间问题。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可以,你要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做好自己的事,活到那一天。这个过程你可能会遇到难处,遇到很多荒谬和可笑……你就把它当作一种观察,人还能这样呢?还能有这样的事呢?你要把它们当成笑话记住,等到将来写出来,讲给人们听,日子过去是这样的呢,多有意思!」
黄永玉不思考「为什么」,人为何作恶,恨从何而来,江湖人不琢磨这些,人心险恶,是非多变,这本就是江湖底色。黄永玉信奉的是一种打架的哲学:不必分析拳头为何挥过来,重点在于应对,见招拆招,把命活下来。在每个难关都想办法笑,把痛苦熬成笑话,这就是他的活法,一种笑的方法论。
小时候放学回家,他围观弟弟打架,局面一度激烈胶着,弟弟挨了不少拳脚。事实上,打架从来都是这样,挨一拳,回一脚,一边受伤,一边求胜。最后弟弟打到满脸伤,终于赢了,把对手死死压在地上,可他不知道为什么,赢了还在抡拳,一边打一边哭。讲到这里,黄永玉出场,故事终于变成了笑话——哥哥拉开难过的弟弟,小声传授给他胜者的规矩:「打赢的人不哭。」
这是黄永玉的笑话,或许,也是他的信念。黄永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笑到最后」的人,他的人生或许是一种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只要活下去,眼前经历的一切困顿、绝望、无可扭转的败局,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项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见黄永玉只要带着耳朵就行了,他准备了很多热闹等着你。第一次见面那天,他刚刚交上自己连载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最新一章,从书房扶着助步器走出来。黄永玉忙得很。客厅柜子上压着一幅颜料还没*新画,桌上的草稿纸有一首还在圈圈改改的新诗,沙发边的书摞成小山,最上面那本中间夹着纸巾做的书签,读了一半。他谈的每句话都有典故,像一堂眼花缭乱的历史课。看到墙上那幅小像吗?那是周令钊画的二十三岁的黄永玉,现在这幅画叫《小鲜肉》。今晚吃的这种葱是王世襄的做法,还有餐桌旁的那幅屈原的《九歌》,注意看落款:从文时年整八十岁。
黄永玉人生三大爱好依次是读书,打架,侃大山。过去腿脚还能跑的时候,他闲下来最爱骑个小摩托逛潘家园市场,往热闹人堆里扎。他喜欢买东西,可他不会讲价,整天兴高采烈地往家里搬一堆上当受骗的证据:虚高价的花瓶,缺一只眼睛的画眉鸟,名不副实的老字画。来子是他的年轻朋友,到家里看望他,进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坐他家里喝茶、看画、侃大山,每人手里一根他的雪茄。热热闹闹招待了一下午,把人送走了才知道,全是下午在官园买鸟认识的路人。
「你认识他们?」
「不认识。」
「那他们来干嘛?」
「好玩!」
后来摔倒受伤,聊天升级为一个老人最大的娱乐。高兴起来有时候说粤语,有时候说凤凰话,他还会说很流利的闽南语和从星期一数到星期天的英语,这都是流浪时学会的语言技能。其他的语种他只会一两个单词,比如日语会说鸡蛋(tamago),因为讲笑话的时候用得上,「他妈的」。
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笑话。齐白石招待客人的点心是放了多年的月饼,李可染练字把垫在下面的毯子都练出一个坑,*纪念堂一进门的壁画是他画的《祖国大地》,草稿是在废稿纸上画的。当时出了几个方案都不通过,最后找到黄永玉,黄永玉就随手捡了别人的稿纸,在背面画了大河山川,寓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喜欢讲述家乡的故事,湘西的水、湖、山,还有表叔沈从文。小时候在老家只见过一面,流浪的时候没有联系,他刻木刻,表叔在一本诗集里看到插画,找到了他。表叔总是不慌不忙,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笑的眼睛。新中国成立后,表叔写信劝他北上,他带着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搬来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一见面大家都笑了,那是北京的二月份,一对南方长大的年轻父母也对北方毫无概念,没给孩子穿袜子。他们后来笑话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湘西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