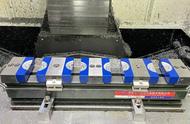那时我家住在村庄南岸子(渭北人的“岸子”这个词指的是方向,比如南边就叫南岸子),一溜子七八户人家,家家都是几间青瓦白墙的土屋。那屋顶上的瓦片,经历天长日久的岁月冲刷,都变成黑色的,瓦沟里还长着一棵棵瓦松;而原本用白土粉刷的雪白色的墙壁,被夏季的雨水冲刷得坑坑洼洼,露出泥土的本色,墙皮上清晰地露出一根根金黄的麦草节。

那时,家家都没有院墙,屋前就是一道荆刺篱笆围起的菜园。春日里,太阳的明黄一点一点地浓厚起来,菜园里的几丛青葱韭菜一天一寸地向上生长,争抢这第一缕的春光,其余的园地就敞开它赤裸的胸怀,懒洋洋地享受着阳光的翻晒。三月,村头的柳树生出绿绿的嫩芽,邻家园子里,一树桃花开出粉色的花朵。父母就把菜园子的篱笆修整好,然后翻整土地。一把磨得发亮的铁锨,用脚一踩,就深深扎进土地。刚刚翻上来的土壤,是深褐色的,经过太阳暴晒,渐渐发黄。散发出一种泥土的清香味道。
翻过的土地,还要用耙子耙平,再用一道道土垄把菜地分隔成几块。然后点瓜种豆。通常最大的那一垄,种的都是辣椒。母亲拿来半碗金黄的辣椒种子,拌上草木灰撒在锄头勾出的一行行沟中,再用铁锨抹平。
地畔上种的大都是菠菜,葫芦,南瓜,西红柿。就连篱笆下,也要点下一颗颗刀豆种子。
三四月渭北多是干旱的,偶尔落雨,也不过是稀稀疏疏一阵小雨,刚刚湿了地皮,就被风吹散了。种下的蔬菜迟迟不见雨水,就一直沉埋在土地里,安静地等待那轰轰的雷声。父母也不急不躁,他们对土地有足够的耐心。
幸好菜园里还有一洼多年生的韭菜,春天的韭菜叶片宽阔、脆嫩。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用头茬韭菜加一点猪油蒸成的包子包饺子,它们煮熟蒸熟之后,那脆嫩的叶子几乎融化成一包绿色的酱汁,味道的鲜美,刚刚进入口里就融化了。
当黄土塬上的白杨变得葱葱郁郁的,把田野分割成一个个绿色的方格,当田野上的麦子,终于形成绿色的波浪——小麦开始扬花吐穗,天上终于落下了一场透雨,大雨哗哗地,激烈地敲打着屋瓦,溅起一股泥土的腥味。人们都兴奋起来,雨还没停,男人女人小孩老头老婆婆都走出屋门,蹲在菜园边仔细查看。呵,篱笆下,那一个个刀豆苗,从地下探出两只圆圆的耳朵,仿佛在倾听地面的消息。地畔上的南瓜葫芦也都向地面伸出了它们的手掌。辣椒地里,那一棵棵幼苗,看上去仿佛一根根鹅黄色的细嫩的针。长得最快的,当属菠菜了,这一场雨后,才几天时间啊,它们就把肥厚的叶片伸展到老碗一样大,人们就可以把它割下来汆面吃了。

最痛快的是麦收以后,老天好像在紧张地照看了一个春夏的麦田后,终于有机会把憋了一年的雨水尽情地挥洒下来。屋檐下一溜儿盆盆罐罐叮叮当当地响成一串。院子里的水一股股地汇入菜园。所有的蔬菜,都喝饱雨水,可着劲儿地往上长。很快,原本只有寸把长的辣椒、西红柿,雨过天晴时就蹿到一尺多高, 葫芦南瓜也伸出了枝枝蔓蔓,把地畔盖严,刀豆蔓呢,都攀住了篱笆互相比赛看谁爬得更快。
这时父母就走进菜园,把长得稠密的辣椒苗拔下,移栽到空处,并拿来一根木棒,插在西红旁边支撑着它。然后在地垄的空缺处,点种一些萝卜、白菜。
整个秋天,所有的蔬菜都都在互相较劲,那一棵棵刀豆蔓,把篱笆围成密密实实的一堵绿墙。只要你拨开那肥大的叶片,就能看到刀豆枝蔓间开出的那一串串淡紫色的小花,以及一串串翠绿的豆角。肩并肩生长的葫芦、南瓜,也快乐地吹起一只只金黄的小喇叭,招引着一只只蜂蝶为它们授粉。辣椒已经像一棵棵半米高的树,枝桠间都是一朵朵白色的花,还有刚刚结出的辣椒。整个园子让人看着就充满快乐。

母亲只要有闲暇,就会待在菜园子里,这里拔拔草,那里松松土,看见菜叶上生了虫子,就一只只捉出来拿去喂鸡。家里那几只母鸡,看见母亲就激动地围着她打转,等着她手里的虫子落到地上。每次雨后,母亲都要给每棵蔬菜根部施上农家肥,甚至把榨油剩下的油渣碾成细粉,作为最贵重的肥料,在每棵辣椒和西红柿根旁挖一个小洞,把它埋进去。别人看见了,都觉得母亲这哪是种菜呢,简直就是侍弄孩子啊。
不过我们家的蔬菜,确实一直都比周围几户人家的蔬菜长得好。尤其西红柿,大家种起来看着很容易,家家户户都长得枝繁叶茂的,足有半人高,可就是很少结果,或者结了果子,却一直是绿油油的,不能成熟。而母亲种的西红柿,不仅枝干粗壮,腰间还挂着一串串拳头大的果实。那果实经过阳光的映照,先后都红了起来,一个个看着就很诱人的。于是有的人就羡慕地问母亲有什么秘诀,母亲却又说不上来。
整整一个秋天,家里蔬菜是吃不完的,母亲可以用面粉拌豆角蒸熟,用青椒剁成碎末调好了吃。可以做葫芦包子,醋溜葫芦,或者洋芋南瓜汤。西红柿是我们最喜欢的,不论炒什么菜,只要放一只西红柿,我们就觉得味道鲜美。

当然吃不完的豆角,就让它成熟了再摘下来,一只只地用麻绳串起来,挂到屋檐下。葫芦也一样,吃不完的,把它摘下来掏去瓜瓤,切成长长的条,也挂起来晒干。这样,到了冬天没有蔬菜的时候,母亲就把葫芦干泡软切成细片,和洋芋一起用来做连锅面。刀豆可以煮豆子稀饭,就连刀豆那干*豆荚,母亲都舍不得扔掉,把它泡软了,切碎,放上水和一点碱、面粉,拌好蒸熟,也算一道不错的菜。
深秋,原野上的玉米棒子裂开了口,露出一口金色的颗粒。高粱把红艳艳的旗帜覆盖在山坡的梯田里。谷穗像一条条沉重的老虎尾巴,洋芋把土地都挤得裂了口子。地畔上的白杨的叶子,也都变成金色的,一片片地重回大地的怀抱。
这个时候,农家的菜园是丰厚的。一棵棵白菜包得又大又结实,萝卜粗壮得含满汁液。辣椒今天刚摘了一批,第二天又是满地红彤彤的了。只有葫芦、南瓜、西红柿们一天天地衰老了,叶子在慢慢地干枯。
每天,父母从生产队放工回来,就会提上一个笼子去采摘菜园里的辣椒、豆角、茄子,屋檐下也就一串串地挨挨挤挤地挂满了辣椒豆角、干葫芦。
霜降的前夜,对于农家是一场战争。就那么一天,忽地冷风刀子一样呼呼地吹了来,所过之处,一片片植物的叶子都凋落到地上。人们于是不分老少,一家人全都扑进各自的菜园子,把一棵棵大白菜砍下来,和萝卜一起拉回屋子。豆角也要一个不剩地全都摘完。辣椒太多了,来不及采摘,人们就连辣椒秸一起拔下来,在菜园里围成一堆,再用麦草苫盖住。其他来不及搬回的蔬菜,也都一样堆起来,用麦草盖严实。
那个夜里,白霜无声地降落下来,把一片片还留连着枝头的叶子全都扫落地上,即使没有落地的叶子也全都冻成蔫巴巴的了。整个菜园子一下子变得荒凉。
收获后的菜园子,土地会再次翻过,袒露的土地在暗淡的阳光下仿佛在积蓄着力量,在等待着又一个春天和又一个蓬勃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