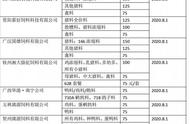深秋初冬时际,红薯又开始大量上市,即使在国内的众多大都市里,无论是早市,还是商场超市,都频现红薯的身姿;在城区街边,也可看见三轮车架上的圆筒状铁皮烤炉周遭摆放了一圈烤红薯,而一些连锁快餐店里,小袋包装的烤红薯条,乃是高价的佐餐主料……
此情此景,屡屡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农村和红薯结下的深厚缘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缺粮的老家农村大集体时期,几乎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好在还有大量的红薯来抵事,红薯在那时虽不算粮食,但在庄户人家里,红薯是添加在主食里当顿吃的东西,“红薯能当半年家”,多吃红薯确实可以节约口粮。
红薯不择土,春季栽种,秋后收获,省工省事,产量高,用途多,也不费肥,很受农民欢迎。
农村春夏两季,地头绿油油的红薯藤煞是好看,而红薯藤上的嫩尖,即红薯尖,口味纯正,也是不错的蔬菜,掐下、清洗,或素炒,或沸水烫渍,变成凉拌菜,偶尔也可将其“升格”为炒肉的佐菜。红薯藤则是喂猪的好饲料,丢生的、煮熟的红薯藤,大猪小猪都肯抢槽吞咽,嘴里稀里哗啦嚼得欢。
待到夏季时节,生产队插种的大片红薯,已经在地下初步成型,和我一样读小学的一拨农村孩子,每天从村小放学回来,书包一丢,出门找猪草、捡狗屎,瞅见村野周围没大人,顺便抠一两窝长势良好的红薯窝,刨出其中尚未成型的红薯,擦擦上面的泥巴,嘴啃去苕皮,巴嘎巴嘎就咬进嘴里,暂时填充一下肚子。
秋天红薯成熟时际,生产队把红薯挖出来后,全队按家庭人口和工分来分配,大人们挑着红薯回家,先拣选大的、好的红薯存放自家地窖,小的、差的、有伤口的,便赶紧拿来食用,自此,一日三顿都和红薯见面,红薯吃多了,屁也多,有时肚子还翻胃,但无论如何,总比吃不饱肚子好受得多,当然,红薯也要用来喂猪,尤其是红薯皮和烂红薯,几乎都进了猪肚皮。
犹记得当时尚在世的祖母心疼我,常常在中午烧火煮饭时,悄悄往灶火堆里搁置一两个红薯,我下午放学回来时,自个儿拿火钳去灶火灰里找取,撕开红薯皮,带温热的红薯肉,软软的,香香的,吃进肚皮里,浑身上下有股舒服劲,红心子的红薯味道特别好;祖父则把红薯切成片,晒干后,一部分做红薯干,可以当零食,也可拿去卖,一部分打成红薯粉,再加工为红薯粉和红薯粉条,那红薯粉条可炒可煮可炖可烫,可素也可伴荤,可凉拌也可热上,属于农家的家常菜,尤其是在新鲜菜少的月季,更升格为当家菜 ;附近不远的一个村子里,还有农家酿制红薯酒,只是听说红薯酒的味道有点苦涩,远不如粮食酒爽口好喝。
红薯,其貌不扬的红薯,过去的一些年辰,曾在家乡农村悄悄扮演过救命的角色,曾是农村人的重要副食品,还曾充当农村小孩子的零食和水果,也演绎着家人的温馨情怀。
文/ 吴志强 陕西省西安市
本文由“盛田杯·记忆中的禹州味道”征文比赛组委会推荐,原创首发。
该活动由中共禹州市委宣传部、中共禹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改革办)、《禹州通讯》、新华小记者禹州组委会、禹州市红薯制品生产行业协会和河南省盛田农业有限公司联合举办。